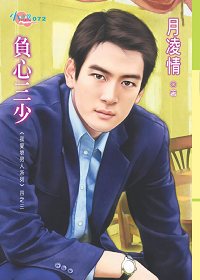暧昧的关系-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W的耳朵也许一年四季都是脏肮不堪的。他是我们区著名的耳膜炎患者。每年冬天他戴上一个黄色的耳朵套子,骑着车从什么地方来,敲我家的门。这些夜晚很冷。我姐姐总是系着花围裙从厨房里冲出去给他开门。她开了门后把双手交替在花围裙上擦拭,等W说完话再给他重新开门让他滚蛋。他捂着他的耳朵套子,站着,喘着气说话,远离我坐的白木椅子。我能看见W进门挟来的一股冬夜的淡蓝色寒流。我姐姐藏身在里面显得瘦弱无力,信佛一根迎风摇摆的柳枝。如果我还坐在白木椅子上,W说话声像蚊子叫一样轻。如果我走到厨房侧耳细听,听见W总是对我姐姐说老鼠怎么样袜子怎么样那家伙怎么样怎么样了。
〃他有病吗?〃我一向厌恶戴耳朵套子的W。〃不。他就是耳朵有毛病。〃〃他耳朵有毛病不去五官科治跑我家干什么?〃〃他跟我在伍家畈一起呆过。他帮我逮过八只老鼠。〃我发现我姐姐的眼睛在W离去之后就扑朔迷离了。她把她男人和婴儿搁在一边,独自躲在厨房间里,一声不吭地扮演怀旧的女妖。〃那家伙那家伙到底指谁?〃我擂着厨房门。〃不能告诉你。〃她说,〃怎么能告诉你呢?〃那家伙是谁?两年前我就想写一篇关于屋顶和人的小说。起因是我在图书馆的地板上偶然看到一张掉落的书中插页。插页是一幅石版画。画上覆盖了一片草苫屋顶,屋顶下迷迷朦朦地闪烁着人影,有几个人?一眼看不清。当我的手指抚摸那张无名石版画时,感觉到茅草屋顶在簌簌颤动。聚集在屋顶下的到底有几个人呢?如果那是一家,那么一家到底应该有多少人呢?这片屋顶下暂时先有三个人:W、傻子和老农。W听见整个伍家畈在夜风中抖动屋顶的茅草,沙沙沙沙响得他耳朵里长出泪珠子来。那时候W就有神神叨叨的毛病。他说这种夜晚这种地方人已经不会哭,但他的耳朵老是受不了伍家畈的夜风夜雨,很不要脸地流泪。老农说:〃你那双破耳朵是挖耳屎挖烂的,当我不知道?〃W继续说:〃一碰到大风天降温耳朵就烂得更厉害。流泪。流得不要脸。明天我要再出工就是灰孙子。谁出工谁就是灰孙子。〃
透过窗户玻璃看见村中的池塘结满了冰,结冰的水在夜晚会泛出淡淡的蓝色。这事他们从前在城里一直没发现。伍家畈的所有茅草屋顶都冻得够呛。W看见一条人影黑乎乎地沿着池塘走过来。W说:
〃我想要一副耳朵套,最好是丝棉的。破棉絮的只要布结实也行。〃这时候老鼠又从房子的各个角落里奔出来,聚集在一盏十五瓦的电灯泡下面。老农扔在那儿的饭团突然喷发出香味,老鼠们围着饭团很忙碌很活灵。屋顶下三个人从床铺上同时坐起来观望。这就是伍家畈夜晚的老鼠运动。他们每回都仔细地观望。傻子说,〃他们都饿慌了吧,怎么没打架?〃老农说,〃怎么没打架,他们在运饭团,运回窝里就要打,我听得见声音。〃老农每天省下一块饭团喂老鼠。W很可惜。他记得就是这一夜老农在墙上写下一排草书,是用红墨水写的,每个字看上去都是遍体鳞伤的痛苦样。
老农的瘦马脸也淌下那些字的血印,就像胭脂令人厌恶。W转过身看窗外。他看见村中的池塘结满了冰,一条人影黑乎乎地沿着池塘走过来。〃那家伙回来了,嘻嘻。〃W说。
〃明天我要出工我就是灰孙子。〃W又说。他听见门外踏冰的脚步越来越近,跳起来关了灯。
那条人影一旦走进茅屋,屋顶下面的人数就是四个了。那家伙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显得多么悲伤。他闯进门来挟进伍家畈冬夜透心彻骨的寒气。杉木板哐哐猛晃。W挂在门后的棉大衣扑在地上,棉大衣口袋里的两颗钢珠突破而出,乱滚一气,惊起老鼠树叶般的脚步声。
〃快把门关上,你不怕冷我怕冷。〃W把头缩进被窝深处说。进来的人影找不着灯,迷乱地摸黑徜徉。W似乎看见他捏造的情书躲在那家伙汗湿的手中扮鬼脸。他也在被窝里做了个鬼脸。他想至少要过几天假情书才会败露,收拾那家伙其实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只苦了八妞儿。她蒙受了不白之冤。八妞儿才十七岁,她还不知道约会是怎么回事呢。W曾经被八妞儿叫去逮他们屋里的老鼠。八妞儿的屋子也像八妞儿一样杂乱无章,疯疯颠颠。他就喜欢墙上贴的一张杨柳青年画。有个金娃娃骑在一条红鲤鱼上欢欢喜喜大闹冬天。〃儿子、女儿。〃W看着金娃娃咧开嘴笑。八妞儿说,〃你又叨咕什么呢,傻子。〃W问八妞儿,〃你墙上这娃真好,是男娃还是女娃?〃八妞儿开始说是男娃,又改口说是女娃。后来性急地乱摇辫子,红了脸。W就安慰她,管他是男是女呢,看着暖和就行了。八妞儿的茅草屋顶下只有两个人,他和她。W觉得他的耳朵不像平日那样疼。他开始施展多日来苦练出来的捕鼠术。他把一碗剩饭浇了香油放在屋角,碗上拴了一根粗麻线紧拽手中,等待八妞儿的老鼠闻香而动。〃我们屋的老鼠咋这么多呢?〃
〃多吗?肯定全是些男老鼠。〃
反正八妞儿经常听不懂男人的话。W笑着就真看见一只魁梧而英俊的老鼠跳上饭碗。他匀起手指把线一拽,碗如山峰压住了老鼠。那也许真是一只男鼠,鼠脚被压后还探在碗外强劲地挣扎。八妞儿欢叫一声上去观赏那只鼠脚,嘴里含糊地惊叹着什么。W问八妞儿,这捕鼠办法好玩吗?她没听见。她搓着手紧张地眨巴眼睛,突然高喊一声:〃拿火柴!烧老鼠!〃W对着满脸绯红的八妞儿愣了会,〃烧……吗?〃他掏出火柴盒交给八妞儿,然后睁圆眼睛注视她烧老鼠脚的动作。火苗子从鼠脚上喧腾而起时,W的耳朵一阵烧灼的疼痛,他护着破烂不堪的耳朵说:〃八妞儿别烧了,你给我织副耳朵套好吗?〃〃你看鼠脚一烧怎么发黄了?〃八妞儿说。〃我给你毛线织,我还有二两丝棉。〃W说。〃天呐,老鼠爆炸啦。〃八妞儿说着拍手蹦起来。W听见那只合扣的白瓷碗里爆发出一阵沉闷的呼啸声。他从来没听到过鼠叫声如此奇怪如此凄惨。那只孤独的鼠脚已经烧焦,它在八妞儿的胯下拼命踢蹬,仍然是有力度的。W在一股熏臭味中长叹一声,〃八妞儿,我他妈的白给你逮老鼠了。〃他把手里的麻线拴在八妞儿的床架上后,昏沉沉转了圈跑出门去。在八妞儿的屋檐下,W趴在窗棂朝里张望:八妞儿如痴如醉烧那只鼠脚,她的红脸膛还是挺可爱的。但W的呼吸道几乎被一股浓烈的腥臭灌满了,恶心难忍。他只得逃离八妞儿的屋檐下。外面风很大,耳膜炎患者W的耳朵让风一吹,痛苦得直想掉泪。这屋顶下原先是四人一家。初到伍家畈时大家都这么说。傻子还想做个光荣匾挂在门楣上。可后来发现那家伙买了烟藏在牛棚的草料堆里,夜里独自对牛抽烟。他有一本绝妙的好书锁在箱子里,每隔几天就取出来,躺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研究。就这样直到他睡着,那只手电筒总是忘了关,射出一道黄澄澄的光,照亮另外三个人。在另外三个人辗转反侧之夜,能听见那家伙在梦中鬼喊鬼叫:
八妞儿八妞儿八妞儿啊
〃他当真了。〃另外三个人说。
而八妞儿却蒙在鼓里。她跑来把鼻子压在窗玻璃上扫视四个人的屋子,鬼鬼祟祟地问:
〃那家伙怎么,那家伙……〃
其他三个人望着窗外心怀叵测。
〃你们屋老鼠多吗?〃〃多,老鼠每天在打洞。〃W朝泥地上猛一跺,他的脚就隐进去了,〃老鼠打地道战。〃
W从八妞儿的脸上掂量出她的手工编织本领。八妞儿确实不会织耳朵套子。他原谅了她也宣告这个冬天他的耳朵将要完蛋了。那家伙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脸色渐渐阴暗下来。他双手插腰,喉结在宽大的颚下跳动,敲出第一声愤怒的钟:〃把东西交出来!〃〃你丢了什么东西,那本黄书?〃
〃别他妈乱打岔。把袜子交出来。〃
〃我们三个人,你让谁把袜子交出来?〃
〃让你们三个人!〃〃三个人。袜子。哈哈哈。〃W第一个笑出声来,我知道丢袜子是借口,那家伙总归要爆发。一笑耳朵又疼,赶紧捂住。W朝另外两个人扮鬼脸,他发现傻子突然不笑了,傻子原先高高翘起的脚往床底下缩了缩,解放鞋鞋口上耷落着肥大的白球袜。其他三个人都看见了那种袜子,那家伙扑上去一把揪住了傻子的脚。〃不是你的。〃傻子梗着脖子喊,〃这双是我昨天上集买的,新的。〃〃鬼话。你一贯偷偷摸摸的不偷难受!〃
〃×!〃傻子的脚被擒住后红头紫脸,他侧过身去抓搭在箱子上的棉大衣。W看出来傻子想掏大衣口袋里的钢玩意干仗,他护住了自己的口袋,搡走傻子:
〃愿干仗掏拳头,掏我的东西干什么?〃
这时W回头看了看床上的老农。老农的眼睛兴奋得鲜红,欣赏他们三个人。一只黑鼠奔驰过他的枕头,老农的眼睛依然一眨不眨。〃走,我们出去打。〃偷袜子的喊。
〃出去打,地方大。〃丢袜子的说。
剩下的两个人望着两条背影怒气冲冲卷出屋子,谁也不说话。他们屏息谛听着外面的动静。但是夜风一个劲地狂吼着,几乎淹没了那种奇怪的人声,唯有茅草屋顶簌簌颤动。〃外面多冷,天又黑,傻子眼睛不好,准吃亏。〃老农先说话。〃傻子傻子,怎么不偷那本书,倒偷一双臭袜子?〃W的样子有点恨铁不成钢。〃鬼知道。傻子喜欢他的白球袜吧。〃
七八分钟过后两个打架者归来,昏暗的灯光照耀着两张年轻的疲倦的脸。都挂了彩。那家伙纤薄的嘴唇还在流血,红得使人心碎。傻子的伤在前额上,大概是被十片指甲同时抓出来的,形状像一片沼泽地。他们先后坐到自己床位上,一声不吭,傻子说那句话的时候W正在手里拼命转钢球,他突然听见傻子在哽咽,哽咽声越来越响,傻子跳起来眼泪汪汪对他们三个人吼:〃都滚出去,让我一个人一间屋住一宿啊!〃他们三个人没有理睬。但屋顶被傻子骂得浑身一颤。他们听见整个伍家畈在夜风中抖动屋顶的茅草,沙沙沙沙响得他们耳朵里长出泪珠子来,透过窗玻璃看见村中的池塘结满了冰结满了冰。伍家畈欲雪未雪的日子总是拖得很漫长。那些日子里老农得了严重的皮肤病,浑身奇痒不止。W抓起老农的手臂看见无数斑驳的鼠印,逶迤起伏。他说,〃都是老鼠夜里爬的。〃W想起老农夜里睡觉总是把手臂伸出被子,呼唤他心爱的老鼠。W对老农说,〃你这皮肤病好不了,你知道吗?〃老农说,〃我知道。抓痒挺舒服,总比得耳膜炎好。〃
下头一场雪的那天黄昏,老农对着墙继续搔痒,他创作了一支奇怪的歌谣陆陆续续唱出来。W听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