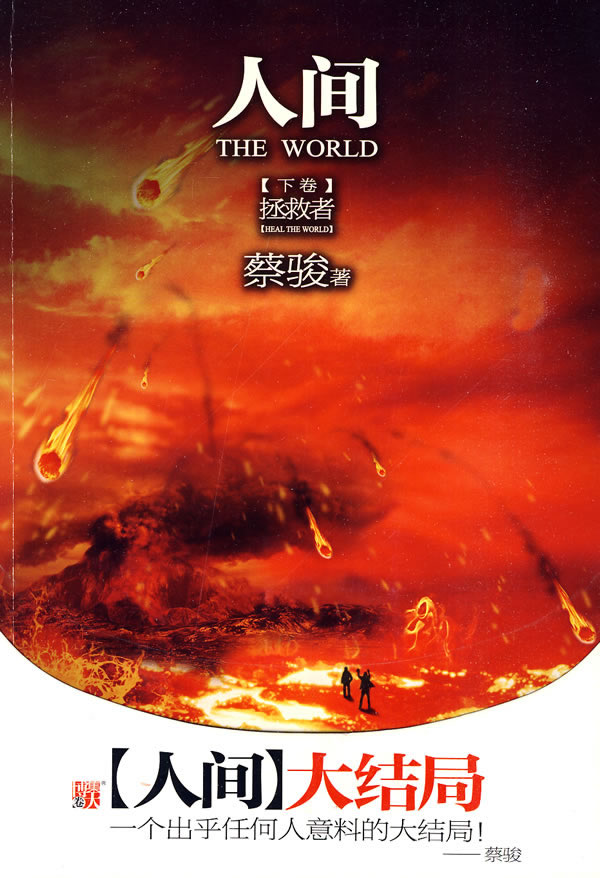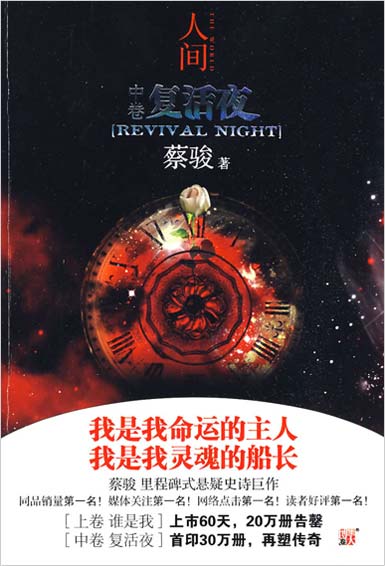说吧,房间 作者:林白-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巫器与刑具
那些器械闪闪发光,寒冷而锐利。它们奇形怪状,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出现过,它们的弯度、刃尖、齿痕所呈现的非日常性使它们具有深不可测的复杂色彩,巫器的神秘、刑具的决绝、祭器的神圣不可抗拒,以及它们作为手术器械的尊严,这些品质中的任何一种都会使我们不寒而栗。当它们聚合在一起,那种寒冷绝非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魔法般的质变,变成刀刃之上的刀刃,寒光之上的寒光。我们惊弓之鸟般的身体即使背对它们,也会感到它蓝色的火苗吱吱作响。
我们遭受白眼,白眼也是刀刃,它们在空中掠来掠去,我们尚未到达医院就能感到它们,从大门到门诊挂号处,到妇科的候诊室。妇科这两个字也是某一种形式的白眼,它只能使四十岁以上的女人感到亲切,却使二十多岁的未婚者感到无地自容。这是一个男女之事的后果必须到达的地方,这个地方一逆推就会推到性事,凡是需要遮掩的私密的事物到了这里都被袒露无遗。初潮的年龄、经期的长短和数量,人流史、生育史、婚史,等等,一点都没有办法隐瞒。我们完全丧失了意志,下意识地答出真实的情况,我们说出未婚,这本是首先需要隐瞒的事实,但我们不说她们也会知道,她们一看就会知道,一摸就会知道,而且这事即使从逻辑上也能推出,既然结了婚又从未生育过为什么还要打胎呢?她们既不接受终身不育者又不尊重别人。就这样,未婚这个事实从里到外掠夺了我们的力量,我们心虚腿软,目光游移,穿着白大褂的女人全都是巫婆一般的明眼人,明眼人一眼就把我们入了另册。
这个人冷冰冰地坐在我们的对面,白色的大褂跟巨大的眼白的确是同一种事物,黑色的瞳孔在眼白之上,从那里透出审判的严威和巫婆的狠毒。如果我们吓得一哆嗦之后如实道出我们尚未结婚就已经做过一次或两次人流,这已经是第二次或第三次,白色的巫婆就会说,你是只图快活不要命了。
然后我们怀着绝望进入人工流产手术室,这是如此孤独的时刻,如果有人陪我们来,她们将留在门外,如果我们独自前往,每接近手术台一步就多一层孤独。与世隔绝,不得援救,耳边只有一种类似于掉进深渊的呼啸声。在四周冷寂的敌意中听到一句像金属一样硬的命令:把裤子脱了!全都脱掉,没有羞怯和迟疑的时间,来到这里就意味着像牲口一样被呵斥和驱赶,把自尊和身体统统交出。“把裤子脱掉”这句话所造成的心理打击跟被强奸的现场感受相去不远,在手术器械之前就先碰疼了我们,或者说这句话正是手术器械的先期延伸,是刑具落下之前一刻的预备命令。
然后我们赤裸下身。这是一个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时才能坦然的姿势,即使是面对丈夫或情人,赤裸下身走动的姿势也会因其不雅、难看而使我们倍感压力。在这间陌生、冰冷、白色,异己的房子里,我们下身赤裸,从脚底板直到腹部,膝盖、大腿、臀部等全都暴露在光线中,十分细微的风从四处拥贴到我们裸露的皮肤上,下体各个部位凉飕飕的感觉使我们再一次惊觉到它们的裸露,这次惊觉是进一步的确证,它摧毁了我们的最后一点幻想。
我们的脑子一片空白,命令的声音像铁一样入我们的意识,我们按照命令躺到了产床上,这是一个完全放弃了想法、听天由命的姿势。我们像祭品一样把自己放到了祭坛上,等待着一种茫然的牺牲。那个指令从天而降,它不像从一个女人的嘴里发出、没有声源,声音隐匿在这间屋子的每一个空气分子里,它们聚集在上方,像天一样压下来。这个声音说:
把两腿叉开!
如同一个打算强暴的男人,举着刀,说出同一句话。这使我们产生了错觉,以为这个女人在这一瞬间变成了男人。“把两腿叉开”,这是一个最后的姿势,这个姿势令我们绝望和恐惧,任何时候这个姿势都会使我们恐惧。那个使我们成为女人的隐秘之处是我们终其一生都要特别保护的地方,贞操和健康的双重需要总是使我们本能地夹住双腿。但现在我们仰面躺着,叉开了腿,下体的开口敞开着,那里的肌肤最敏感,同样的空气和风,一下感到比别处更凉,这种冰凉加倍地提醒我们下体开口处空空荡荡一无遮拦,有一种悬空之感。
但对于那个将要动手的人来说天然的开口还不够大,有一种器械,专门用来撑开子宫颈,是一种像弹弓一样的东西。另有一种细而长的器具,用来伸入子宫弄掉里面的胚胎,这个过程妇科称为“刮宫”,我想那细长闪亮的钢条也许就是叫作“宫刮”。宫颈撑触碰到皮肤的时候我们以为开始刮宫了,肌肉紧张,骤然收缩,在僵硬的同时一层鸡皮疙瘩从私处迅速蔓延到大腿、膝盖和脚背,我们神经的高度紧张使这触碰变形为一种疼痛,也许只是由于宫颈从未被器具碰过而有一点异样的微疼,但我们禁不住呻吟一声,仿佛疼痛难忍。
真正的疼痛马上就到来了。
那根细长坚硬冰冷的钢条(或者叫宫刮)从下部的开口处进入我们的身体,它虽然只进入我们的子宫却像进入了我们的五脏六腑,抑或是子宫在这个时候就变作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它在我们身体的深处运动,用它铁的质地强制我们的肉体,将紧贴在子宫内壁的胚胎剥离开。那是一种比刀割的疼痛还要难受十倍的痛,没有身受的人永远无法知道。虽然它痛在局部却比任何一种痛都要迅速地涨遍全身,在传递的过程中又加强了痛感,每一个细胞的痛都真实而直接,仿佛那个宫刮巨大的刀锋(我从来没有搞清楚它是否有刀刃)直接刮在每一寸皮肤和内脏上,而不只是刮在子宫里。这种痛使我们感到一秒钟就无比漫长,五分钟就如同五十年。我们在此前听到的有关经验全都是不准确的,做过的人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小手术,五分钟就能解决问题,甚至都不需要麻药,因为简直就不疼,最多跟来月经时肚子疼差不多,还说现在有一种新的办法,用电吸一下就出来的。
我们痛得冷汗直冒,全身瘫软,眼前发黑,我们的子宫从未受过损伤,现在有一个铁的东西要把吸在上面的胚胎生剥下来,就像有人要把我们的五脏六腑硬扯出来一样。这跟断指之痛的单纯和明亮完全不同,那是一种闷痛,是痛的噪音,黑暗的痛,是碎裂和放射的同时又是凝聚和胶着的痛,是一种刺眼的泛光,没有方向却又强劲无比的风,它使人无法叫喊只能呻吟。这种痛的难耐使我们怀念另一种痛,那种在皮肤表面割一刀的痛,被开水烫伤被火烧伤的痛,它们火辣辣的痛像晴朗的天空一样透明,像鸽哨的鸣叫那样确定和易于捕捉,像晴天霹雳那样令人震惊却比噪音容易接受,在我们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记忆中,它甚至灿烂无比,它的亮光被混浊晦暗的闷痛衬托得无比真实。
我们后悔听信了别人,如果没有相反的心理期待疼痛肯定能减弱一些,我们的心理脆弱而敏感,瞬间就能放大或缩小生理上的感受。那些别人不是道听途说者就是已经生育过的女人,而与我们境遇相同者的经验永远深藏不露,真相连同经验一起被遮盖。
没有人能将真相告诉我们。
过去
在80年代的N城,人工流产是韦南红成为我的朋友的一个契机。但做人流的是我,而不是南红。那时候她刚刚跟一个本学院的青年教师好,那人是颜海天的同事,也是画画的,但才气不如颜海天。颜对南红没有感觉,这是很久以后他告诉我的,他跟南红的关系一直平平。与南红好了一年的那个谁,现在我已经记不住名字了,好像叫什么军,建军或小军,但这关系不大。他在南红心里没有留下太深的痕迹,我也只见过他一次,那时候南红跟他已经讲清楚,不存在什么特定的关系了,但他们还像朋友一样来往,没有人呼天抢地,悲伤欲绝。
对比起来,我有时会为自己感情的古典而不解,爱一次就会憔悴,再爱一次就会死。我只比南红大五岁,却像大了整整一个世纪。真是匪夷所思。
还是回到人工流产这个话题上,这是几个重要的话题之一。
当时我的母亲尚未到N城,所以我在这个城市可以说是举目无亲。举目无亲这个词一点也没给我造成孤苦伶仃的感觉,这事有点奇怪,我好像从小就喜欢举目无亲,中学读书的时候离家只有五分钟的步行路程,我还是执意要住校,每周只回家一次。上大学的时候过春节也不回家,留在学校天天睡懒觉,心里十分舒服。因此在N城的十年时间里举目无亲正好使我如鱼得水。我一向觉得,在一切社会关系中,亲戚是最无聊的一种,凭着莫名其妙不知有无的血缘或亲缘关系,一些毫不相干的人就跟你有了干系。你跟他们完全缺乏认同的基础,永远不可能有相同的价值观,你认为很珍贵的东西别人觉得一钱不值,你认为好看的颜色别人心里感到晦气十足,你们哪怕到了下辈子也不会有多少共同的地方,但仅仅因为一个亲戚的称呼你就对他们有了责任,他们来办事、看病或者只是来玩,你都必须责无旁贷地帮忙。这真像被强行套了一个笼头,跟野生动物被驯化为家养动物一样痛苦。
亲戚就是这样一些事物,它的本质是网(这点大家都已经指出了),它漫布在水中,像水草一样漂荡,谁碰上它就被网住了,网住了还是在水中,不会马上死去,但前后左右上上下下却被死死圈住,往任何一个方向都游不开。这样的鱼只能在梦中设想那广阔无比像空气一样轻盈的水。
这多么悲惨。
大学毕业分到N城使我既高兴又人心不足,N城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它距离我的家乡有500公里。但距离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它的陌生不是因为远才陌生,而是因为没有任何亲戚熟人朋友的那种陌生,陌生得像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N城这个名字对我来说跟西宁或贵阳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地图上的一个圆圈,与我从未有过关系。
一张白纸意味着什么?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到N城的单位报到,唯一的遗憾是这里离家乡还不够远,亲戚们还是有可能到这块白纸上来,涂上一些令人不快的色彩,我想若是弄到西藏拉萨或者黑龙江的齐齐哈尔什么的,一辈子都不会有亲戚光临,这该有多么美妙!
在N城的自由生活中我度过了七年时光,七年中我在业余时间里埋头写作,80年代跟90年代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没有双休日而后者有,所以80年代的整块时间除了节假日就是每周的星期日,在这些神圣的业余时间里我不需要拜亲访友,连想一想的工夫都不需要,这使我在大量的阅读和练习中慢慢地成长起来,写出了一些还说得过去的诗,使我在虚荣的青春期获得了一些轻佻的自我膨胀的资本。我想我如果在N城有许多亲戚,她们决不会眼睁睁看着我到了二十七八岁还没有一个可以用来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