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天系列之 离恨-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哪来的野鸟!”追命抱怨。仰头灌了满口酒香。
六月初四,忌出行,诸事不宜。
甘侯堂里来了不速之客。
甘侯堂主欧阳祁看着戚少商和追命,道:“二位名捕来访,不知有何指教。”
“指教倒是不敢。”追命很不客气地坐下,道:“听闻欧阳堂主最近自徽州购买了些上好的角刺,我们想尝尝。不知欧阳堂主肯否?”
欧阳祁很大度的挥手,侍婢端来了紫砂镶金的茶具,濯,冼、泡、煎,洗,点。
两杯醇香略苦的上好角刺便放在了二人前。
戚少商端起杯子慢慢地饮了一口。
放下杯子,戚少商直视欧阳祁:“敢问堂主,这苦丁本为药茶,并不适宜平日饮用。甘侯堂做的是生意,自然不该打亏本的算盘——既然堂主肯大费周章远从徽州运茶,何不到杭州取龙井?”
“戚少商。你精明,更聪明。难怪诸葛先生有意让你坐拥金风细雨。”
后面的珠帘顾惜朝悠哉游哉地挑开,走到中堂。
追命大骇:“顾惜朝!你不是……不是早死了么?”
顾惜朝看了一眼追命,嗤道:“谢谢三爷的吉利话。可惜今天诸事不宜,不然顾某也好入土为安。”
追命悚然坐下,看着戚少商。戚少商却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把杯子里续了茶,道:“苦丁容易受潮变味。而在下有所耳闻,甘侯堂主大手笔,用檀木盒子将这些茶密封了,再用大箱子套住那些盛放角刺的檀木盒子,中间放了从襄州舍近求远运来的草木灰。”
“戚神捕果然耳听六路眼观八方。草木灰防潮,何怪之有。”
“单是草木灰,也就罢了。”戚少商坐下自己点满了茶杯,笑道:“我还听闻了一件趣事。清友堂该行做起了盐卤生意。”
顾惜朝一偏头:“那又如何。”
“戚某就是好听旁门左道的事——想我在连云寨时,寨里柴盐都是自给自足。曾听一个制盐工匠说盐卤和碱头一起熬煮,晒过后,就是雪白的盐。”戚少商喝完了茶。起身道:“襄州本就是我大宋制碱之地。地含碱而生草木亦然多碱。那里的草木灰妇孺皆知洗衣胜过皂荚千倍。”
顾惜朝只静静听着,默默看杯中墨玉色的茶汤,然后展颜一笑:“说得甚好。顾某无话可讲。”
“说来还多亏了盛兄安插的线人们集回的线报。戚某不过是坐享其成,胡乱猜想些。”戚少商负手道:“请欧阳堂主和顾公子,不,该是清友堂主和我们回六扇门。”
顾惜朝笑意更浓了:“既然你也做了捕头,拿人归案不是该有证据么。”
戚少商道:“证据。我知道清友堂主做事一向不喜欢留把柄。上次意外沉船,这次进门就嗅到了桐子的味道。恐是要茶库失火了。”
欧阳祁哼笑一声:“那你们还有什么证据?”
戚少商眸子炯亮地看着欧阳祁:“盛兄说让我在这里找一个内应的人。我正寻着他。”
顾惜朝和欧阳祁的面色都沉了下来。
欧阳祁慌了神,一把揪过顾惜朝:“谁是内鬼!是你?!”顾惜朝苦笑:“为什么恶人总是我做?”说完手里飞刀末入了欧阳祁心口。
戚少商和追命悚然看着顾惜朝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当啷一声,那飞刀扔进了茶壶里,墨色的茶汁里散了嫣红,红黑相间。周围的侍婢尖叫着乱作一团。
顾惜朝冷看了追命和戚少商一眼,拍开一扇暗门和身边几个仆臣悉数离开。追命抢身拉住戚少商进了暗门,顾惜朝回身,掬起一把飞刀抹向戚少商的颈脉。戚少商一凛,剑尖一挑,那飞刀便脱了顾惜朝的手,却不及被顾惜朝反手一扣脉门。
戚少山看着那扣住自己的手腕的纤细五指,冷得像冰。这一扣,顾惜朝的体温便顺着腕下的动脉,延到了戚少商的心室里。
顾惜朝看着戚少商,一刻刹那。他们有多久没有这样近的看着彼此了——那“报恩令”一劫后,每次二人咫尺相看间,无名和逆水寒锋刃砥砺的光痛刺眼瞳,隔得两人咫尺彼岸,两茫茫。
[我终究是不想杀他的。]
往昔杀路千里,血阑干,终不忍。
只缘感君一回顾。
戚少商觉察了顾惜朝在分神。
空气中有一丝兰香——高贵而谲艳。
“追命!”戚少商喝道:“截住那灰衣仆!”
言罢,只是深看了一眼顾惜朝,撤了剑追过去。
横剑在那灰衣仆之前,戚少商道:“欧阳堂主。”
易容的面孔上是一双含了怨毒的杏目。
欧阳祁冷笑:“顾惜朝。最后你还是做了恶人。你这个卑鄙小人,叛徒!”
最后一句叛徒欧阳祁似恨不得生啖了顾惜朝的肉一般。
却换来一句冷笑:“堂主,好眼力。”
戚少商紧了紧手中那把小巧的钥匙——
欧阳祁笑得森然:“别以为女人好骗。你的一举一动都收在我眼里。你不该这时给九现神龙钥匙!”
顾惜朝笑笑,嘴里却有了锈香。
“我只怕没时间了。”
欧阳祁突然凄绝地望了那青色的背影一眼,杏目翻白直倒在地。不一刻便七窍流血。
追命骇然:“她事先服毒了!!”
戚少商只觉得那女子流血的七窍惨极无比——无关其他。他只想到了最坏的结局。
“顾惜朝!”戚少商回身,只见那颀清的背影耸然一震。倏然倒下。
“顾惜朝!”戚少商来不及接住他倒下的身躯。再扶起顾惜朝时,只见他面色惨白如雪,映衬着发越发得黑。
“走。”顾惜朝仿佛耗尽了平生的气力,吐出一个字。
“去哪?”戚少商愣问得连追命都实在听不下去背转过身,人神共愤。
“我已中毒……死状……面目可憎……你……别看。”顾惜朝说得断断续续,不多见的口气平平而语,倒像是说着一件无关于己的事。
“我带你一起走。”戚少商全然不觉自己已经泪湿了脸颊,那些无意识的水珠淋漓在怀里气息危旦的人煞白的颜面上。
“大当家的……你要再……向我讨债……恐怕……断无可能了。”顾惜朝笑得像个孩子,毒发让他眼盲得一片黑,手指摸索在戚少商面上,一片冰凉。
那只冷而苍白的手突然像中了箭的隼,倏然垂下,带了一手不是自己的泪,静静地搁在了地面。
尘埃落定。
壅市子上人寥寥然。牛仁街前几个贩夫讨生活匆匆而过。
黄历上诸事不宜。
整个汴梁在薄暮里安安静静。
六扇门中庭里无情把那隐笛轻轻凑到唇边,天上便掠过了一剪隼影。是顾惜朝的微风。那白隼乖顺地絮絮鸣叫着,盘旋在六扇门四阁两院六道门的地界上空。
“云王已然招供。多亏了秘窖里的账本和那些茶箱。”
戚少商默默喝着炮打灯。那镪水一样的味,那刺鼻的酒气,那一切的一切成了一种习惯,像渴了就要喝水,饿了该吃饭。
酒味横亘在空气里。无情踟蹰着,把顾惜朝在甘侯堂塞给戚少商的钥匙慢慢推到戚少商面前。
那不算遗物的遗物。
戚少商斜眼看着钥匙,劈手拿过来塞到怀里。
“那晚赴宴之人无一幸免。毒却不是顾惜朝所下。欧阳祁觉察了有人潜入清友堂,便按云王的意思准备了毒酒,灭口清友堂,顾惜朝便将计就计助甘侯堂毁了之前的盐茶。宴会上他也是才知有毒,事发突然也应付自如。保全了你。”无情垂着眼睫,道。
戚少商看着手里的酒罐空了,便又换一罐,拍开了泥封,仰头灌。
无情轻叹:“也亏得顾惜朝献计‘卤碱制盐’,才又让断线重续。”
“这差使。是六扇门找上他的?”戚少商问。
“是师父的意思。”无情看着扇面,幽道:“师傅说他不安宁,得找个让他安宁的法子。于是我便问他可愿意帮忙。”
戚少商一怔,到口的酒滞了滞:“他知道这个案子我在办?”
无情啪地收起扇子。他恍惚想起那日惜晴小居里,陋屋中端然而坐的书生。屋顶漏光而下,尘霰乱飞。青衣却恍若片羽不沾。晚晴的牌位放在桌上,纤尘不染。
他凝眉集思,然后放了手里的书:“你这个不情之请,顾某应承了。就算是还戚少商的债。”蓦然他展颜一笑,轻挑着好看的眉峰:“诸葛先生说得甚是……这辈子我恐是不能背着债去死。缠得够烦了,现世两清未尝不是好事。”
“然后他便来找到我。他对我说:‘一个大活人被囿在陋室里成日和亡妻为伴,期期艾艾自己都觉得可悲。’他让我帮他摆脱铁手的监顾,摆脱六扇门,摆脱这个尘世。”戚少商仰头灌了一口酒,突然笑得人畜无害:“说来,我们摆了二爷一道。”
无情扬唇一笑,不自觉得蹙了眉。
说罢了。无情默然,戚少商复又成了哑炮。二人就这么坐听风吹。
满厅槐芳,一地落英。
他果然是机关算尽。戚少商边喝边想。
就连那晚残了的腿都尽收其中。要刺中癔怔中自己的左心对他顾惜朝来说易如反掌。就如同三脚猫刺个草把子,何其容易!
而他居然把“残腿必然趔趄”都算计在内——他那虚晃地扎在自己左胁,骗过了所有人,也让所有人都信极了顾惜朝要杀戚少商,他们不共戴天。只不过失手了。
他这样苦心经营着,打落牙和血吞。只为了留命,留住他戚少商的命,留住他这个最亲密的敌人,留住他此生唯一的视若知己。
难道真应了那句:人一转性,离死就不远了。是啊,那个曾经是草菅人命杀人如麻的玉面罗刹顾惜朝,为什么偏偏对他戚少商就是下不得手?
然而,他还是怀疑了他,他还是没看透他。直到那个无法挽回的最后,一切为时,已晚。现在的通透,阴阳两隔,自己是永无机缘对他说说;而他,也再听不到。
戚少商挺直腰板站在曾经的惜晴小居,如今长蒿没人的空地上,泪下潸然。向着那苍天百日长吼一声:“我不配!我戚少商,不配!!”
不配……
不配…………
不配………………
四周的回声如鹊鸟学舌一般重复着那声不配,滑稽至极。
惊飞的翠鸟扑着短翅飞过蒿尖,远去不见。
六扇门前庭里一桌的酒罐子。追命挨个拿起来摇晃,最后瞠目结舌。
铁手看着那七七八八酒罐子堆里晶莹玉润的平乱珏,嗟然。
那晚惜晴小居最后的三人对酌。
戚少商中的哪里是鹤顶红。
那是天下的至毒,随着日子走五经串六脉,终难幸免。
那毒,名为“离恨”。
人间四百四病,相思病最苦。
天上三十三天,离恨天最高。
那是女娲氏炼了五彩石都补不回的遗恨,断无绝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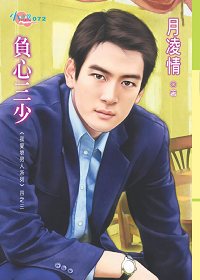



![实验的人生[法医馆系列]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1339.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