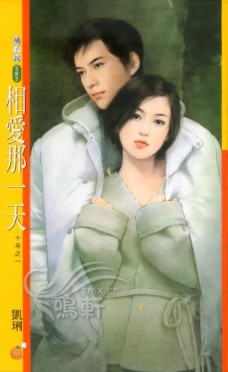爱那么短,遗忘那么长-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洗净生命
红头发的哥哥,喝完苦艾酒
你就开始点这把火吧
烧吧。
海子《阿尔的太阳给我的瘦哥哥》
无数的人为凡·高写过诗,却独爱这首海子的《阿尔的太阳》。
凡·高不是理想的情人。
理想的情人,应该是金庸先生笔下的陈家洛。他必是浊世翩翩佳公子,身份显赫,有使不完的金山银山,可以为我买花衣裳,还有桂花糕;他也必须武艺高强,在我受人欺负之际闪亮登场,一手挽出几个剑花,另一手温柔地抱住我,在丝竹声中从半空中旋转,慢慢落下。他还要长得面如冠玉,玉树临风,日日看他不厌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才愿意陪他远走大漠,永不回中原。
再看凡·高,被海子称为〃瘦哥哥〃的凡·高,1853年3月30日出生于荷兰北部布拉班特省的格罗渥特·松特丹一个乡村穷牧师的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由于家大口阔,不得不从16岁开始就出外打工,在很多画店做过助理。一度在叔叔家卖画度日,爱上了守寡的表姐凯。凯是典型的荷兰女子,深栗色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睛,热情而典雅。一次午饭后,当凡·高与凯在小溪旁的树阴下休息时,凡·高终于忍不住向凯吐露自己的心声。凯却很愤恨地离开了,躲到家中再也不愿见到他。终于有一天,凡·高把手放在蜡烛上烧,烧出铜钱大的洞,要表姐答应他的求爱。凯在惊骇之余,却坚定地说:
不,永远不。
换作我们任何一个女子,也会说: 不,永远不。
我们只是一些有小小虚荣心的凡间女子,上演不起大悲大喜的戏剧,我们只合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我们承受不起那样荒诞炽烈的爱。如果我的陈家洛拿着一把大刀,砍下自己的一只手,递过来对我说:
香香公主,你爱不爱我?不爱我,我再砍一只?饶是他长得貌比潘安,钱比邓通,我也要逃命去了。我们的爱人合该似徐志摩那样: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在我们拒绝他之后,他只是缓缓地转过身,一缕长发遮住他的左眼,背着剑,朝着如血的夕阳走去,留下一个萧索的背影。从此,江湖上多了一个断肠人,他却永远记得那年我们相识时的桃花。
我们分得清幻想和现实。而凡·高却常常游走在神界和人间之间。他捧着自己的心,用神的热忱去待人,常把周遭人烤炙得惊恐离去。在叔叔家卖画不成之后,他决定去布鲁塞尔的传教士培养学校学习,期冀全能的上帝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可怜他拉丁文和希腊文很糟糕,只好退学了。他不甘心,自愿去条件极其艰苦的矿区当牧师。
那是1878年,他回到艾登,在没有领到许可证的情况下,去比利时的波瑞纳吉煤矿区开始传教活动。那是一个如地狱一般的地方,矿工们过着非人的生活,经常有瓦斯爆炸事故。为了给矿工们最大的帮助,凡·高与矿工们住在一样的破房子里,并把自己全部的食物和物品送给他们。他怀着火中取栗的精神忘我地为矿工奔走,代替天上的老爷子洗净生命。
26岁的时候,也就是1879年,他被布鲁塞尔传教本部解除传教士职务。最终也被教会辞退。理由很荒诞,因为〃过于热忱〃。他热忱到神的使者们都感到恐惧了。
读李碧华的《霸王别姬》,突然又想起凡·高。程蝶衣和凡·高一样,分不清楚虚幻和现实,他们只管在自己的天地里,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1880年,27岁的他决定去学画画。就像只有小学文化的沈从文跑到北京要用一支笔打天下一样,让人乍一听简直就是疯话。可是他们都是天才,我们从来都允许天才可以有特殊的地方。疯话成了神话。
他遇到了妓女西恩,两人很快同居。西恩给他做模特儿,为他做菜、烧饭、洗衣服,他让西恩抽雪茄、喝酒,自己却常常饿着肚子。他不是西恩的白马王子,他不名一文,穷得三餐不继,全靠弟弟提奥的救济,相貌堪称丑陋。可是西恩对他来说却意义重大,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需要〃他的人。他不是仅仅把她当做情妇,而是要和她结婚,给这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人一个名分,一个家庭,一段完整的爱情和结局。他要照顾她一生一世。
这桩拎不上台面的婚姻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可是他们两人心意已决,并且商量好,等到凡·高一个月能挣到150法郎就结婚。
但是凡·高始终都没有能够挣到150法郎,始终靠弟弟提奥的接济过活。他黯然地离开了西恩,唯一一个〃需要〃而又愿意接受他的人。1883年,他走了,从此再没见过西恩。
他还不甘心,从第一个英国房东的女儿、表姐凯、西恩,他始终怀着如火的激情,可是每一次都是以失望收场,他内心的热情如同死火山的熔岩,百转千回,一旦迸发,就能摧毁整个庞贝城。终其一生,他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只能看到他画的那一束向日葵,那么得浓墨重彩,却刻骨地荒凉。
最近又有英国传记作家嚷嚷说,根据考证发现凡·高还有一个秘密儿子,就是和西恩生的,正欲做DNA检验云云。大约世人总爱痴人说梦,拿他人的伤痛八卦扯淡,所以活得自在。
1888年初,35岁的凡·高厌倦了巴黎的城市生活,来到法国南部小城阿尔寻找他向往的灿烂的阳光和无垠的农田,还有向日葵。他租下了〃黄房子〃,准备建立〃画家之家〃(又称〃南方画室〃)。他的创作真正进入了高潮。《向日葵》、《夜间咖啡座·室外》、《夜间咖啡座·室内》、《收获景象》、《海滨渔船》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第51节:凡·高:一如鸢尾任平生(2)
1890年7月27日,精神病数度发作的凡·高借口去打乌鸦,在一块麦田里对着自己的肚子开了一枪。他没有立刻就死,还自己走回客栈,要求医治。两天以后,他痛苦地死在弟弟提奥的怀里。
71年后的7月,也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海明威把双管猎枪放在自己嘴里,扣动了扳机。
海明威是一只决绝的老狮子,他果断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可是凡·高是多么地不想死,虽然他选择了死。
他来到他那么热爱的麦田里,也许只是想向上帝呼告: 求求你,给我一点点的爱,只要一点点。他想用枪声来引起上帝的注意。
就像一个孩子,站在旷野中号啕大哭,哭得每咳一下就呕出一碗血,天地动容。如果我是上帝,我会擦去他的泪水,收回他的猎枪,让人间变得如他的画一样美好。他馈赠了这个世界那么多,给予他多少都不过分。
他活着的时候只卖出一幅画《红色葡萄园》,1890年,比利时画家安娜·博赫以400法郎的价格买下了,现存于莫斯科。在他死后,他的画卖到了天价。1988年,《鸢尾花》拍卖到5300万美元,可是谁能想到他活着的时候只有一个卑微的想法:自己的画卖出去能值买颜料的钱。
每每看到这里,便悲伤得不能自已。
如果我能穿越时空,我想来到凡高的身边。假如我是有钱人,就买下很多他的画;假如没有钱,只是一个穷记者,我愿意为他写一篇中肯的评论登在报纸上,让他高兴一下;假如我既没钱,又没有文化,也许就是一个村姑,那么我诚恳地告诉他我喜欢他的画。
看他的画,不需要太多的修养,只要你真正地去喜欢大自然,喜欢生活就够了。
我会不停地说,《鸢尾花》太美了,《有云雀的麦田》太美了,《春季垂钓》太美了,《阿尔的吊桥》太美了,《开花的栗树》太美了。太美了。
据说在凡·高博物馆里循环放的歌曲就是美国民谣歌手Don Maclean唱的Starry Starry
Night。一把木吉他,简单的配乐,简单的旋律,却直逼心灵,正如凡·高,和他的画。
……
星夜下,当心中再没有一丝希望
你像热恋的人儿般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我本可以告诉你,文森特
像你这样美的人是不适合这个世界的星夜下
空荡荡的大厅里挂着画像
无名的墙上挂着没有边框的头像
他们看着这个世界,无法忘却
就像你曾经遇见的陌生人
衣衫褴褛、面带嘲讽的人
血红的玫瑰银色的刺
破碎在洁白的雪地上
现在我知道你曾想对我说些什么
你清醒的时候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你努力想让他们得到解脱
他们却不予理会
他们不会明白
也许永远不会
无数的人为凡·高写过歌,这首是最美的,最悲凉的,最达到凡·高内心的歌。
Vincent van Gogh
文森特·凡·高(1853~1890),出生在荷兰一个乡村牧师家庭。后期印象派的三大巨匠之一。生前他只卖出过一副画,死后他的《向日葵》、《鸢尾花》、《加歇医生像》卖出了天价。1890年,他开枪自杀,年仅37岁。
第52节:毕加索:那是你要的幸福(1)
23。 毕加索:那是你要的幸福
Es tan corto el amor; y es tan largo el olvido。
我的每一幅画中都装有我的血,这就是我的画的含义。
毕加索
印象中,画家似乎就是穷困潦倒、神志不清的代名词。
毕加索却是一个奇迹。
看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铁饼掷出的临界姿势造成一种行动前的紧张。这叫蓄势。
从巴塞罗那到巴黎,他潦倒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他住在巴黎〃洗衣坊〃,那是穷困艺术家聚集的地方。除了酗酒,就是作画。但是,他的〃势〃早已蓄到骨子里去了。他总是能够抓住最紧张的那一刹那,成为画作表现的焦点,也让自己成为人群的焦点。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刚刚24岁,一幅《拿烟斗的男孩》当时就卖到了30000美元。100年以后,这幅画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中,以104,168,000美元售出,成为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画作。
37岁的时候,与著名的野兽派画家马蒂斯举行联展。当然,那个时候,他也成了著名画家了。
他一生向往东方风情,研习西班牙民间绘画。
2005年年初,〃向毕加索致敬毕加索版画中国巡回展〃在上海开幕。他的绘画风致在〃遥远的东方〃引起了共鸣。
他高喊着〃让风雅见鬼去吧〃,以血和激情打破了美与丑的界限。从扭曲的人体器官里、从色块的杂乱堆积里,他都可以找到激情宣泄的渠道。也许,审丑才是他的本意所在。
有生之年,他的作品就被卢浮宫收藏,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他以63岁高龄加入法国共产党,还获过列宁和平奖章。
这个奇怪的男人。
14岁的那次静物写生入学考试,规定期限是一个月,他却只用了一天的时间。美术学院的大门就是为这样的快手天才敞开的。在校期间,他的成绩不是〃优〃,就是〃优上〃和〃特优〃。
童年时候,他非常喜欢一幅〃绘有鸽棚和无数鸽子的画〃,那是父亲画的。也许,后来的《和平鸽》就是童年记忆的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