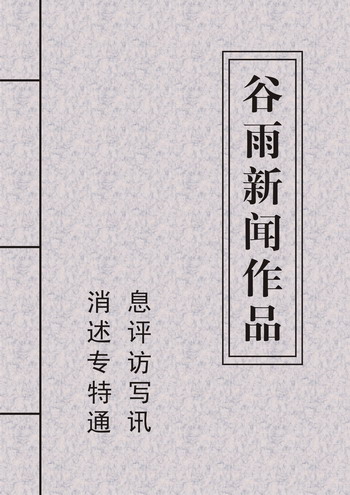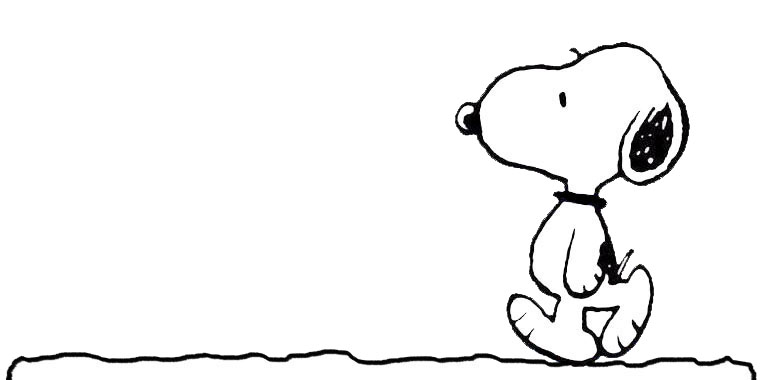博尔赫斯作品集 作者 博尔赫斯-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从1899年开始,伊斯曼不仅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成了一个重要选区的把头,向他管辖范围内的妓院、赌场、街头野雉和流氓小偷收取大笔孝敬。竞选委员会和个人经常找他干些害人的勾当。他订有酬劳价目表:撕下一只耳朵十五美元,打断一条腿十九元,用手枪打伤一条腿二十五元,身上捅一刀二十五元,彻底解决一百元。伊斯曼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有时候亲自出马执行委托任务。
由于地盘问题(这是国际法尽量拖延的微妙而伤和气的问题之一),他同另一个黑帮的头目保罗·凯利正面冲突起来。巡逻队的枪战和斗殴确定了地界。一天凌晨,伊斯曼越境,五条大汉扑了上来。他凭猿猴般敏捷的手臂和大棒打翻了三个对手,但是肚子上挨了两颗枪子,对方以为他已经毙命,呼啸而散。伊斯曼用大拇指和食指堵住枪眼,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自己走到医院。他发着高烧,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好几星期,但守口如瓶,没有举报任何人。他出院后,火并已成定局,枪战愈演愈烈,直到1903年8月19日。
里文顿之役
百来个同照片不太相像、逐一从罪犯登记卡上消失的英雄,浸透了酒精和烟草烟雾,头戴彩色帽箍的草帽,或多或少都有花柳病、蛀牙、呼吸道疾患或肾病,像特洛伊或胡宁战争的英雄们一样做不足道或者功勋彪炳,这百来个英雄在纽约高架铁路拱形铁架的影子下面展开了那场不光彩的武装斗争。起因是凯利手下的泼皮向一家赌场老板,蒙克·伊斯曼的同伙,勒索月规钱。一个枪手毙命,紧接而来的是无数手枪参加的对射。下巴刮得很光洁的人借着高大柱于的掩护不声不响地射击,满载手握科尔特左轮枪、迫不及待的援军的出租汽车接连不断地赶到现场,增添了吓人的气氛。那场战斗的主角们是怎么想的呢?首先,(我认为)百来枝手枪震耳欲聋的轰响使他们觉得马上就会送命;其次,(我认为)他们错误地深信,只要开头的一阵枪弹没有把他们撂倒,他们就刀枪不人了。事实是他们借着铁架和夜色的掩护打得不可开交。警方两次干预,两次被他们打退。天际刚露鱼肚白,战斗像是淫秽的勾当或者鬼怪幽灵似的突然销声匿迹。高架铁路的拱形支架下面躺着七个重伤的人、四具尸体和一只死鸽子。
咬牙切齿
蒙克·伊斯曼为之服务的本区政客们一贯公开否认他们的地区有帮派存在,他们解释说那只是一些娱乐性的社团。里文顿肆无忌惮的火并使他们感到惊慌。他们召见了两派的头目,吩咐他们必须和解。凯利知道,为了稳住警方,政客们比所有的科尔特手枪更起作用,当场就表示同意;伊斯曼凭自己一身蛮力,桀骜不驯,希望在枪头上见高低。他拒不从命,政客们不得不威胁他,要送他进监狱。最后,两个作恶多端的头目在一家酒吧里谈判,每人嘴里叼着一枝雪茄,右手按在左轮枪上,身后簇拥着各自的虎视眈眈的打手。他们作出一个十分美国式的决定;举行一场拳击比赛解决争端。凯利是个出色的拳击手。决斗在一个大棚子里举行。出席的观众一百四十人,其中有戴着歪歪扭扭的大礼帽的地痞流氓,也有发型奇形怪状的妇女。拳击持续了两小时,结果双方都打得筋疲力尽。一星期后,枪战又起。蒙克被捕,这次也记不清是第几回了。保护人如释重负地摆脱了他,法官一本正经地判了他十年徒刑。
伊斯曼对抗德国
当蒙克莫名其妙地从辛辛监狱里出来时,他手下一千二百名亡命徒早已树倒猢狲散。他无法把他们重新召集拢来,只得单干。1917年9月8日,他在公共场所闹事。9日,他决定参加另一场捣乱,报名参加了一个步兵团。
我们听说了他从军的一些事迹。我们知道他强烈反对抓俘虏,有一次单用步枪枪托就阻挡了这种不解气的做法。我们知道他从医院里逃出来又回到战场。我们知道他在蒙特福松一役表现突出。我们知道,他事后说纽约波威里街小剧院里的舞蹈比欧洲战争更带劲。
神秘而合乎逻辑的结局
1920年12月25日凌晨,纽约一条繁华街道上发现了蒙克·伊斯曼的尸体。他身中五弹。一只幸免于难的、极普通的猫迷惑不解地在他身边逡巡。
杀人不眨眼的比尔·哈里根
亚利桑那的土地比任何地方都更壮阔: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州的土地底下的金银矿藏遐迩闻名,雄伟的高原莽苍溟濛、色彩炫目,被猛禽叼光皮肉的动物骨架白得发亮。那些土地上还有“小子”比来的形象:坐在马背上纹丝不动的骑手,追命的枪声惊扰沙漠、玩魔术似的老远发出不可见的、致人死命的子弹的青年人。
金属矿脉纵横交错的沙漠荒凉而闪烁发光。二十一岁就送命的、几乎还是孩子的比来为人所不齿,他欠了二十一条人命——“墨西哥人还不计在内”。
早年
那个日后成为威镇一方的“小子”比来的人于1859年出生在纽约一个大杂院的地下室。据说他母亲是个子女众多的爱尔兰女人,但他在黑人中间长大。混杂在那些散发汗臭、头发鬈曲的黑孩子中间,满脸雀斑、一头红发的比来显得鹤立鸡群。他为自己是白人而自豪;但他也羸弱、撒野、下流。十二岁时,他加入了在下水道系统活动的“沼泽天使”帮。
在散发雾气和焦糊味的夜晚,他们从恶臭的下水道迷宫里出来,尾随着一个德国水手,当头一棒把他打昏,连内衣都扒得精光,然后回到下水道。他们的头目是一个头发花白的黑人,加斯·豪泽·乔纳斯,在给赛马投毒方面也小有名气。
有时候,河边一座东倒西歪的房子的顶楼上,有个女人朝过路人头上倒下一桶炉灰。那人手忙脚乱,呛得喘不过气。“沼泽天使”们立刻蜂拥而上,把他拖到一个地下室门口,抢光他的衣物。
那就是比尔·哈里根,也就是未来的“小子”比来的学徒时期,他对剧院演出不无好感;他喜欢看牛仔的闹剧(也许并没有预先感到那是他命运的象征和含义)。
到西部去!
如果说纽约波威里街拥挤的小剧院(那里演出稍有延误,观众就要起哄)大量上演骑手和打枪的闹剧,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当时美国掀起了西部热。西方地平线那面是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黄金。西方地平线那面是大片可供采伐的雪松树林,脸庞巨大、表情冷漠的美洲野牛,大礼帽和摩门教主布里格姆·杨的三妻四妾,红种人的神秘的仪式和愤怒,茫无涯际的沙漠,像海洋一样,接近时会使人心跳加速的热土。西部在召唤。那些年来,一种有节奏的声息始终在回荡: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占据西部的声息。1872年,早就跃跃欲试的比尔·哈里根逃出监狱,参加了到西部去的行列。
一个墨西哥人的毁灭
历史像电影导演一样按不连贯的场景进展,现在把场景安排在像公海一般力量无边的沙漠中间一家危险的酒店里。时间是1873年一个不平静的夜晚;确切的地点是新墨西哥州竖桩平原。土地平整得几乎不自然,而云层错落的天空经过暴风雨的撕碎和月光的映托,却满是拆裂的沟壑和峻峨的山岭。地上有一具牛的头颅骨,暗处传来郊狼的嗥叫和眼睛的绿光,酒店斜长的灯光下影影绰绰可以看到几匹高头大马。酒店里面,劳累而壮实的男人们用胳臂肘支在唯一的柜台上,喝着惹是生非的烈酒,炫示有鹰和蛇图案的墨西哥大银元。一个喝醉的人无动于衷地唱着歌,有几个人讲的语言带许多嘶嘶的声音,那准是西班牙语,讲西班牙语的人在这里是遭到轻视的。比尔·哈里根,从大杂院来的红毛耗子,在喝酒的人中间。他已经喝了两杯烧酒,也许因为身边一文不剩了,还想要一杯。那些沙漠里的人使他吃惊。他们显得那么剽悍,暴烈,高兴,善于摆布野性的牲口和高头大马,叫人恨得牙痒。店里突然一片肃静,只有那个喝醉的人还忘乎所以地在瞎唱。一个墨西哥人走了进来,身体壮实得像牛,脸相像印第安人。头上戴着一顶大得出奇的帽子,腰际两边各插一枝手枪。他用生硬的英语向所有在喝酒的婊子养的美国佬道了晚安。谁都不敢搭腔。比尔问身边的人来者是谁,人们害怕地悄声说那是奇瓦瓦来的贝利萨里奥·维利亚格兰。突然一声枪响。比尔在一排比他高大的人身后朝那不速之客开了枪。维利亚格兰手里的酒杯先掉到地上;接着整个人也倒了下去。那人当场气绝,不需要再补第二枪。比尔看也不看那个威风凛凛的死者,继续谈话:“是吗?我可是纽约来的比尔·哈里根。”那个醉鬼还在自得其乐地唱歌。
精彩的结局已经可以预料。比尔同大家握手,接受别人的奉承、欢呼和敬他的威士忌酒。有人提醒他手枪上还没有记号,应该刻一道线表明维利亚格兰死在他枪下。“小子”比来收下那人递给他的小刀,说道:“墨西哥人不值得记数。”这似乎还不够。当天夜里,比尔把他的毯子铺在尸体旁边,故作惊人地睡到第二天天亮。
为杀人而杀人
凭这一枪,“英雄小子”比来(当时只有十四岁)应运而生,逃犯比尔。哈里根就此消失。那个出没于下水道、专打问棍的小伙子一跃而成边境好汉。他成了骑手;学会了像怀俄明或者得克萨斯的牛仔那样笔挺地坐在马鞍上,而不像俄勒冈或者加利福尼亚的牛仔那样身体往后倾。他根本没有达到传说中的形象,只是逐渐接近而已。纽约小流氓的痕迹在牛仔身上依然存在;原先对黑人的憎恨现在转移到了墨西哥人身上,但是他临死前说的话却是用西班牙语说的诅咒话。他学会了赶牲口人的流浪生活的本领,也学会了更困难的指挥人的本领;两者帮助他成了一个偷盗牲口的好手。有时候,吉他和墨西哥的妓院对他也颇有吸引力。
他晚上难以入睡,聚众纵酒狂欢,往往一连四天四夜。只要扣扳机的手指还有准头,他就是这一带边境最受敬畏(并且也许是最孤独、最微不足道)的人。他的朋友加雷特,也就是日后杀他的郡长,有一次对他说:“我经常练射击,枪杀野牛。”“我射击练得比你更经常,我枪杀的是人。”他平静地回道,细节已无从查考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欠下二十一条人命——“墨西哥人还不计在内”。在危险万分的七年中间,他全凭勇气才混了过来。
1880年7月25日晚上,“小子”比来骑着他的花马飞快地穿过萨姆纳堡唯一的大街。天气闷热,家家户户还没有点灯;加雷特郡长坐在回廊上一张帆布椅子上,拔出左轮手枪,一颗子弹射进比来肚子。花马继续飞奔;骑手倒在泥土街道上。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