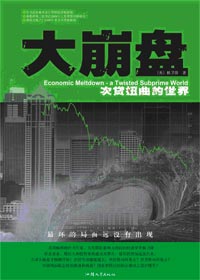平凡的世界 (卷三)-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半月二十天。
“这太慢了!”少安着急地叫道。
但没有办法,他只能回村去耐下心等待。
可是刚过三天,石圪节的信贷员就跑来说,他申请的贷款县农行已经批复了。信贷员惊
讶地对少安说:自他当信贷员以来,县农行还没有这么快就批复这么大宗的贷款!
孙少安心里明白,是根民给周县长打了电话,才如此迅速地解决了他的问题。现在这社
会,即是办正事,也得走旁门拐道!
这样一来,他就得立刻动身到河南巩县去提货了。临走前,秀莲连夜为他出远门而打点
行装。
到河南去!这对少安来说,也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在此之前,他最远只到过黄原。
现在,他将不仅走州过县,还要通过本省省城,到外省去办一宗大事。过去,都是河南人到
他们这带来做生意;而现在,黄原人也要涉足那个漂泊者们的故乡去了。
中国的大变革使各省的人都变成了不安生的“河南人”。如今,汽车、火车、轮船、飞
机,客员急骤暴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各地的个体户生意人。最有趣的是,大多数火车卧铺
的软席都被这些腰里别着大把人民币的生意人占据了。瞧吧,这些人穿着粗劣的西装,脖项
里挽着结死蛇一般皱巴巴的领带,操着醋溜普通话,蹬着脏皮鞋,理直气壮地踏进了铺红地
毯的软卧房间;而把许多身份优越的老干部挤到了拥挤不堪的硬卧车箱。干部有权,但权力
有限。人民币魔力无边,只要肯出高价,二道贩子手里有的是软铺票。至于软铺票如何流入
二道贩子手中,普通人只有想象的权力,以后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一九八七年,铁道部才不
得不发了一个专门文件予以限制——因为铁路上连外宾的软卧都不能保障了。
一九八二年夏天从黄原山区出发的孙少安,还没有这种气派。他仍然属于贫困地区那些
痛苦创业者的行列。他的装束在石圪节一带农民中间就算是很“现代”了,其实仍然是一副
土包子模样。他身上装着一点有限的钱,勉强可以去河南打个来回。当然,他已经远远不是
杰出的柳青所描写的那种五十年代的创业者形象,到外地办事还背着家里的馍,孙少安甚至
很有气魄地在个体商贩那里买了两条高价“红塔山”牌香烟,以备一路上应酬。
他在黄原没有停留。
他在铜城也没有停留。
他甚至在繁华的省城也没有停留。
他心急火燎,坐罢汽车,又坐火车,急迫地向河南赶去。制砖机提不回来,一切都无从
谈起!再说,那是一件万把块钱的东西啊!一点都不敢大意!
本来,他应该从铜城拐到大牙湾去看看弟弟。或者至少应该在省城停留一天,去看看上
大学的妹妹。说实话,正是弟弟和妹妹有了出息,才使他对生活更有了信心,以至于激发起
更大的雄心和魄力。他很想顺路见见这两个亲人,可又实在耽搁不起时间。看来只能在返回
时再去看望他们了。
少安是第一次坐火车。他找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听着车轮在铁轨上的铿锵声,出神地
望着车窗外绿色无边的中部平原。最使他惊讶不已的是,眼前竟连一座山也看不见了。啊
啊,世界上还有看不见山的地方?
列车喧吼着驶过辽阔的中部平原,在闻名天下的三门峡跨过铁路大桥,进入河南省。这
里的黄河已经很宽阔了。少安觉得,几年前他去山西丈人家买那头骡子时,也曾在一座大桥
上仔细看过黄河。不过那里的黄河水面很窄,桥也没这里长。想当年,他是骑着光脊背骡子
过桥的,而现在坐着火车跨过了这座更为壮观的大桥。那时过黄河,他是为了买头骡子;现
在他却是为自己的砖场买一台价值近万元的机器!
孙少安带着创业者的激情,一到河南巩县,立刻就办妥了制砖机的事。
等他返回省城,算了算时间,觉得制砖机几乎和他同时出发直达铁路终点铜城,因此无
法停一来去看妹妹,只好遗憾地即刻向铜城赶去。
现在,他连到少平那里走一趟的时间也没有了。从铜城把制砖机运回双水村,需要很快
在此地包一辆专车。可是他在铜城人生地不熟,到哪里去包车呢?
他突然想到了他们村的金光明。听说光明去年就调到这里,当了原西百货公司驻铜城采
购站的站长。
他费了好大劲,才在“劳动饭店”找到了金光明——原西的采购站在这里长期包着两个
房间。
金光明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看来不象个商业干部,倒象个大学讲师。他很热情地接待了
少安。尽管金家的人都对他二爸孙玉亭反感透顶,但这几年对他们一家人还比较尊重。这种
新关系最初的建立,应该归功于少平——我们知道,正是他利用给金光亮家的三锤补习功
课,才打破了金、孙两家将近十年的“三不政策”。
同村人突然相逢在异乡倒使两个人都感到十分亲切。当少安向他提出他的困难后,神通
广大的金光明二话没说,很快就跑出去给他联系好一辆车。
“正好,”金光明高兴地说,“我给我哥买好了两箱蜂,还发愁没个熟人捎回去呢。这
下咱俩的问题都解决了!”“那还有啥问题!蜂可以直接运回咱们双水村。”少安说。“先
还不敢运回村里!你先捎到原西城我一个熟人家里,这人是个养蜂行家,罢了叫我哥到城里
去,先学一学,再把蜂运回去。你知道,我哥没养过这东西,一下运回去,他老虎吃天,无
法下手!”
光明立刻给原西城他的熟人写好一封信,交给了孙少安。他然后感谢地对少安说:“你
还是有气派!敢弄这么大的事!我哥和我弟弟虽然生活没什么大困难,但钱也不宽裕,买化
肥常得我操心。归根结底日子要自己过哩!我给我哥买了两箱蜂,弄好了,也是来钱处。我
弟弟的情况稍好些,听说光辉媳妇在咱们村的公路边上卖茶饭,还有些收入……”“收入不
错!”少安说。
当天晚上,光明在另一间房里临时搭了个铺,少安就在这里睡了。
第二天,他坐在包车的驾驶楼里,拉着他的制砖机和光明捎给他哥的两箱子蜂,离开了
铜城。
他在黄原住了一个晚上。当天下午,他跑到东关去打问雇用一个烧砖师傅。原来的师傅
在他的砖场关闭后就走了,现在他不得不另雇人。烧砖是技术性很强的活。需要有个行家指
导——哪怕掏大工钱也得雇个内行师傅。
交运的是,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人——也是个河南人。不过,这人说不能马上跟少安起
身,得把他手头的瓦盆卖完才行。
少安一听说他卖瓦盆,心中不免有些疑问:他究竟会不会烧砖?他随即拐弯抹角问了这
人一些烧砖的事,河南人倒也说得头头是道。
于是,少安现场拍板,把他的住址留给了河南人;这人保证说,他过几天一定会及时赶
到双水村。
在黄原顺路办完这件当紧事,第二天少安就回到了原西。他先到城里卸下了金光亮的蜂
箱子,然后在中午前后回到了亲爱的双水村。
从离开村子到返回来,他一路上只用了八天。
他的返回对双水村来说,当然是一件大事!尤其是那些企图指靠他的人,一听说他回来
了,立刻兴奋地纷纷从金家湾和田家圪崂赶到了他的砖场。人们笑逐颜开地抚摸着他买回来
的庞然大物,把这钢铁家伙看成是他们共同的财神爷。田五在闹哄哄的人群中说开了“链子
嘴”——孙少安,走河南,买回个东西不简单,嘴里吞下泥疙瘩,屁股后面就屙砖!
众人的热烈情绪使少安深受感动。在生活中,因为你而使周围的人充满希望和欢乐,这
会给你带来多大的满足!
第十四章
几天之后,卖瓦盆的河南人不失前约,如期地来到了少安门上。
河南师傅一到,少安的砖场就重新开张了。他一下子雇用了村中三十几号人马,开始另
建四个大烧砖窑;同时开动新买回的大型制砖机,打制砖坯。
自实行责任制以来,双水村还没有过这么多人聚在一块劳动。村子南头这个小山湾里,
机器的吼叫和喧腾的人声不免叫人想起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场面。但今非昔比,这里不再有红
旗和高音喇叭,而是主要的是,这砖场属于孙少安个人,其他人都是来赚他的“工资”——
男劳一天三元,女劳一天一元五角。少安的媳妇贺秀莲,脸上带着出人头地的满足,既是她
丈夫的“副统帅”,又是给众人记工的会计。所有来这里干活的人,都是双水村目前的“穷
人”;有田家圪崂的,也有金家湾的。孙少安尽量满足了村里所有想来他这里赚几个紧用钱
的村民。有些家户的男劳还要忙自家地里的农活,他就让他们的婆姨和子女来上他的工。他
的行为大得人心,双水村有许多人为他歌功颂德。
他二妈贺凤英也来了。她还当着村里的妇女主任,只不过这职务早成了个名义。几年
来,她和她丈夫在村里都没什么“工作”可做。那光景依旧过得没楞没沿,她不得不屈驾来
侄儿这里赚几个买化肥的钱。少安夫妻不好意思叫二妈也和众人一样去刨土挖泥,只好让她
帮秀莲在家里做饭。
孙少安搞起这么大摊场,又雇用了村里这么多人,在东拉河前后村庄马上传扬开来,有
些邻近村庄没办法的庄稼人,也跑来想上他的工。他赶快婉言谢绝了。现在这么多人就够他
心惊胆颤的——一月下来光工钱就得开两三千块!实际上,他最多用二十几个人就够了,只
是因为同村人抹不开面子,才用了如此多的人——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人情和道义感,
而不是他有多大经济实力。
众人在这时当然不能象在自己地里干活,可以随便晚出早归,得象以前的生产队一样,
天明出工,天黑收工。
后半晌,那些从自己地里早归的村民,都不由纷纷串到这里来,蹲在砖场周围,观看少
安的红火场面,在这些旁观者中间,有时也能看见我们的孙玉亭同志。
热爱集体场面似乎是玉亭的天性。尽管他也知道,这场面和当年的农田基建大会战屁不
相干,但几年来他终归又看见了一群人凑到一块劳动的场面,不能不使他触景生情,唏嘘感
叹。有时候,在这纷乱的人头上空,他恍惚看见一面面红旗在风中招展……别了,往日那火
红的岁月!
孙玉亭蹲在侄儿的砖场边,吸着从他哥烟布袋里挖来的旱烟,心绪烦乱地思前想后,不
时用手指头把流在嘴唇的清鼻涕抹在他的破鞋帮子上。世事变了,他还是一副穷酸相,一身
破烂衣服,胸前的钮扣还是缺三掉四,旱烟照样由他哥供应。要不是大女儿卫红已长成个懂
事姑娘,相帮这对“革命夫妻”种地,一家五口人恐怕连口也糊不住。这不,凤英现在也只
好投在“资本主义”门下,赚几个“下眼”钱。
玉亭不仅光景没变,其它“爱好”也没变。他一直不间断地到小学教师金成那里取来报
纸,抢着赶天黑看完(晚上他点不起灯),如此关心“政治”的人,至少在东拉河一带的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