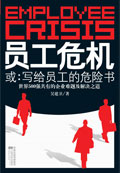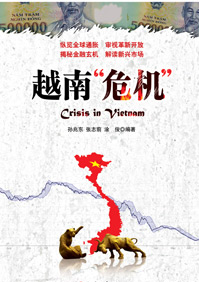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争,而麻生野就是支持这一斗争的团体的领袖,所以,我们的性关系并非是建立在健全的心
理基础上的呀。我本来就不是认真进行斗争的,后来是因为迷上了麻生野,所以才去参加集
会呀。不过,我也为自己辨解:我迷恋的不是一般的女人,而是在麻生野的风韵面前倾倒
了。”
“她倒是有风韵的。”
“是呀,我就是被她的风韵所迷,才发展到性交的。可是,到了动真格的时候,却像搂
住对方的松弛的地方性交了。这第一次性交是有原因的,我和她性交时头一次体验到了阳萎
的可怕。
我们的孩子们现在已经把对方的存在彻底从意识中消除了,但又以自己的动作配合着对
方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在破纸上画出密集着许多小点儿的图案,像一对离不开的共牺类动
物似的玩耍着。不论是森的父亲还是我,在我们的孩子身边,谈论起有关性的事,都是没有
必要避讳的。森的父亲在后一个集会上,心里一直惦记着酒后失态的麻生野樱麻,那天夜
里,不知为什么,经常围在她身边的那些被人们称为保镖的青年一个也不在,也许是麻生野
派他们去送西班牙诗人了。麻生野在完成了长时间的连续演讲之后,如释重负而喝醉了,她
让那位作家洗脚的消息早就不胫而走,这消息使森的父亲下了决心去照顾她。于是,当清晨
到来集会结束时,森的父亲扒住了麻生野乘坐的出租汽车。不料,汽车刚刚跑起来,麻生野
就说她恶心,只好驶进路旁的汽车旅游旅馆。虽然自从开展斗争以来森的父亲就常常见到麻
生野,但是两个人关在一间旅馆里还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当森的父亲看到未来的电影家在
浴室里收拾完呕吐的污物,恢复了精神时,他感到这时应该开始性交了。这是森的父亲硬要
如此说的,他说得很简单,最初五分钟性交进行得倒很顺利,因为在和她同样酒醉了的森的
父亲的扁圆形记忆里,麻生野的面容就像运动会上奋力拼搏的争强好胜的童女。但是,当那
光辉灿烂的五分钟过去之后,性交变成森的父亲的独角戏时,质量立刻下降了。
森的父亲讲话时的样子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森的父亲也有同龄人所有的进了理科就轻蔑
文科的那股劲儿(我们的青春是在原子弹使我们战败、都却又达到了汤川博士①获得诺贝尔
奖的科技至上时代中度过的啊),而且,他表里如一,对于写东西的人的想象力和驾驭语言
的能力,一律不分青红皂白地吹毛求疵。他在默默之中仿佛在说:
①汤川秀树(一九○七—五九八一)东京大学教授、物理学家、因在理论上解决了
中子问题,一九四九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包容译注
“我要把你当做从我的下意识的整体性为光源的幻灯机的放映幕布,映出连我自己也不
识真面目的我。也就是要把仅仅是感受到的支离破碎的预感或者梦想,在你的幕布上拚凑起
来,成为清晰的图像。难道作家的想象力和语言技巧的锤练首先不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的
么?”
这当儿,我和森的父亲都注意到我们的孩子们默不做声,局促不安,仰着脖子,好像憋
得不知所措了。带他们一进洗手间,我们的孩子们就在那洋式便器的两旁一齐排起尿来。因
为憋了好半天,阴茎像蝮蛇头似地勃起,这一来尿就四处飞撒,把他俩的腿上和我,还有森
的父亲的裤子都弄湿了。
“半夜里换尿布和把尿是我的事。可是,看见儿子的阳物挺得那么硬,怪吓人的。”
“我也有点儿怕呢。不过,我却因此产生了两种思想。一是我们的儿子下生时头盖骨上
有一个洞是宇宙的说服者对我们人类进行监视的措施,当我们在半夜里赤裸地面对死亡的念
头时,儿子那硬得一塌胡涂的阳物不正是接收说服者的信息的天线么?那信息就是遗传基因
子的密码,存储在儿子的细胞里了。有朝一日,所有的密码将会得到解释,成为情报,笼罩
东京的黑暗的夜里,有一个小小的亮点儿出现在宇宙说服者的望远镜里,那就是坚挺的阴茎
天线在激烈地颤抖啊。低级昆虫常常为了供奉高级昆虫而献身,我们不是也这样替他们换尿
市,取下尼龙布,然后换上新的尿布,一一按上按扣的么?哈哈!”
“还有一种思想是什么?”
“另一种?……那就是我和麻生野性交时已经出现了症候,我正在阳萎呀,可是,儿子
却白白地硬起来,令人感慨呀……”
那天,作为另外一位来客的森,一直沉默着。但是,到了最后,他却叫了起来。森的父
亲因为撒尿弄脏了洗手间,很不过意,我对他说不必介意时,露着起鸡皮疙瘩的屁股的森既
刻板而又准确地责怪他说:
“不行啊,这样到处乱尿可不行啊!”
6
一方面因为来我家的森的父亲对我妻子没表示好感,另一方面森的母亲带孩子上学时又
讲起麻生野和森的父亲如何保持那种恶劣的关系,所以,妻子也不可能对森的父亲表示什么
好意了。不过,也不能因此就认为森的母亲得到了我妻子和那些母亲们的同情。森的母亲频
频对那些人搭话而当对方要回答时,她就十分粗暴地横加打断,继续讲她丈夫和麻生野如何
密谋之事,对方只好再忍下去。直到对方等到开口的机会时,她却低下头来直打哆嗦,不肯
听了。
“她长了一双斗鸡眼,盯着小鼻子头儿,嘴唇边净是汗毛和粉末!”我妻子向我描述那
位夜间酒吧里工作的寡妇似的母亲说。
森的母亲皮肤浅黑,像粘着颗粘状的油烟,唇边生着许多汗毛,说话时嘴角冒白沫,干
了就像白色粉末。因为对于那些希望倾诉一下自己的处境的我们的孩子们的母亲来说,没有
比森的母亲讲话时再蛮横无理的了,所以,这样的评语里含有恶意,也就不必责备了。
且说,有一天,带儿子一同去参加购物实习的妻子比原定晚回来了一小时,她抑止不住
兴奋,说出了对森的父亲的敬意。连我儿子也揉着他那发红的面颊,一遍又一遍地这样说,
当然,那是我妻子口授的了。
“了不起的人呀,科学家,了不起呀,科学家!”
我们的孩子们在男女两位教师的带领之下,出发到“购物”的现场去了。家长们离他们
五六米在后边跟随着。这种“购物”课是让那些会付款买东西的孩子随意买一件东西,而让
那些不会的孩子学会走进商店门。
那是一家有自动门的自选市场,偏偏就是那个自动门,挤住了一个小班儿的男孩子的胳
膊。被挤住的恐惧超过了疼痛,那孩子拚命地嚎叫。那平素绝对稳健的男老师自不待言,就
连日常勇猛善战的女教师也拿不出一点有效的措施。自选市场的店员也是一样。可是,谁也
没想到,那位离开母亲们不远、常常爱用斜眼看人、爱搭不理的森的父亲却采取行动,把孩
子从自动门上救了下来。
“当一切郁结束时,在自动门旁散落了许多盛在塑料盒子里出售的工具、星期日木工用
的木料和毡子,那是森的父亲找遍了整个自选市场才收集起来的,刚才弄那自动门时从他的
袋子里接连掉出来了。自动门从门框上拆下来了,电源也切断了,那孩子被救出来时胸前一
片血红,不过,那是森的父亲拆卸自动门时为了避免孩子受伤,把自己的左臂伸进去受了伤
而流的血。
第二天,学校为了向当时不在场的家长说明事故情况,并向森的父亲的献身精神表示感
谢,开了一个反省会。虽然妻子再三请我去,我却没有出席。因为我估计到在校长和教务长
都出席的反省会上可能发生一场骚乱。果然不出所料,过了中午,妻子从特殊年役专用的电
话里传来了消息,森的父亲把校方和家长们都当做对立面争吵起来,不肯罢休。孩子在那可
怕的氛围中又饿又怕,所以叫我去接,而她则打算把争论听到最后。妻子说时又冷静又兴
奋,真怪。
当我走进学校时,只剩下几个父亲和母亲把自己的孩子搂在身边,聚集在教室的后部,
活像一小撮难民。看来我们的孩子们早就因为家长们也感到饥饿和争论的难以结束而茫然
了。只有森的父亲一个人站在黑板前胡扯,校长和校方的人员们委屈地坐在孩子们的木椅
上。我走进教室就被校长盯了一眼,那是处在胜败难分的节骨眼上投给一个不知是敌是友的
出场者的目光。在有点寒意的教室里,只有校长面红耳赤,大脑袋上直冒热气。大概他就是
森的父亲攻击的靶子了。那位总是充满自信的女教师的颧骨上通红,她用愤恨的目光瞪着森
的父亲,另一位班主任男老师在低矮的木椅上深深地弯曲上身,好像向森的父亲求饶。
“……我们的孩子们应该摆在学校集体的中心位置上!我并非如同刚才校长故意曲解的
那样要统治那些不是我们的孩子们,而只是要求放在中心位置上!否则的话,学校将失去了
接受我们的孩子编成特别班的意义了,我们的孩子们来到这所学校,去自选市场去学‘自动
门是危险的’,那又有什么益处?我听说,当孩子被自动门夹住胳膊时,不但自选市场的人
员置之不理,就连带队的老师也不肯救助,这像什么话?在事故发生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的
孩子们的记忆里,只剩下黑乎乎的一片恐惧,再也没有别的了!果真我们的孩子们在这间教
室里学一些必要的课程之后就能走上社会么?面向那些毕业后走上社会的孩子们,教师们能
够提供的真正的援助应该是教给他们:你们将要生活下去的现代社会是这样的,你们要对某
些事物留神!我看应该教他们这些。这是可能的么?教师们能够对我们的孩子们做到这些
么?现在,这里所教授的,不是只要求我们的孩子们将来生活在社会的角落里充当一名不大
惹麻烦的混蛋,料理一些身边琐事。如果在将来的社会里,这一种体系被合法化,那么我们
的孩子们不仅要学会料理身边琐事,而且还要学会料理整个自己,也就是,哈,哈,也就是
学会自杀了。如果真为我们的孩子们着想的话,那就要为了击退未来社会的那种淘汰的力
量,就得教给我们的孩子们独立武装自卫!也就是说,现代世界正在受到污染,既然如此,
像我们的孩子们那样的孩子的人数社会飞跃上升,如果一旦增加到比比皆是的地步,形成未
来世界悲剧的前兆,那就变成民众憎恨的众矢之的了。也就是变为弱小民族和受压迫阶级都
不得不在它的威胁之下生存下去的仇恨的对象了!虽然也有已经站起来了的民族和阶级,但
是,在这个班级里教导过我们的孩子们自我保护的方法了吗?”
“这种事靠学校根本办不到!难道不是这样么?你说将来还要为特殊班级毕业生划出独
立地区,里边还要拥有原子弹,这已经是语无伦次了。但是,那不是恰恰背离了学校教育的
宗旨了吗?我认为教育就是教导学生在身心两方面都与自然和社会和谐。我作为校长,特别
是以体育为专长的校长,多年来就是这样认为,并且也是这样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不要求为了反抗淘汰他们的力量而教给他们自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