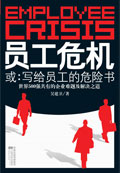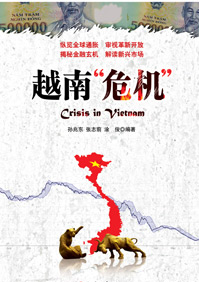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第3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啦。因为在色彩斑斓的世界的人们的眼里,我们是“看不见的人”,所以,我怕那些要踢烂
我的睾丸的那些家伙确信我不敢见人,所以就把那些凶残的行为视若平常了。
①Jean Cocteau一八八九—一九六三,法国诗人、剧作家、电影家。
②jean-Paul Sartre一九○五—一九八○,法国文学家、哲学家。
且说我和“志愿调解人”成了俘虏,被带进写了许许多多字的屋里,万幸的是十八岁的
水灵灵的睾丸平安无事,哈哈。那屋里的窗钩用铁丝拥住了、玻璃被木板蒙住,而且用胶带
粘了缝隙,屋子的正面靠里边的地方,摆着两把木椅,我们被命令坐下。他们在什么时候准
备了如此严密的监禁室呀?如果是日常工作的查讯室,又令人觉得太阴森了。我们勉强从打
肿了的鼻孔里出气,顺从地坐着,可是,进屋来看俘虏的人们不住地往后退,终于把靠在墙
上的二、三十根钢管碰倒在地板上了。我和“志愿调解人”同时听见有人哎哟地叫了一声,
用我们流血的耳朵。据说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有所谓专供观赏的拷打,我们就要遭到钢管的
专供观赏的拷打了。
而且,就连控制自己不要哇地一声叫出来的力气也没有了。其实,当我们作为俘虏被带
走时,就不再受到粗鲁的待遇了。起码避免了只伤内脏不伤皮肉的、上百回的钢管的捅撞,
那是高级技术的拷打呀。因为我们不仅是俘虏,而且是受到某种怀疑的身分啊。而且,那也
是沾了“志愿调解人”被打倒在地、踢来踢去、却仍然以铁一般的意志表达的语言的便宜
啊。他能从两肋到睾丸到处都遭到踢打的情况下表达了我是“大人物A”的袭击者的近亲、
而那位勇士又是“志愿调解人”所要隐匿的人,也真够了不起的了。因此,我和“志愿调解
人”在那些静观今后即将发生什么的人们的面前的确是不折不扣的俘虏;但是,同时也是纪
念“大人物A”遭到半歼灭大会的贵宾呀。
那些默默地看着我们的人,与其说是革命党派的活跃分子,倒不如说是已经倒退为被动
地期待着今后可能发生的情况的孩子了。如果找来三十名婴儿,不是很难分辨么?只要不是
像我们的孩子们那样的婴儿。哈哈。和那一样,那些头戴盔帽、用手巾蒙面,只露出眼睛、
鼻子的家伙们也无法辨认。当我被他们踢倒在地之后犹且不肯罢休地踢我时,我心想一定要
报仇。虽然他们是以组织的成员身分干的坏事,但是,暴力是通过个人的肉体表现的,所
以,我要向那些个人还以暴力,我心中燃烧着仇恨。但是,我已经想不起来是哪些人干的。
悲伤和浑身的疼痛交织在一起了。
“志愿调解人”既然向那些人表示了他的意见,在他的意见被转达到领导部门并且得到
答复之前,他似乎决心一言不发了。如果在踢打之下被迫说话,那就是对自己采取的态度的
背叛了。我对“志愿调解人”更加钦佩了,我也不想用破了皮的、肿了的嘴唇说话了。旁观
的人们也完全沉默了。但是,他们是期待着即将开始的对间谍的私刑和欢迎勇士的大规模的
祭典啊。虽然他们沉默时露出孩子似的眼神,可是内心倒满充实啊!
而且,沉默的他们,仍然下意识地发出了信息。那就是臭味儿啊,哈哈。初春的下午,
在暮色将临的大建筑物里,那熏人的臭味儿冲进变凉了的空气里,他们怀着怎样热烈的追求
才疲于奔命得到了连洗洗身子的闲暇也没有的地步啊?我只能感叹不已了。
一会儿,一位领导用双手拨开那些人走了进来,显然他害怕那股臭味儿,不加掩饰地表
现了出来。他当然不戴盔帽、不蒙手巾,就像刚才那个党里的小官僚的复制品,穿着朴素的
西服,是个有点儿肥胖的中等个子。他在我和“志愿调解人”前边坐下,故意摘下眼镜来
擦,皱着眉头苦思冥想,然后,主要朝着“志愿调解人”,用沙哑的声音低声说道:
“你的情况,我知道。不过这个年轻人,是你的什么人?是徒弟?……我想直接问你,
你是什么人?你是谁?相当于我们的战士的什么人?”
刚才一直默不作声的在背后那些人(就连踢我们时也没喊叫)哄堂大笑,好像他的问话
里蕴含着精彩的幽默似的。我在他们那愚蠢的、没有来由的笑声当中,确定了方针。我决心
对那家伙说,我是森的父亲、“转换”了的森是我的同志,我作为同样也是“转换”了的
人,协助森开创的事业。如果连这个小官僚也不肯承认“转换”的事实,而硬要把我当作森
的堂弟以抬高他自己的话,我就预感到不能完成赋给我和森这个“转换”了的一对儿的使命
了。我尽力在想,要不要叫他们永远把森称为我们的战士。
“我认为你们使用我们的战士这个词儿是不恰当的。因为你们连袭击‘大人物A’的人
的名字也不知道啊。他的名字是森,而以他的名字为轴,我也有了称呼,我就是森的父亲。
我一向是依靠他的,因为我就是森的父亲呀。”
“他所说的父亲,请你理解为一种比喻吧。”在我身边的“志愿调解人”介入了,肿胀
的嘴唇笨拙地吧嗒着。他可真是天生爱介入的人啊。
“我的话里根本没有什么比喻的意思。”我冷冷地把他的话顶了回去。在我和森的一生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上,哪里还有闲心使用比喻的字眼儿啊?我们已经到了“转换”的最后阶
段了。“转换”这个新词作为占卜人类未来的语言,马上就将风靡全球了!如果你们也是肯
于考虑革命的人的话,就请注意这句话吧。……你们知道袭击‘大人物A’的是一位二十八
岁的人么?”
“你胡说些什么呀,”审讯官满脸困惑,背后的人们哄堂大笑。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话
了。“……袭击‘大人物A’成功之后,我们收到了战绩报告。”
“那么,你们也知道他是二十八岁的男子汉吧。他是森,我虽然是十八岁的身子,却是
森的父亲!如果你们不能理解这个‘转换’的事实,也就不可能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了!”
“建设性的对话就不必要了。我只想问你是谁?你是谁?当然也可以采用其它方法来讯
问,你不是已经遭到了足够的踢打了么?那么,就合情合理地进行吧。你,是谁?”
那个小官僚说是讯问我,而事实上他却是在煽动他背后的战士。在他的话的断句处,战
士们都填补上柔顺的笑声。
“刚才我说过了,我是森的父亲。而且,和那个好像是你们的党派里的女学生一同去袭
击‘大人物A’的就是我儿子森!在我这方面,从一开始就希望合情合理地办事呀。”
“我的头脑不好,所以整理了一下基本的数字。你十八岁,你的儿子二十八岁?那就是
你儿子十岁时你才下生,你是怎么生出来的?难道是你儿子做疝气手术时,从他的睾丸里生
出来的?”
我从他的构思当中意外地发现他把我的下意识当作幸运的事情了。而且,我看出这位有
点儿肥胖的中等个子讯问官虽然外表装作平庸,但他绝不鲁钝,所以,我静等那些哄堂大笑
的战士们静下来。
“我三十八岁,是八岁的森的父亲。如果你想掌握基本的数字,就由这里出发吧。后
来,我和森发生了“转换”,我返老还童变成二十岁,森也成长到二十岁了。这不是很简单
的算数么?”
“因为革命家反对任何歧视,所以,我这句话也并不是为了歧视才使用的。你是‘癫
痫’病?由于这种病才头脑出了问题?当然,我们作为革命家,对精神病患者一般是不歧视
的……”
“那并不是你所谓的措词不当而造成的下意识的错误,而是你十分清醒的神志造成的歧
视。我是受过某些歧视的呀。我想让你们明白的是很简单的事呀,如果你们还有理解的精神
的话!森为了他的事业的初步成功,带着你们党派里的女学生走了。但是,要实现他的事业
就必须实现‘转换’的使命,在这一点上,它才具有意义。这和你们的党派对敌对的党派所
做的歧视的姿态是没有关系的。森不是你们的战士!……直到现在,你们对‘大人物A’也
没做出明确的评价吧。你们宣称‘大人物A’为了赞扬袭击者而召开大会,可是你们至今还
没有关于‘大人物A’的评价?对于你们来说,‘大人物A’实际上是什么人物?他为什么
必须遭受袭击?如果你们已经认识了这个道理,为什么在森动手之前你们不去干?”我如此
据理陈词时,一直盯着讯问官的眼睛,因为有句老话说要靠毅力制服狗,就得死盯住它呀。
哈哈。他那圆鼻子头的周围好像忽然充血,不知在什么时候用偏振光镜排除了我的目光似的
露出了满脸冷漠。也就是对我今后即将遭遇的惨事的冷漠。与此同时,他身后那些笑得没劲
儿了的人们却一致向我表示了敌意。他们一动也不动,从身上冒出强烈的臭味儿,仿佛马上
就要抓起钢管,给我身上戳出上百个内出血的血斑来。
“你们不要挑拨森的父亲,也不要煽动年轻人啦。”“志愿调解人”机灵地进行他的专
职工作了。“森的父亲确实是袭击‘大人物A’的那个人的亲人。至于他怎样想,就凭他去
想好了。只要那想法对运动有利……森的父亲可是有用的人呀。因为你们虽然能够瞒哄官方
把森带进大学,但是,他发言时需要森的父亲当翻译呀。森的父亲是唯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
人啊!”
“战士森,来到大学里了。”讯问官若无其事地说道。“他说话时,头部的创伤确实产
生震动,所以,演讲时恐怕需要人帮助的。……战士森确实克服困难完成了义务,可是他沉
默寡言啊。”
“没有反对意见!”一阵强烈的共震,震颤得覆盖着木板的玻璃哗啦哗啦响。
我觉得那个发出像钝器似的粗笨而又沉闷的声音的、由于用力过猛而目光呆滞的战士是
个无法忍受的卑劣的家伙!而且,……特别是因为我出于十八岁的鲁莽,终于对那个引诱青
年的、而且是利用森来做那事的小官僚遏止不住愤怒,顾不得脚下蹒跚就向他打去!
“把我的森还给我!”我尖声尖气地喊叫。“我不许你们把森叫做我们的战士!把森还
给我!”
可是,我把话全都喊完了么?我的拳头指向的目标的那颗人头霎时间低下去了,从他两
旁跳出两个相似形的机器人,把我给掀到一旁去了!我的后脑勺撞在覆盖玻璃的木板上,证
明了那木板的有效性之后,滚倒在地板上了。虽然没断气,但是,我充分地体验了疼痛,我
佯装昏迷不省了。这种士兵的暴力和湄公河三角洲的电影一样,除了在不高兴的脸上现出的
厌恶之外,仿佛在能量的源泉上还有不可抗拒的庞然大物呢。
4
我保持了一会儿这种佯装的昏厥状态,……因为在别人的眼里那和人事不省是等价的。
哈哈。但是,我能够未被刻薄的或者执拗的检查发现我已恢复神志,从而再次真的使我昏迷
而且陷入可能被打杀的绝境,那多亏“志愿调解人”的足智多谋了。“志愿调解人”准确地
判断了情况,并且迅速地采取了行动。他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