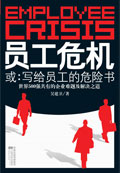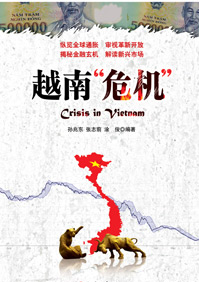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褶的左眼已经失明,眼睑里边黑乎乎的,所以,即使另五只眼睛因为疑惑或者愤怒而目光闪
烁时,它也常常留下深深的阴影。好像那一双眼睛能够轻易地测量出对方的肉体和精神的总
量,却不能表示出它的答案。
说到这里,难道我还不是敬畏“老板”的吗?如果你忠实地记录了我的语言,那么,已
经写下的语言本身不就证明这一点吗?
我在那天深夜,一边等候森和那个女学生,一边用电饭锅烧饭,我炒了咸牛肉和洋葱,
但是,当我独自吃起来时,才注意到那咸牛肉罐头也是“老板”新年礼物当中的一份,是今
天袭击时,正在吃午饭的笨蛋秘书发给我的。哈哈。每一个提供简报的人,他都一律发给
了。由此可见,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到处都有“老板”的影子啊,所以,在“老板”遭到
袭击的那天晚上,他的事怎么也不肯离开我的头脑,也是很自然的啊!但是,如果是这样的
话,我的“转换”了的精神生活本身不也不知不觉地受到“老板”的影响了吗?我只吃下所
做的夜宵的三分之一,因为在这当儿,我的胃翻腾得厉害呀。我一想到在老板的影响的无意
的波及之下,我成了受他支配的人,不由得联想起在巴黎公寓的亭子间里踩着高高的床铺上
吊自杀的朋友来,他的尸体像幻影似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他刚开始的时候不是也不能理解老
板的整体构想,把老板当作国际关系的外行而藐视,却又自相矛盾地对他的存在的本身怀着
畏惧和敬爱之心,再加上对经济上的耽心,才努力向老板讨好,搜集情报,归纳起来递交的
吗?后来,他逐渐深入了,深入到连我也不懂的老板的全部构思的深度里。就是这个他,直
到古巴危机时他才想到了老板的真正的意图,醒悟了他一直协助老板干了哪些事,而且是无
可挽回的了。那是对和他一同在普林斯顿进修国际政治的法国人妻子也不能挑明的事呀。他
首先想到必须和老板结束这种关系了。他开始对提供情报——更确切地说是提供简报——怠
工了。老板来到巴黎时,他俩当面对质。但是,这次对质在第三者看来只是一方蒙受训斥,
精疲力竭的他已经没有精力再去寻找合适的地方,便在床边吊死了。那间公寓是他的全部财
产,被遗留下的夫人,不得不继续睡在那张床上!
凌晨两点,电话。又是那位女学生,不知从什么地方打来的,用傻哩吧叽的女学生语
言、自鸣得意地送来了她作为活跃分子武装起来了的消息。她怀疑我家的电话已被窃听,想
得倒周到,这个连屁股沟子前边都让人偷看的粗心的家伙。
“喂,喂,爸爸们在监视着,不能靠近车库,咱们暂时不能在你家见面啦。我们俩干了
那事,你生气么?那是自然的啦。不过,那叫什么?那只是应酬呀,真正的要和你干呢。这
也是命运吧?那样一来我什么也不能做了。妈妈来了,请多关照,多保重!”
原来是森和那个女学生袭击了老板啊!本来对森去袭击时甩下我是很有意见的,却被作
用子几句话就立刻说服了。不过,那是什么意思?她说不过是应酬,真正的要和你干呢。那
是命运么?今天森仅仅是去给“老板”发出警告的,而在实现使命时森要和我作为“转换”
了的命运的共同体两个人一同去的。所以,今天被留下来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宇宙精神要命
令袭击“老板”呀?不过,既然要在森的领导之下实现这一使命,我也就没有问题了!
电话的意思是警察现在正在监视我的家,邻居家的车库对着我家的门敞开着。女学生的
话很有说服力地反映了她对走过我家门前的陌生人的观察。当电话被单方面挂断以后,我立
刻要熄灭起居室的电灯,但是,我猛然一惊,没有熄灯。我强忍着没去从窗帘的缝隙往外窥
视,因为如果让监视的家伙把刚才的电话当作秘密联络就麻烦啦。
当然,我也并不认为那是森和女学生暴露身分之后来张网捕人的。因为如果是那样的
话,他们就会痛痛快快地拿着逮捕令来强行搜查了。有人不是针对森和女学生,而是准确无
误地针对我向警察告密了啊。警察大概对那情报半信半疑,所以才在这里监视。也许是森和
那女学生本人,或者是把他俩送到我家来的那些人,敏感地发现了警察的踪迹,才逃过这一
关的吧。
是谁检举我?当然是我妻子,也就是前妻!她从电视上看到“老板”遭袭击的新闻,然
后就把它和我联系起来,这不是很自然的么?然而,我为森和那个女学生或者他们的护卫们
能够巧妙地逃脱根据我妻子、也就是前妻告密而布下的罗网,并且因此收到使森和那个女学
生能够在今后我妻子、也就是前妻的告密情报中避开警察追究的效果而欢欣鼓舞。而且,一
经证实了袭击“老板”的是森等人所为,我感到事过将近十年,我和那个挂在巴黎市街上很
高很高的地方的朋友的尸体总算找到了和解的头绪,至于我刚才还向他表示敬畏的“老
板”,我仿佛看见了他又恢复了那副凶相和倒在血泊之中的幻影。十八岁的善于多变就是厉
害呀。哈哈。虽然我只惦记森负伤,可是那女学生不是像唱歌似地说:请多关照,多保重么?
等了二十分钟以后,我熄了寝室的电灯,然后不去我自己的床,却在森的床上把脚伸到
栏杆外头睡着了。在天明之前有好几次我感到马路上有人的动静而醒来,大概警察真在监视
吧。我被麻生野集团的上层组织视为间谍、被它的反对党派当作对立面的支持者,而且妻
子、也就是前妻和她的巨人族弟兄们,也很可能为了发泄生活上的宿怨而趁我熟睡时袭击
呀。不过,我家门前有警察监视,这对我倒是最安全的保护啊。人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境
遇,如果你们作家不能从各种角度看世界,就不能洞察一切。譬如,没有我这样滔滔不绝地
吹嘘、你那样老老实实地记录的配合就不行啊。哈哈!
4
具有尊重人权精神的警察给了十八岁的我足够的睡眠时间之后,以两位绅士的面貌出现
了。那个根本不讲什么人权的大喊大叫的告密人正是我的妻子,也就是前妻啊。哈哈。我一
睁开眼睛,就精神百倍地准备和官方抗争。因为森已经着手实现了宇宙精神赋予他的使命,
我这个也应尽快参加那场斗争的战斗员同志怎能自甘落后啊。首先是清晨的洒扫,当我把家
里所有的窗户全部大开时,看见四五所房子以外的地方停着一部车。这一带的路上是禁止停
车的呀。然后又看见邻居家车库的屋檐下有一名闲得无聊的长发族在早春的晨风里冻着,他
直跺脏兮兮的长筒皮靴的后跟。他那长靴和全身的打扮,表明他是生活得疲惫了的长发族,
比街上司空见惯的长发族味道更足。哈哈。不过,一会儿就听到铃响,我到门厅一看,站在
那里的并不是那些监视的人,而是全身制服的两名警察。一个是全局柔道大赛的冠军似的美
男子;一个像是去年年底因为结核病请病假、现在是春天了所以又跃跃欲试的人。显然是把
高压派和怀柔派两种战术做了分工,不说我也明白。但是,“高压”直接点了我的名,“不
在家么?”他这样一问,“转换”后的我就心中有底了。
“舅父舅母昨晚没回家。舅母好像前,前一个晚上就没回来。他儿子也在这儿,舅父带
走了。前、昨天的昨天的晚上,好像出了点乱子,所以叫我来看家。现在出了什么事么?我
是这个家里的人,告诉我吧。莫非是舅母、或者舅母的兄弟又割了舅父一刀?”
“您是他外甥么?……给他看家?你再说说,你舅父为什么被人家割了?”
“嗯?”诱供!
“我在严肃地和你谈呀。”“高压派”插进来了。“你舅父昨晚一直未归,到现在也没
回来!和你联络过么?”
“没有联络。请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吧,我真是他们家的人。”
“你看电视看得太多了吧?”“怀柔派”一边说着,一边露出了判断的神色。我虽然有
些胆怯,但是,他好像把我错当做头脑欠佳的小鬼了。“不,因为有人来找你舅父迷了路,
我们是带他来的。既然你舅父舅母有的动刀、有的挨刀,那就快些送去吧。哈哈哈。”这不
是诱供,是向善良的、健全的市民发出的协助请求啊。哈哈哈。
这时,在退让了一步的警官中间,(从前的喜剧电影不是演过消防队员破门而入的场面
么,就像那样)走出了志愿调解人。
重新在近处看看他,他那黑得发青的皮肤简直令人想问
“是否还活着?”可是,他的整个脸上,不仅没有垂死般的颓丧,反而使你一眼看去就
对他那蒙着黑得发青的皮肤的宽宽的前额、三角形的鼻子和口须,都产生好感。就在这时,
他把方形的黑色眼镜架向上捅了捅,在他那真挚的眼睛里露出惊讶来。仅此一点,就使我明
白了“志愿调解人”是代替森和女学生来联络的,虽然他也许在森那里听到了有关“转换”
的说明,但是,当他来到这里亲眼目睹我这个“转换”后的人时,他却禁不住惊讶和迷惘了。
“在府上的杜鹃花丛里,小猫产仔啦。”这位“志愿调解人”不事寒暄地说道。“今天
天气暖,倒不要紧……”
当然,警官要把他的话当做暗号了。那位“高压派”立刻走到“志愿调解人”身旁,牵
制他的下一个暗号。经验丰富的“怀柔派”则已经去检查杜鹃花了。但是,遗憾的是他不得
不赶快躲开呼地一下子怒吼着窜出来的桔黄色带斑纹的猫爪子的攻击。“不要惊吓它,它如
果觉得危险,就会把猫仔吞下去呢。它已经吓得吃起来了,只剩下一只了。因为昨晚这一带
吵吵闹闹,母猫被他们吓坏啦。”
“被吓坏的是我呀!”
“怀柔派”上气不接下气,非常不高兴地说道。我对那软硬两派的角色,说不定要给相
反的评价了。……至此,已经无话可谈,“志愿调解人”也看出来警官们在那里失去继续读
下去的时机了。从侧面看,他的鼻子和口须的一半以三片螺旋桨的角度,均衡地向警官仰
着,不容分说地客套起来。
“实在给您添麻烦啦,太抱歉啦!实在是,谢谢,警察先生!多亏您帮忙,这下子好
啦!”
警官们似乎在语言方面的力学上感到羞愧,致意之后走了出去,但因关闭那扇坏了锁卡
子的门,使花丛中产褥里的猫又呜呜地咆哮起来了。哈哈。
“不给猫弄点水和食物么?”刚才我没想到,因为警官也没想到啊……
“不过,警官也没受过抓猫的训练呀。”“志愿调解人”好像很讲公平似的忧虑地说
道。“既然不是你家的猫,就由它去吧。……因为至少那个母亲现在是吃饱了的呀。”
“你是猫问题的专家?”
“猫问题的?喏,那种专家恐怕还得年长一些吧。……那么,可以让我进屋么?”
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当我们在起居室里对面坐好时,“志愿调解人”又目不转睛地
看着我。于是,在厚厚的眼镜片后边,仿佛有黑灰色的微粒在涌动的眼睛里快活地露出了惊
异的目光,他发出有些吓人的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