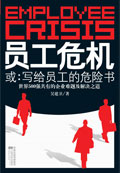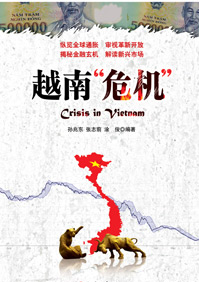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岁的我和二十八岁的森挑选了适合外出的服装,打扮一下,走下楼去。如果在集会以后逮住
麻生野,我想试一试更新以后的性能量,就把杂物箱中的避孕套装进了衣兜,而且是四个!
哈哈。不过,如果想起歌德的下一句,可能就给兴高采烈的我劈头盖顶地泼上冷水啦。
但是,我并非为了在世上享乐,
才被放在这样高的地方。
4
那天下午,我正在和森玩“架桥”游戏时,发生了大地震。所谓的“架桥”游戏,就是
在正方形格子棋盘的奇数行上开五个洞,偶数行上开四个洞,用丁字型的塑料棋子往里填的
游戏。对立的双方一方执红,一方执白,用丁字形棋子架起红—红、或白—白的桥。如在建
桥当中遇到对方棋子的阻拦,就得迂回前进或者为了填上空格而跳一格前进。我曾经煞费苦
心地教过“转换”前的森下这种棋,这也是一种教育啊!什么教育?那就是教育他必须和别
人斗争、教育他别人就是妨碍森的生活方式正常进行的人。还要教育他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什
么措施、怎样前进、被别人穷追不舍时怎样逃脱,有时还不得不阻挡别人的前进,而且必须
打败别人。这不是人生教育的游戏么?
首先,教他“桥”的抽象概念就很难,一直向前摆、用五个丁字形棋子造成的“桥”;
遇到阻拦就拐弯抹角、最终以二十五个棋子才摆成的“桥”;要他理解这两者都是“桥”,
是需要相当高深的理解力的啊。其次,要求他把自己的棋子拦
在对手的棋路上,这个训练也是相当麻烦的。因为森不懂下棋的逻辑,而是出于造型的
动机,想摆成图形啊。
尽管如此,森还是大体上掌握了下棋的程序。于是,先在森的阵营上摆了个丁字形棋
子,从这里开始,因为这种游戏的规则很简单,森居然以那三个棋子为基础赢了。当我没棋
可走时,我就变成为了击败优势的森而不惜采用任何卑鄙手段的、绝望了的仇恨的俘虏了。
那不是以下棋来进行“转换”的预演么?因此,我是在发生了“转换”的现在,用下棋加深
我们的转换呀。
一开始,按惯例我让森先摆3个棋子,游戏开始了。我很快就走投无路了,因为森的攻
击恰中要害,不留反手的空隙啊。我输了。第二盘,让森两个子,我聚精会神地下,我想孤
立他那两个棋子,不让它和后摆上的棋子形成连跳。可是,大概由于我只顾对付对方,而把
自己的棋子摆得太草率,以致我完成包围时已无法阻挡森从别的方向架起的桥了。我嗓子眼
儿痛得直冒火啊。于是,第三盘我只让森一个子。我想打乱森的布局,下了一步猾棋,再也
不顾名誉廉耻了,我才十八岁呀!哈哈。不料,倾刻之间,我就在那步猾棋上跌交了。因为
猾招儿是有两面性的呀。我勃然大怒,大汗直冒。与此同时,我从森的身上也闻到了既不像
我的汗味儿、也不像少年的汗味儿的男子汉的体臭。森也紧张啦。怎么办?
……这时,发生地震了。那是一种奇怪的有稳定性的上下颠簸、仿佛坐在震荡的大型地
基上、使你并不担心而最后又落下来的地震。我按照老习惯,立刻给森讲起地震来了。
“这就叫地震,是地壳表层在活动。如果要问它是怎样引起的,在一般情况下……”
面对我的讲解,满脸胡须茬子的森的眼里发出了很感兴趣的光亮,而且,那眼神十分平
静。
我忽然满面通红,因为我怀疑如此饶有兴趣、并且十分平静地聆听我的讲述的森,也许
就像苏格拉底,是一个首先让我自知无知,然后再把我引向智慧的人啊。恰在这时,打来了
电话,我才脱离窘境。
且说,这次电话虽然和刚才那个恫吓电话一样也是年轻男子打来的,但是,这一位倒相
当和气,工会里不是有一个干劲十足、爱用假嗓说话的年轻人么,就是他呀。
“如果刚才是八级大地震的话,东京就毁灭了。当然,自卫队要出动的。而且,自卫队
会利用这个机会搞政变。日本国内没有力量制止啊。地震加政变,革命力量就要被镇压了。
地震这种情况多变的机遇,只有自卫队能够利用,而革命党派是无法利用的。基于这样的现
状分析,如果再发展一步又将如何呢?要准备与地震规模相当的大规模的破坏力,并且要显
示出能够自由地发动和控制那个破坏力,只能如此,别无良策了。人类是制造不出能与地震
的总能量匹配的巨大的能量的。如果限定在东京这个地区,我们是可以展望它的前景的。一
颗核弹被革命党领导下的人民拥有了,我们趁着与毁灭东京的地震几乎相等的混乱的机会,
把那颗核弹掌握在自己手中,到那时,底牌不就亮出来了么?虽然反革命党派宣传说他们也
有过类似的设想,可是,我们从十年前就遵照这个战略坚持战术活动啊。他们是似是而非
呀。只有我们的党派才是革命的。关于这条路线,我们在理论上、实践上,都
是正确的。我们期待你不要屈服于反革命集团流氓式的恫吓,前来参加集会。我们将对
专家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加给以评价。
“专家?什么专家?我不过是十八岁的没有经验的小伙子呀!?”
我用发自“转换”以后的肉体的自然的声音问道。我在“架桥”游戏中连战连败,我感
到我不但肉体,而且连精神也完全变成十八岁的的了。
“什么?”
那家伙不再用刚才伪装的声音,他的真嗓音粗暴,还带些幼稚的不安。
“十八岁的小伙子?别装蒜了。你不是那个核电站的原职员么?”
“那,你随便提问些专业问题来试试吧。你可以试试我积累到三十八岁的知识还剩下多
少?试一试十八岁的青年的头脑里是否还我留着那些……
“嗯?!蠢货!”
打电话的那个人说了一句土语方言。仔细一听,他说了几句古老的骂人的话,就把电话
挂断了。哈哈。我倒向他赤裸裸地讲了大实话。无可奈何。他大概是趁着地震才给我打电话
的革命党,把我视为敌人了。因为我是不愿给他们提供核动力知识的人啊。
其实,我早就受到反对党的威胁了。我知道肯定要遭到某一党派的反对,但是,没想到
最后各个党派都反对我!然而,在现实当中,他们反对的是那个已不存在的三十八岁的我,
所以,转换了的我应该是安全的了。哈哈。
当我和森来到集会的楼前时,一个陌生人正站在融化了又结冻的雪堆上讲话,他大约三
十来岁,刚说几句就遭到佩带“反面警察”袖章的保卫会场的青年们推搡,他一连几次都头
朝下倒在雪堆上。那人的气色很不好,因为他蜷缩着,看上去要比实际上个子小,是个忧郁
型的人。可是,为什么蓄着自我标榜的胡须,难道是自我意识的分裂?顺着那胡须再仔细
看,宽大的额头下面是又大又尖的鼻子,讲话的神态也不单纯,既直爽坦率、又妄自尊大,
双重性格。
“一个党要打倒它的反对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不这样做,就不叫党啊。起码不
是列宁主义的党。但是,何必一定要用钢管敲碎脑袋、砸坏手脚关节、以致于非杀戮不可
呀?其实,只要偷偷地逮住,扒下裤子,打完屁股放走就行啦。不论抓多少回,打完屁股就
放。因为他们都是好学生,渐渐就会厌倦了被打屁股,说不定就加入你们的党了。有这种可
能性的。如果被你们敲碎了脑袋、砸坏了关节,这些人即便加入你们的党派也没有用了。杀
死的当然更不行啦!这一点,你们明白吧,因为你们是好学生啊!(这时,被他指到的两三
名“反面警察”一边说:“我们可没被别人敲碎脑袋、砸坏关节、当然也没被杀死呀!反对
党算什么东西!什么叫打屁股?”一边将蓄小胡子的那人推开。那个人像等待这一手似地,
倒在雪堆上,他一站起来就抖落身上的雪和泥,像狗抖毛似地把雪渣儿和水滴甩出去。然后
稍稍躲开反面警察,又开始演讲,可是,一会儿,他又向反面警察挨过去了。
“我也考虑过斡旋组织之间的和解方法,暂时从a党b党各派五个人,“出差”到对方
的党派里去,也就等于双方都被
索去了人质,所以,他们会为留在对方的同志的命运着想而对到这边来“出差”的人们
以礼相待吧?如果为了给自己的党争取同样的待遇而举党欢迎,也许那才是聪明的党派的所
为!××可是款待从外国来的客人呀!如果认为对反对党的人只能用暴力排除,那就不是聪
明人了。在这期间,双方党派的派出人员也会了解到反对党的理论和实践和自己一方的并没
有太大的分歧,起码也没有分歧到值得打屁股的程度了。于是,他们就可能成为一种动力,
推进两个党派的合并,不是这样的么?如果不是这样,请你说出来怎么不是这样?“你既不
懂得组织原则、也不了解世界形势,现实当中存在的不是只有革命党派和反革命流氓集团
么?”反面警察进行着险些中了那人圈套的反驳,然后更加凶狠地把他推倒。
且说这位留胡子的演说家,从我和森在一旁看热闹时已经被推倒四五回了,当他仿佛已
经不指望自己能爬起来却又慢慢腾腾地爬起来时,他一边拍打身上,一边向我俩走来。大概
因为看热闹的只有我俩吧。他用深度近视眼看人由于某种原因而摘下眼镜(这时显然是由于
他的脑袋扎进了雪堆呀,哈哈)时的半睁的羞涩的眼睛望着我们这样说:
“革命党向群众做政治宣传时,就要把党外的知识分子拉到自己一方来,难道这件事本
来不是应该相反的么?如果不把圄囿自己的围栅拆掉、向外扩展,党本身又如何扩大呀?仅
仅拉拢几个知识分子是无用的。把他们当做面向普通群众的政治宣传的自由媒体,牧养他们
不是更好么!”
开头我还以为留胡子的演说家的议论是对我而发的呢,可是,转瞬之间我就明白过来
了。他在对那个被他当做革命派而且即将接纳的一名知识分子,也就是森说话呀!二十八岁
的森露出宽厚的微笑,倾听着留胡子的演说家的讲话,仿佛无声地勖勉他。他的微笑使鼻孔
里堵满血的留胡子演说家也不由得露出如同淘气而被发现了的孩子似的特殊的微笑。这时,
“反面警察”过来了,对着我们和演说家,用同样的表情和声音传达了原本是不同性质的信
息。尽管为了便于表达,我希望分开来记述。
“请参加集会的入场!你想防碍别人开会么?”
在“反面警察”把我们蛮横地推开之前,森充满信心地伸出手去,冲破阻拦握住了留胡
子的演说家伸过来的手。于是,我产生了一阵与十八岁小伙子相称的、嗓子眼发热的冲动。
5
在会场入口的大厅里,以极小的间隔面对面摆着两张长椅,人们经过那时时,不仅能接
到许多种传单、还要掏出参加集会的捐款当做回报,这种长椅的置法真是一年比一年有长进
啊。像我这样的吝啬鬼可受不住了。虽然如此,我还是把我和森的份儿、二百日元硬币投进
箱里。可是,森不是从昨天以前我穿的裤子口袋里掏出五千日元钞票捐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