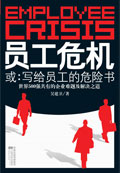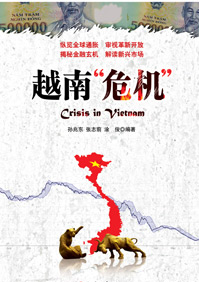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躲过去。
“都是你伤害了森,我和森绝不饶你!”
不知是她想再踢一脚、还是由于酒醉蹒跚,反正我从妻子悠悠晃晃的脚步里逃脱,并且
为了顺便逃出酒精的雾气,向旁又躲了一步。
“我要带森回娘家了!你去板桥的日大医院把森切除的瘤子要回来!那是你的!除此之
外,再也不让你从森身上拿走什么啦,我和森要和你斗争!”
“不要胡说八道嘛,就连那些搞市民运动的活动家们也不用这种腔调啊。”我这样一
说,忽然觉得掩护着森的妻子好像指的是麻生野,因为她那柳叶眼瞪着我啊。说不定妻子的
不着边际的议论是出自对麻生野的对抗心理呢。
3
因为妻子给我包扎伤口时纱布上的绷带只缠一半就撒手不管了,我只好自己来绑好绷带
了。可是,怎么也弄不好,我不知缠到哪里固定才好。我到起居室去取出只露出眼、鼻和嘴
的黑毛线滑雪帽,把它套在头上,不但绷带按住了,而且加在伤口上的压力也减小了,满舒
服的。我试着叫森、森,但是,随着面颊的震动只发出咦、咦的声音。
我返回书房,妻子刚才还在对森耳语,忽然大声来劝森了。
“森,和妈妈在一起,离开这里啦。妈妈只带森一个离开这里呀。把那个打森的疯子丢
在这儿,妈只带你走啊!”森已经脱离了抱着头吓得缩成一团的状态,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
来了。妻子并拢双膝、挺起上身,紧搂着森的身子。森比那种姿势的我的妻子还要高出一
头,他看见重又出现的我,目眩似地抬起了他那肿胀的双眼,并不想摆脱那拥抱。
“森,和妈妈一块儿离开这儿吧。只有咱们俩,走吧。把那个又想抛弃森、又殴打森的
疯子留下!”
我只是坐在自己的床上,不知是因为气候变化还是因为身体的变化,我浑身冰凉,直打
冷战;我等待我的高招儿①的到来。其实,我已经为我和森之间不会再有那机会而不安了。
这时,妻子弯着腰抱着森想往外走,但是,显然森在反抗。妻子使出力气,强拉硬拽地往外
拖,可是,森就像钉在那儿的木桩,反倒使妻子蹒蹦了。
①原文为“持时间”,即赛棋时棋手想招儿的限时。
“森,你干什么呀?好啦,森,咱们走吧!”
“森、森!”我想介入,但是,只发出咦咦的声音。“森、森!和我在一起吧,森、
森、和我在一起吧!”
然而,我发出的只是咦、咦、咦咦的声音啊!在我和儿子的生命当中很可能造成一大转
折的这个关键时刻!
森抗拒着想把他连根拔走的我的妻子,他采取了非暴力抵抗者的作法,只是叉开双脚使
劲踏住,酒醉加上体力消耗,妻子每一用力就趔趄,而且,森在这时一直把脸正面对着咦、
咦、咦地呼叫的我。戴着红边儿黑毛线帽的我深感羞愧,但是,在森的目光的鼓舞之下,我
坚持着咦咦咦地叫了下去!
“你说什么呀?”妻子扭过头来申斥我,她和森不一样,她看见我的毛线帽好像受到了
相当不小的刺激。哈哈。
“咦、咦、咦!”我叫着,把嘴里的血泡一口吐在枕巾上,那血色很像牙龈脓漏患者吐
的唾沫。
“森、森,爸爸不好啊!”
“爸爸,不好,不是啊!”
“森,跟妈妈走吧!”
“咦、咦、咦!”
“森跟妈妈,去,不是呀!”
这时,妻子一下子松开森,挺直腰,朝我前进了两三步。然后站住,像虾夷人模仿鹤的
动作的舞蹈那样,不过,她表演的不是起舞的鹤,而是恫吓的鹤,她缓缓地伸起僵硬的双臂。
“你们父子俩都是钚中毒的疯子呀!”
她喊叫着,却又号啕大哭,跑下楼去。
我拿出为了不能入睡而又不敢去取掺威士忌的啤酒时而藏在书柜里的白兰地和意大利香
肠,不过,我还是意识到受了伤,就把白兰地放回去,用爱摆弄机器的人都会珍惜的那把万
能刀,切开了香肠。
“咦、咦、咦!”
森径直走到我身旁,吃起摆在计算卡上的香肠了。他用指甲剥下皮、把胡椒粒全抠出
去,而后水平地举着那薄薄的圆饼,用那仿佛再也看不见外界的黯淡的水一般的眼睛盯着
它。对待如此微小的食物,表现出如此把食物当做物的存在的敬意,能够如此自然流露地吃
东西的人,除了森以外,我再也没见到过。当然,我也知道这短暂的休息只是暂时停战,看
着吃意大利香肠的森的喜悦简直就像在战壕里喝军用水壶中的一滴水。
但是,楼下那位孤独的女战士还在折腾,好像收拾行李,还频频地打电话。因为起居室
和书房的电话连通着,有一方拨号,另一部电话也随着叮铃叮铃地响。我如果举起这边的听
筒,就能知道妻子和谁通话,可是,我不干那种事。因为得到了森的参与,现在我稳操胜
券,不必急。况且,不论你怎样悄悄地拿起听筒,妻子马上都会发现,她就会突然袭来。
“你偷听啊,这个钚中毒的疯子!”哈哈。
等森吃完了香肠,我把森一向依赖的毛毯、也就是他第二次动手术时带到医院去的那条
老朋友似的毛毯,从他床上取来,给他盖上。我因为疲乏,无力给他换尿布,就带他去撒
尿。回来,我和森就一同在床上合衣而卧了。脸上的伤,一个劲儿地疼,就像用竹签把我钉
在“现在”上了。那疼痛有周期运动的感觉,那所谓“现在”的周期运动,不是常常令人想
到永恒的回归么?疼痛的永恒回归!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为了入睡而闭上眼睛时,眼睑里
就现出各种各样的图形,滴溜滴溜地转,分散开、又聚合,好像有一定的周期。而且,它也
很像曼陀罗,仿佛上面写了我一辈子的预言,本想设法把它读下来,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
起,就再也不出现了。我很想把我对那已经忘了的过去的发现讲给在我身边仰面静卧而内心
却热得像着了天火的森听,可是,由于不愿再去打扰今天已经经历了许多变故的森的反思起
了作用,我还是取白兰地了。不料,我还没从床上起来,睡着了的森却搂住了我的脖子,是
为了再也不走失、再也不迷路了么?
4
我睡着了。可是,总是做充满不幸的离奇的梦,在睡梦之中弄得更疲惫不堪了,而且是
在复杂的情节之中累得精疲力尽的了。自从在“铁皮人儿”事件中我遭受辐射以后,我的人
生就变成无休止的暑假了,因为醒来时没干什么活儿,所以,睡着时做这种梦的劳动也许就
是它的补偿吧。虽然醒来时常常带着记不住内容的梦给我留下的疲倦,但是,我觉得那疲倦
的总合不是恰与人在弥留之际回溯一生的我的幻影的总量相等么?不过,那还是转换以前的
事啊。因为我这样和你交谈时这个“现在”就已逝去,所以我需要代笔作家,不过,“转
换”的时刻马上就到了,有关这些就先放过吧。
我所说的梦,是这样的。我遭到某人的毒打,正在返回家中。看那情形,我出门好像就
是为了去挨打的。我的嘴里很不舒服,似乎和我脸上的伤以及两颗假牙的不舒服相呼应。牙
医给我带上临时假牙以后,由于筹款的原因,至今还没装上永久的假牙,在这期间,牙床硬
了、萎缩了,从临时假牙和牙床的缝隙里喷出带沫子的口水。当我发现以后,就用劲儿咬那
假牙的顶部,回家来用手指伸进嘴里一摸,因为固定假牙的金属架挂得不合理而碰掉了上边
的两颗小臼齿。当我用舌头把它推出去时,满口牙齿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全掉
了。嘴里含着掉下来的全部牙齿,向前走着,实在蹩扭……
我睁开了眼睛,因为传来了妻子跑上来的脚步声。这是我和妻子共同的毛病,我们在屋
里时总是慢慢腾腾地挪动身子,而去别的房间的中间地带时却是快步,好像害怕在那中间地
带再遭到森头上的瘤子一类的东西的袭击似的。妻子啦地一声打开室内电灯,滔滔不绝地说
道:
“丢下你和森,我要走啦!以前我可怜你和森,怕你们一起自杀,太凄惨,所以才没丢
下你们。可是,我已经下了决心,丢下你和森,我要走啦!我要重新开始学习,我要为了和
你生下这样的孩子所做的牺牲而重新学习!然后就正经地结婚,生一个正经的孩子!如果我
不是和你而是和别人结婚的话,就一定能生育正常的孩子!假定Ⅰ:如果森确是由于钚污染
所致,那么,下一次和我结婚的对象就是没受到钚污染的人。因此,孩子正常!假定Ⅱ,如
果说森只是事故的产物,那么,我已经出过事故,从概率来看,下一个孩子也应该正常!你
看过这个么?!我要丢下你和森,我就要离去了!”
“不过,今晚不是已经不能办什么事了么?明天再走不好么?”
我本想这样说,但是,只能发出咦、咦、咦的声音。不过,按保守估计,和我性交过二
千五百回的妻子却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
“你说什么?导演已经想到路面结冰在轮胎上挂了防滑链来接我了。因为你说不定会控
告人家私闯民宅、不让我走,所以,他在外边等我呢。还不赶快起来,替我搬手提箱?因为
我要丢下你和森出走啦!”
她把导演这个普通名词的未加诠释的使用,打消了我要挽留妻子的念头。从敞开的门厅
外边,在这深更半夜里,传来了军号吹奏的“此地远离故国几百里”①的旋律。我在报纸的
剧团专栏上看到过,这位话剧导演在破汽车上安装音乐喇叭的消息。听说那个剧团接连成
功,似乎为复兴戏剧赢来了转机,而我妻子在少女时期就和那位年轻导演有过来往。
①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期间的军歌。
“是这个手提箱,别磨磨蹭蹭啦!丢下你和森,我要走了!”
起居室里翻腾得乱七八糟,在我去外国出差的手提箱旁堆着直到最后还不忍丢弃但又装
不进去了的东西。底部已变成波浪形的煎锅,那是女医大的同班同学的结婚礼物,回想一
下,我们并没用这个锅吃过算得上烧熟的肉类啊。哈哈。我试了试手提箱的盖子能否关上,
我想把那煎锅塞进去,不料在一旁叉着腿站着的妻子却狠狠地把它一把抢过去,扔了。为什
么突然恨那煎锅,我不知道。
不过,没装那个沉重的东西反倒是万幸了。因为原本脸上的伤就疼,再加上和森在狭窄
的小床上共眠早已浑身关节疼痛,现在被手提箱一压,马上就受不住了。
“你在干什么?这就要歇着么?阳萎!”
我再也顾不上什么疼痛,拚死拚活地把手提箱搬到门外。她在十年前求爱竞争的对手能
听到的地方说起阳萎,未免太厉害啦。哈哈。
小个子导演站在停在路灯下的雪铁龙旁,他穿着和车色以及车型都巧妙地谐调的衣服,
天如此黑,却带着太阳镜,满面忧伤。
我一出门就放下手提箱,后退一步,站在那里。按照妻子的逻辑来说,她并没要求我把
手提箱搬上雪铁龙啊。
“赶快把行李装上车!那家伙小气,说不定要搬回去呢!”
导演仍然带着忧伤,不紧不慢地走过来。当他来到手提箱前变成小跑时,突然没头没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