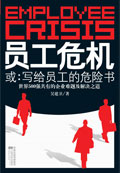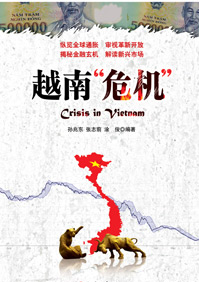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一章 战后业余棒球的鼎盛时期
1
明明那是别人说过的话,而且我还记得别人说那些话时的情景;可是,我总觉得那才是
发自我灵魂深处的话。不过,既然语言得有两个人参与才能成立,也就不能不说是由于我的
存在才成为别人的语言的真正的源泉了。有一回,那位核电站的原工程师,也就是和我相互
排斥的那个人,他既想让我听见,却又装做自言自语似地说:
“没有比选上救场跑垒员①更令人胆战心惊而又最雄心勃勃的了!那是为业余棒球殉难
啊。虽然现在没人叫孩子们去充当球场跑垒员的了。可是,遇到这种情况恐怕也……”
“是啊。即使没有哩哩哩②的声音来加油,也是……”
①打棒球在关键时刻上场的跑垒运动员。
②“哩哩哩”指看棒球的人为跑垒员加油时的喊声。哩是英语Lead的谐音,意思是离
垒,抢先。——译注
我随声附合着,不过,那已经超过了随声附合了。虽然不能简单地以为原工程师发出那
番宏论,我做出回答的那一瞬间就是产生了共鸣;但是,我们却连通了如同骨肉之亲的纽带
似的热乎乎的管道,那是因为我们总算具体地了解到彼此同龄,或者只差一两岁,是真正的
同辈人了。在那以前,我们只知道他和我分别毕业于东京大学理学院和文学院,谁也不知道
谁的年龄,不知道因为什么,稀里糊涂地就造成了前边说过的不和的根源了。
我们怎么是同辈人?因为我在答话里说到哩哩的声音时,他马上就心领神会;而我对救
场跑垒员去殉难这个词儿也立刻就产生了共鸣。我们在暮春的阳光之下,就这样静默着,倾
听着回荡在五脏六腑里的、激励人心的哩哩哩的呼声。
在将近中午的体育场上,一群和我们的孩子不同的孩子们闷声不响地在打棒球,因为他
们想到了在体育场周围的校舍里上课的人。他们是一群并不把体育看做正课的想出人头地的
小精英。他们已经不是靠声音来抒发从体内涌出的运动的喜悦的孩子了。带原始性的肉体的
情感怎么可以不加拘束地大喊大叫出来啊,他们必须成为既能接受外部管束而又能严于自律
的小精英呀。
一阵突如其来的怪声从我们的孩子们的教室里传了出来。不论是他还是我,都立刻怀着
遗憾的心情注视着我们的孩子,生怕他们面对体育场上那些安静而又擅长运动的孩子们所表
现出来的不容置疑的聪慧敏捷大喊大叫起来。
“其实,像我这样的人,也只能靠充当救场跑垒员参加球赛了。因为我没有接球的皮手
套啊。”
“我知道。”我回答他道。与战后业余棒球鼎盛时期的过热的流行程度相反,当地的孩
子们拥有皮手套的实在太少了。
虽然我们村还算侥幸,连接球皮手套带守垒皮手套一共有九只,但那每一只都是正式队
员的私人财产。只有通过黑市途径弄到皮手套的孩子才能取得正式队员资格。我只能难为情
地遮掩着布制的接球手套在“外野”跑来跑去,捡起正式队员没接住漏在场后的球。因为我
只能在保证也是属于正式队员私人所有的球不丢失的条件下,才被允许参加练球啊。
“时至如今,我永忘不掉邻居的新制中学①来赛球时的兴奋和紧张啊。其实,那也就是
我为了独立生存而踏入现实社会的最彻底拚搏呀。我还记得干瘪得连一点儿油水都没有了的
肚脐眼周围一个劲儿地哆嗦,头脑里哩哩哩地直响。如果一开始就拉开了比分,救场跑垒员
就不必饱受等待之苦了。可是不论输球也罢、赢球也罢,对于坐板凳候场的我来说,都是枯
燥无味的,比赛呀。也可以说那算不上什么球赛。只有到了仅仅一分之差的第九轮后攻,或
者也是一分之差的、危机四伏的加时赛后攻,那才叫真正的球赛呢。如果遇上第九轮后攻,
相差只有一分,正式队员打了一个安打,这一来,救场跑垒员就得殉难了。主教练是刚刚复
员回来的财主家的二少爷,他好像要向对方的教练炫耀他的棒球学问(他把这也叫做理论
呢,哈哈),于是就想要点儿手头儿上的技巧给他看看。启用救场跑垒员。我该上场啦!—
—如果我是臂力过人的名手,说不定当场就被启用为救场击球手了。可是,我只是一名一直
坐在瞒着老师从教室里搬出来的双人板凳上的平庸的替补队员啊。即使腿脚并未疲乏,也是
一样。
①日本的旧制中学为五年制,新制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译注
现在,这样的我,打起精神不顾一切地向一
快。和我交接的那个家伙已经瞪起三棱眼了。为什么?是因为他好不容易才打开一个安打,
却被我这个跑得慢的替他出尽了风头啊。如果我偷垒失败,他就会说我糟塌了他的安打,他
总爱唠唠叨叨,唉声叹气!反过来说,如果偷垒成功,而且巧妙地配合击球迅速跑垒,我就
成为拉平比分的跑垒员了。那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加时赛了。虽然时间短暂,但我毕竟成了英
雄,而且在加时赛当中那家伙还不得不把接球皮手套借给我用,所以,他刚才瞪三棱眼也是
理所当然的了。而且,当我以救场跑垒员身份站在垒上的一刹那,我方全体队员、包括那个
三棱眼在内,一齐大声呐喊哩哩哩让我抢先、再抢先些、果断地偷垒!同时也像警告,如果
你离垒两米还死盯着投球手而不跑,你就是背叛!我淋着哩哩哩暴风雨,发烧的脑袋里嗡嗡
直响。本来我应该把自己的腿劲儿加拚劲儿和投球手的动作配合,并且必须准确果断;但
是,我已经头昏眼花,根本做不到了。不但投球手想打坏主意,而且接球手看上去也技高一
筹,蹲在那里简直和《棒球少年》杂志画页上的土井垣武一模一样!如果在平时,也许我会
嘲笑那家伙装腔作势,简直不像城里人而更像油腔滑调的乡下瘪三;可是,现在,我却完全
被他吓住了。是跑出去、还是死守不动?或者略微抢先?我只要表现出一点犹豫,哩哩哩的
催促的暴风雨就向我发热的脑袋和蜷缩的手脚袭来。处在惶恐之中的我,仍然可悲地怀着能
够顺利偷垒的野心啊……
实际上他说了这么多话么?也许他只说了没有比救场跑垒员更痛苦、更处于野心勃勃的
尴尬立场啊。然而,我认为他的灵魂想要表达而令他坐立不安的内容,肯定是这些,我的灵
魂已经全都听到了。我们沉默着,站在根本不像战后不久就建起来的与新制中学的漂亮体育
场的一隅,耳朵里幻听着说不清是鼓励还是诅咒的哩哩哩的喊声,从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就屡
次三番地发烧的脑袋,又烧起来了。
这时,在我们的身旁有几位和我们一样等待我们的孩子的母亲。其中有几位好像是在酒
吧或舞厅工作的,虽然已经到了早晨,她们还带着酒味儿,看得出干这种既破坏了她们的婚
姻生活而又未必适合她们的年龄的职业,也是出于无奈。因为在那里也有属于我们的孩子们
的原因,所以,我们不大交谈,只是相互交换着也许能引起对方注视、也许并没引起对方注
视的含糊暧昧的问候,然后又是沉默,呆望着体育场上那些和我们的孩子们不同的孩子们,
打发时间。终于,我们的孩子们出了教室,向这边走来了。学校有一条规定,我们这些家长
必须在远离教室的体育场的另一侧等候。排成一队的我们的孩子们向这边走得实在缓慢,当
他们走近那些和我们的孩子们不同的孩子们仍在继续打棒球的体育场的边上时,为了保护头
部,用双手捂着脑袋,就像一群年幼的投降者。本来这种保护头部的动作是老师教给我那个
用塑胶弥补头盖骨缺损的孩子和刚才和我说话的那位原工程师的孩子的。但是,那些患唐氏
症①和脑性小儿麻痹症的孩子们,也把它当做必须执行的指示而自觉地接受了。我们的孩子
们参差不齐地用双手捂着脑袋,依然慢慢腾腾地向这边走着。当他们终于蹭到我们这边时,
刚才打棒球的那些和我们的孩子们不同的孩子们已在用竹扫帚打扫体育场了。我们的孩子们
就在那砂尘弥漫之中半睁着弱视的眼睛,但又尽量盯住前方,脚尖朝里,踏着碎步走来。
挂在孩子们胸前的写着住址、电话号码的名牌上,也写着保护人的名字,所以我们这些
家长也可以凭着名牌来辨认孩子。譬如,我是光的父亲,那位核电站原工程师是森的父亲。
虽然我从一开始就对森的父亲的儿子的名字有点儿不解,但仍然没打听过那名字的来由,那
就如同森的父亲不曾打听我儿子以光为名的来由一样。
然而,森的父亲和教师们交谈时,至今还耿耿于怀地提起他的孩子出生时那个不懂事的
实习医生发誓说这孩子不可能有视力的那件事。由此可见,我给我那个和他的孩子在完全相
同的部位上缺了头盖骨的儿子取名时的心态,他也早就看穿了。我不由得想起,在孩子诞生
之后紧急手术的慌乱之中,我因为耽误了报户口而不得不写了检讨书跑到区公所去,以及我
为他想出和拉丁语“白痴”谐音的森②这个名字时的沮丧……
①先天性痴呆的一种,由英国内科医师J.L.唐发现。——译注
②“森”的日语读音为“毛利”。
当我们的孩子们终于走到我们等候的地点时,他们一下子就忘了刚才还和他们排在一个
队里的相互的存在了。而我们也一下子就失去了对家长之间的关心了。于是,我们各自结成
只顾照看自己的孩子的牢固的两人小组,离开了体育场角落上的等候处。就连我和森的父亲
谈起救场跑垒员而看见双方赤裸的灵魂上发出微光的那一天也不例外。
2
刚开始的时候,森的父亲和我搭话,似乎不是为了开辟共识的道路,而是为了明确地表
达敌意才对我说话的。四月的一天早晨,刚开始来迎接儿子的森的父亲对从上学期就一直接
儿子的我疯狂地挑衅道:
“我在外国的研究所里干过,我看得出来,有你这样牙齿的人,就表明了他是出身于什
么阶层的了。”
森的父亲说完就露出他排列得过于整齐的牙齿,向两旁裂开他那形状虽好但太稚嫩的嘴
唇,进一步强调他的牙齿漂亮。
“的确,我的牙齿代表着我的阶层,但也代表着时间。这代表着战时和战后粮荒时期的
少年阶层啊。难道那不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代人么?”
森的父亲作为一位成人毕竟还太幼稚,用他那圆圆的水灵灵的大眼睛睥睨着,沉思了一
下。然后淡淡地表示了要停止挑衅。
“是啊。如此说来,倒也是的。”
森的父亲所以向我挑衅,是因为那天早晨我看不惯他像指挥作战的将军似的站在体育场
上,而告诉他特殊班学童家长应在哪里等候他才对我采取报复的。我虽不是胸襟开阔之人,
但是,那天早晨却根本没动气,因为我深知领着一名我们的孩子,挤进拥挤的公共汽车,走
上又走下一级又一级的天桥台阶,好容易才赶到学校,还必须把忐忑不安的孩子交给人家;
头一次经历这些的父亲会对外界的一切发动攻击,是很自然的现象,我是饱尝了这种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