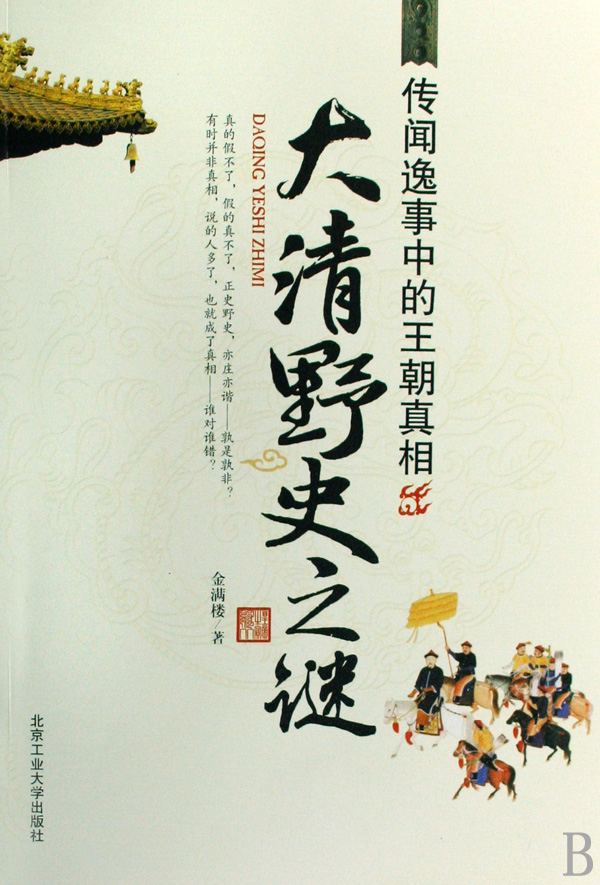中华百年百篇经典散文-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
辛未三月念六夜四鼓,意洞手书。
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选自《历代文选》
“今”
作者: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学者、思想家。著有《李守常全集》、《李大钊选集》等。
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可以宝贵。
为甚么“今”最可宝贵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孙所说的话答这个疑问:“尔若爱千古,尔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
为甚么“今”最易丧失呢?因为宇宙大化,刻刻流转,绝不停留。时间这个东西,也不因为吾人贵他爱他稍稍在人间留恋。试问吾人说“今”说“现在”,茫茫百千万劫,究竟哪一刹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现在”呢?刚刚说他是“今”是“现在”,他早已风驰电掣的一般,已成“过去”了。吾人若要糊糊涂涂把他丢掉,岂不可惜?
有的哲学家说,时间但有“过去”与“未来”,并无“现在”。有的又说,“过去”“未来”皆是“现在”。我以为“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有些道理。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换句话说,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故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不晓得有几多“过去”时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说是由所有“过去”时代的思潮,一凑合而成的。
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声响,都向永远流动传播,不能消灭。屈原的《离骚》,永远使人人感泣。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呼应于永远的时间与空间。一时代的变动,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样传演,至于无穷,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联的永远性。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此数个复杂事件,与明日的数个复杂事件,更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今”最可宝贵的道理。
现时有两种不知爱“今”的人:一种是厌“今”的人,一种是乐“今”的人。
厌“今”的人也有两派。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因起一种回顾“过去”的感想。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风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惟一的希望在复古。他们的心力全施于复古的运动。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与复古的厌“今”派全同。但是他们不想“过去”,但盼“将来”。盼“将来”的结果,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单是耽溺于虚无飘渺的空玄境界。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
乐“今”的人大概是些无志趣无意识的人,是些对于“现在”一切满足的人。他们觉得所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商进取,再为创造。这种人丧失“今”的好处,阻滞进化的潮流,同厌“今”派毫无区别。
原来厌“今”为人类的通性。大凡一境尚未实现以前,觉得此境有无限的佳趣,有无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觉不过尔尔,随即起一种失望的念,厌“今”的心。又如吾人方处一境,觉得无甚可乐;而一旦其境变易,却又觉得其境可恋,其情可思。前者为企望“将来”的动机;后者为反顾“过去”的动机。但是回想“过去”,毫无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时间。若以企望“将来”的动机,而尽“现在”的势力,则厌“今”思想,却大足为进化的原动。乐“今”是一种惰性(inertia),须再进一步,了解“今”所以可爱的道理。全在凭他可以为创造“将来”的努力,决不在得他可以安乐无为。
热心复古的人,开口闭口都是说“现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恶若何深重,祸患若何剧烈。要晓得“现在”的境象倘若真是这样黑暗,这样卑污,罪恶这样深重,祸患这样剧烈,也都是“过去”所遗留的宿孽,断断不是“现在”造的;全归咎于“现在”,是断断不能受的。要想改变他,但当努力以回复“过去”。
照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
忆独秀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文中说过,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尝推广其意,也说过人生惟一的蕲向,青年惟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沉滞于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万亿年的“我”,都俨然存在于“今我”的身上。然则“今”之“我”,“我”之“今”,岂可不珍重自将,为世间造些功德。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
我请以最简明的一句话写出这篇的意思来: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鲁迅与王国维
作者: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作家、学者、翻译家。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译作《浮士德》(歌德),学术论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等。
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国维。但我很抱歉,在两位先生生前我都不曾见过面,在他们的死后,我才认识了他们的卓越贡献。毫无疑问,我是一位后知后觉的人。
我第一次接触鲁迅先生的著作是在1920年《时事新报·学灯》的《双十节增刊》上。文艺栏里面收了四篇东西,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本小说,作者和作品的题目都不记得了。第二篇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第三篇是我的《棠棣之花》(第一幕)。第四篇是沈雁冰(那时候雁冰先生还没有茅盾的笔名)译的爱尔兰作家的独幕剧。《头发的故事》给予我的铭感很深。那时候我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医联二年生,我还不知道鲁迅是谁,我只是为作品抱了不平。为什么好的创作反屈居在日本小说的译文的次位去了?那时候编《学灯》栏的是李石岑,我为此曾写信给他,说创作是处女,应该尊重,翻译是媒婆,应该客气一点。这信在他所主编的《民铎杂志》发表了。我却没有料到,这几句话反而惹起了鲁迅先生和其他朋友们的不愉快,屡次被引用来作为我乃至创造社同人们藐视翻译的罪状。其实我写那封信的时候,创造社根本还没有成形的。
有好些文坛上的纠纷,大体上就是由这些小小的误会引起来了。但我自己也委实傲慢,我对于鲁迅的作品一向很少阅读。记得《呐喊》初出版时,我只读了三分之一的光景便搁置了。一直到鲁迅死后,那时我还在日本亡命,才由友人的帮助,把所能搜集到的单行本,搜集了来饱读了一遍。像《中国小说史略》一书,我只读过增田涉的日译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读过原文。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竟失掉了见面的机会。
事实上我们是有过一次可以见面的机会的。那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年底,鲁迅已经辞卸广州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回到了上海,我也从汕头、香港逃回到上海来了。在这时,经由郑伯奇、蒋光慈诸兄的中介曾经酝酿过一次切实的合作。我们打算恢复《创造周报》,适应着当时的革命挫折期,想以青年为对象,培植并维系青年们的革命信仰。我们邀请鲁迅合作,竟获得了同意,并曾经在报上登出过《周报》复刊的广告。鲁迅先生列第一名,我以麦克昂的假名列在第二,其次是仿吾、光慈、伯奇诸人。那时本来可以和鲁迅见面的,但因为我是失掉了自由的人,怕惹出意外的牵累,不免有些踌躇。而正在我这踌躇的时候,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回国了,他们以新进气锐的姿态加入阵线,首先便不同意我那种“退撄”的办法,认为《创造周报》的使命已经过去了,没有恢复的必要,要重新另起炉灶。结果我退让了。接着又生了一场大病,几乎死掉。病后我亡命到日本,创造社的事情以后我就没有积极过问了。和鲁迅的合作,就这样不仅半途而废,而且不幸的是更引起了猛烈的论战,几乎弄得来不及收拾。这些往事,我今天来重提,只是表明我自己的遗憾。我与鲁迅的见面,真真可以说是失诸交臂。
关于王国维的著作,我在1921年的夏天,读过他的《宋元戏曲史》。那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种小本子。我那时住在泰东书局的编辑所里面,为了换取食宿费,答应了书局的要求,着手编印《西厢》。就因为有这样的必要,我参考过《宋元戏曲史》。读后,认为是有价值的一部好书。但我也并没有更进一步去追求王国维的其它著作,甚至王国维究竟是什么人,我也没有十分过问。那时候王国维在担任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大学的教授,大约他就住在哈同花园里面的吧。而我自己在哈同路的民厚南里也住过一些时候,可以说居处近在咫尺。但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假使当年我知道了王国维在担任那个大学的教授,说不定我从心里便把他鄙弃了。我住在民厚南里的时候,哈同花园的本身在我便是一个憎恨。连那什么“仓圣明智”等字样只觉得是可以令人作呕的狗粪上的微菌。
真正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