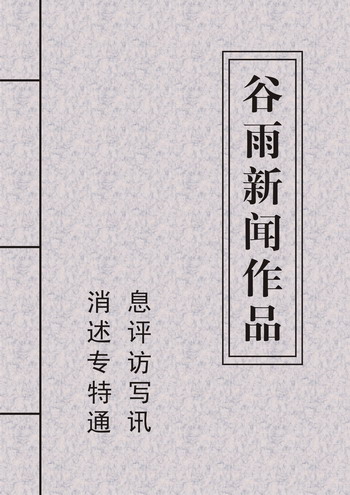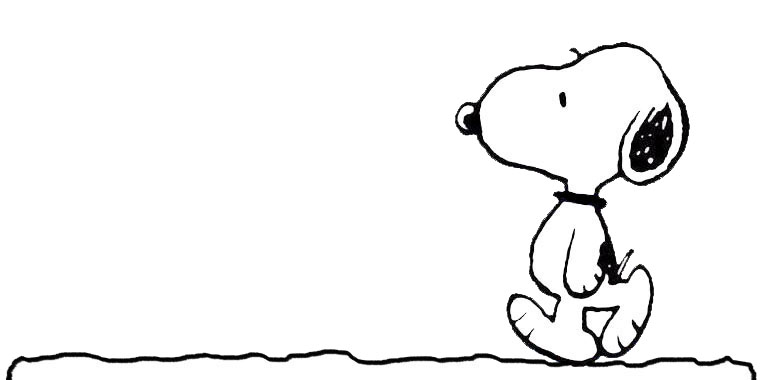川端康成作品集-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说不定也会害怕的。”
菊治默不作声,心想,没分寸的正是说这种话的近子你呢。
“菊治少爷也去野尻湖了吧?”
近子这是明知故问。其实她一进门,就从女佣那里听说了,近子没等
女佣传达,就唐突地走了进来,这是她一贯的作风。
“我刚到家。”
菊治满脸不高兴地回答。
“我三四天前就回来了。”
说着,近子也郑重其事,耸起左肩膀说:“可是,一回来就听说发生了
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这使我大吃一惊,都怪我太疏忽,我简直没脸来见
菊治少爷。”
近子说,稻村家的小姐结婚了。
菊治露出了吃惊的神色,所幸的是廊道上昏暗。但是,他毫不在意地
说:“是吗?什么时候?”
“好象是别人的事似的,真沉得住气啊!”
近子挖苦了一句。
“本来就是嘛,雪子小姐的事,我已经让你回绝过多次了嘛。”
“只是口头上吧。恐怕是对我才想摆出这副面孔吧。好象从一开始自己
就不情愿,偏偏这个多管闲事的老太婆好自作主张,纠缠不休,令人讨厌是
吗。其实,你心里却在想,这位小姐挺好。”
“都胡说些什么。”
菊治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你还是喜欢这位小姐的吧。”
“是位不错的小姐。”
“这点我早就看出来了。”
“说小姐不错,不一定是想结婚。”
但是,一听说稻村小姐已经结婚,心头仿佛被撞击了一下,菊治强烈
地渴望在脑海里描绘出小姐的面影。
在圆觉寺的茶会上,近子为了让菊治观察雪子,特地安排雪子点茶。
雪子点茶,手法纯朴,气质高雅,在嫩叶投影的拉门的映衬下,雪子
身穿长袖和服的肩膀和袖兜,甚至连头发,仿佛都熠熠生辉,这种印象还留
在菊治的内心底里。难能想起雪子的面容。当时她用的红色绸巾,以及去圆
觉寺深院的茶室的路上她手上那个缀有洁白千只鹤的粉红色皱绸小包袱,此
时此刻又鲜明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后来有一次,雪子上菊治家,也是近子点茶。即使到了第二天,菊治
还感到小姐的芳香犹存在茶室里。小姐系的绘有菖兰的腰带,如今还历历在
目,但是她的姿影却难以捕捉。
菊治连三四年前亡故的父亲和母亲的容颜,也都难以在脑际明确地描
绘出来。看到他们的照片后,才确有所悟似地点点头,也许越亲近、越深爱
的人,就越难描绘出来。
而越丑恶的东西,就越容易明确地留在记忆里。
雪子的眼睛和脸颊,就像光一般留在记忆里,是抽象的。
可是,近子那乳房与心窝间长的那块痣,却像癞蛤蟆一般留在记忆里,
是很具体的。
这时,廊道上虽然很暗,但是菊治知道她多半穿的是那件小千谷白麻
皱绸的长衬衫,即使在亮处,也不可能透过衣服看见的她胸脯上的那块痣。
然而,在菊治的记忆里,却能看见。与其说昏暗而看不见,毋宁说在黑暗中
的记忆里见得更清楚。
“既然觉得是位不错的小姐,就不该放过呀。像稻村小姐这样的人,恐
怕世上独一无二。就算你找一辈子,也找不到同样的。这么简单的道理,难
道菊治少爷还不明白吗?”
接着,近子用申斥般的口吻说:“你经验不多,要求倒很高。唉,就这
样,菊治少爷和雪子小姐两人的人生,就整个改变了。小姐本来对菊治少爷
还是很满意的,现在嫁给别人了,万一有个不幸,不能说菊治少爷就没有责
任吧。”
菊治没有响应。
“小姐的风貌,你也看得一清二楚了吧。难道你就忍心让她后悔:如若
早几年与菊治少爷结婚就好了,忍心让她总是思念菊治少爷吗?”
近子的声调里含有恶意。
就算雪子已经结了婚,近子为什么还要来说这些多余的话呢?
“哟,是萤火虫笼子,这时节还有?”
近子伸了伸脖子,说:“这时候,该是挂秋虫笼子的季节了,还会有蛮
火虫?简直像幽灵嘛。”
“可能是女佣买来的。”
“女佣嘛,就是这个水平。菊治少爷要是习茶道,就不会有这种事了。
日本是讲究季节的。”
近子这么一说,萤虫的火却也有点像鬼火。菊治想起野尻湖畔虫鸣的
景象。这些萤火虫能活到这个时节,着实不可思议。
“要是有太太,就不至于出现这种过了时的清寂季节感了。”
近子说着,突然又悄然地说:“我之所以努力给你介绍稻村小姐,那是
因为我觉得这是为令尊效劳。”
“效劳?”
“是啊。可是菊治少爷还躺在这昏暗中观看萤火虫,就连太田家的文子
小姐也都结婚了,不是吗?”
“什么时候?”
菊治大吃一惊,仿佛被人绊了一跤似的。他比刚才听说雪子已经结婚
的消息更为震惊,也不准备掩饰自己受惊的神色了。菊治的神态似乎在怀疑:
不可能吧。这一点,近子已看在眼里。
“我也是从京都回来才知道的,都给愣住了。两人就像约好了似的,先
后把婚事都办完了,年轻人太简单了。”近子说。
“我本以为,文子小姐结了婚,就再没有人来搅扰菊治少爷了,谁知道
那时候稻村家的小姐早就把婚事办过了。对稻村家,连我的脸面也都丢净了。
这都是菊治少爷的优柔寡断招徕的呀。”
“太田夫人直到死都还在搅扰菊治少爷吧。不过,文子小姐结了婚,太
田夫人的妖邪性该从这家消散了吧。”
近子把视线移向庭院。
“这样也就干净利落了,庭院里的树木也该修整了。光凭这股黑暗劲,
就明白茂密树木,枝叶无序,使人感到憋闷,厌烦。“父亲过世四年,菊治
一次也没请过花匠来修整过。庭院里的树木着实是无序地生长,光嗅到白天
的余热所散发出来的气味,也能感觉到这一点。
“女佣恐怕连水也没浇吧。这点事,总可以吩咐她做呀。”
“少管点闲事吧。”
然而,尽管近子的每句话都使菊治皱眉头,但他还是听任她絮絮叨叨
讲个没完。每次遇见她都是这样。
虽然近子的话怄人生气,但她还是想讨好菊治的,并且也企图试探一
下菊治的心思。
菊治早已习惯她的这套手法。菊治有时公开反驳她,同时也悄悄地提
防她。近子心里也明白,但一般总佯装不知,不过有时也会表露出她明白他
在想什么。
而且,近子很少说些使菊治感到意外而生气的话,她只是挑剔菊治有
自我嫌恶的一面,缘此而可能想到的事。
今晚,近子前来告诉雪子和文子结婚的事,也是想打探一下菊治的反
应。菊治心想:她究竟是什么居心呢,自己可不能大意。近子本想把雪子介
绍给菊治,借此使文子疏远菊治,可是现在这两个姑娘既然都已成亲,剩下
菊治,他怎么想,本来与近子毫不相干,然而近子仿佛还要紧追着菊治心灵
上的影子。
菊治本想起身去打开客厅和廊道上的电灯。待菊治意识过来,觉得在
黑暗中,这样与近子谈话,有点可笑,况且他们之间也没有达到如此亲密的
程度。连修整庭院树木的事,她也指手划脚,这是她的毛病。菊治把她的话
只当耳旁风。但是,为了开灯而要站起身,菊治又觉懒得起来。
近子刚走进房间,尽管说了灯的事,但她也无意站起身去开灯。她的
职业原本使她养成了这类小事很勤快的习惯。可是现在看来,她似乎不想为
菊治做更多的事。也许近子年纪大了,或许是她作为茶道师傅,拿点架子的
缘故。
“京都的大泉,托我捎个口信,如果这边有意要出售茶具,那么希望能
交给他来办理。”
接着,近子用沉着的口吻说:“与稻村家小姐的这门亲事也已经吹了,
菊治少爷该振作起来,开始另一种新生活了。也许这些茶具就派不上什么用
场。从你父亲的那代起就用不着我,使我深感寂寞。不过,这间茶室也只有
我来的时候,才得以通通风吧。”
哦,菊治这才领会过来,近子的目的很露骨。眼看着菊治与雪子小姐
的婚事办不成,她对菊治也已绝望,最后就企图与茶具铺的老板合谋弄走菊
治家的茶具。她在京都与大泉大概已商量好了。菊治与其说很恼火,莫如说
反而感到轻松了。
“我连房子都想卖,到时候也许会拜托你的。”
“那人毕竟是从你父亲那代起就有了交情,终归可以放心啊。”
近子又补充了一句。
菊治心想:家中的茶具,近子可能比自己更清楚,也许近子心里早已
经盘算过了。
菊治把视线移向茶室那边。茶室前有棵大夹竹桃,白花盛开。朦胧间,
只见一片白。
夜色黑,几乎难以划清天空与庭院树木的界限。
下班时刻,菊治刚要走出公司办公室,又被电话叫了回来。
“我是文子。”
电话里传来了小小的声音。
“哦,我是三谷。。”
“我是文子。”
“啊,我知道。”
“给您打电话真失礼了,有件事,如果不打电话道歉就来不及了。”
“哦?”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我给您寄了一封信,可是忘记贴邮票了。”
“是吗?我还没有收到。。”
“我在邮局买了十张邮票,就把信发了。可是回家一看,邮票依然还是
十张。真糊涂呀。我想着怎么才能在信到之前向您致歉。。”
“这点小事,不必放在心上。。”
菊治一边回答,一边想,那封信可能是结婚通知书吧。
“是封报喜信吗?”
“什么?。。以前总是用电话与您联系,给您写信还是头一回,我拿不
定主意,惦挂着信发出去好不好,竟忘了贴邮票。”
“你现在在哪里?”
“东京站的公用电话亭。。外面还有人在等着打电话呢。”
“哦,是公用电话。”
菊治不明白,但还是说:“恭喜你了。”
“您说什么呢?。。托您的福总算。。不过,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栗本告诉我的。”
“栗本师傅?。。她是怎么知道的呢?真是个可怕的人啊。”
“不过,你也不会再见到她吧。记得上次在电话里还听见傍晚的雷阵雨
声,是不是。”
“您是那么说的。那时,我搬到朋友家去住,我犹豫着要不要告诉您,
这次也是同样的情景。”
“那还是希望你通知我才好。我也是,从栗本那里听说后,拿不定主意
该不该向你贺喜。”
“就这样销声匿迹,未免太凄凉了。”
她那行将消失似的声音,颇似她母亲的声音。
菊治突然沉默不语。
“也许是不得不销声匿迹吧。。”
过了一会儿又说:“是间简陋的六铺席房间,那是与工作同时找到的。”
“啊?。。”
“正是最热的时候去上班,累得很。”
“是啊,再加上结婚不久。。”
“什么?结婚?。。您是说结婚吗?”
“恭喜你。”
“什么?我?。。我可不愿听呀。”
“你不是结婚了吗?”
“没有呀。我现在还有心思结婚吗?。。家母刚刚那样去世。。”
“啊!”
“是栗本师傅这么说的吧?”
“是的。”
“为什么呢?真不明白。三谷先生听了之后,也信以为真了吧?”
这句话,文子仿佛也是对自己说的。
菊治突然用明确的声调说:“电话里说不清楚,能不能见见面呢?”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