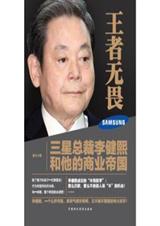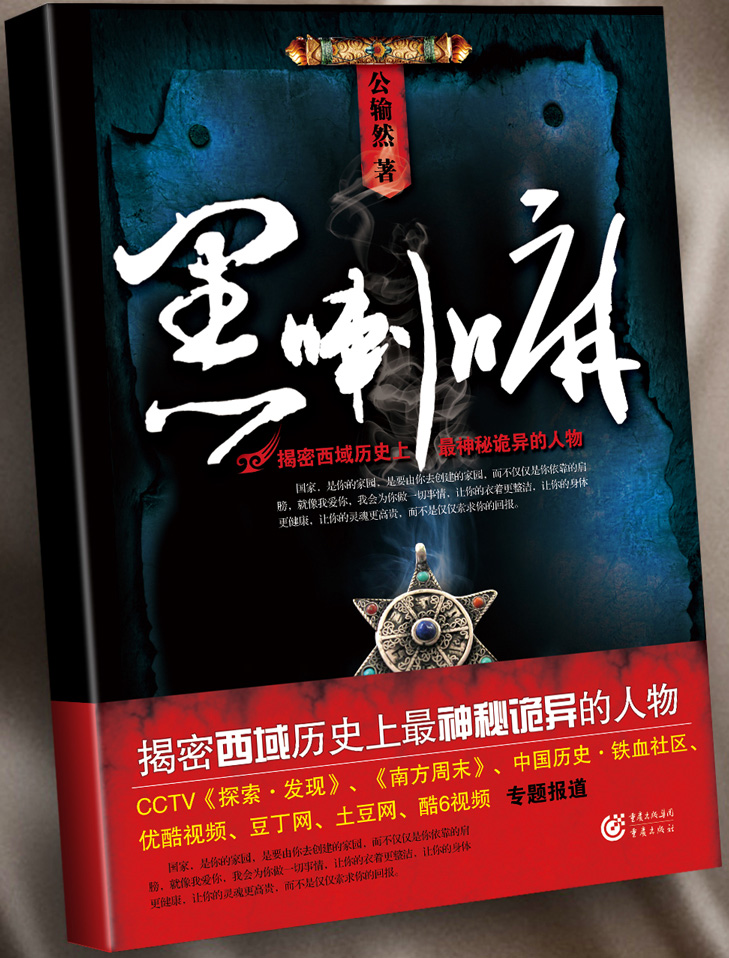萨达姆和他的伊拉克-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问:您从小失去了父亲,这对您有什么影响?您是否从您叔叔和舅舅那里得到了补偿?
萨:事实上我在感情上得到了补偿。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不止一次问自己:你是否感受到了痛苦?回答是: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因为我从家庭里得到了补偿,尽管不是全部的补偿,但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补偿。因此当我记起过去,问自己是否有一天对自己是孤儿而悲伤过,回答是否定的。这也许是农村生活的简朴所起的作用吧。当然,如果父亲不死,我的生活也许会好得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来的家庭是不能完全补偿父爱的。但叔叔和舅舅们所给予的补偿,当然首先是母亲给的补偿,是非常美好的。
问:您是否去看过您的母亲?
萨:当然。
问:您多长时间去一次?
萨:根据情况。如果我不去,她就来我这里。她仍住在乡下。
答记者问(下)
问:您同党内同志的关系如何?是纯政治的关系,还是充满友情的人道主义的关系,尽管在党内的地位不同?
萨:我同我的同志之间的关系是深刻的同志式的关系,我们没有将“纯”政治关系称为革命者之间的关系或复兴党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是我们的原则和革命工作需要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作好流血牺牲的准备,并同另外一位同志为保卫原则而一起献身,就像在秘密斗争时期一样都不会说二话,怎能说这种关系是一种纯政治关系呢?如果说成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关系,那就超出了正常人的想像,超出了党的原则和党的品德。对我来说,在同志之间的关系上,我从来不受任何拘束。无论职位高低,我同他们相处都很自然。因此我同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很正常。我们有时谈笑,有时又很严肃认真,需要严肃认真的时候绝不能宽容,对同志应该关心的时候就要关心,该严格要求的时候,就要严格要求。
问:您读过不少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的作品,谁对您的思想影响最深?谁对您的感情影响最大?您小时候所崇拜的历史、政治人物是谁?
萨:从深刻的政治、思想方面来说,列宁作为永垂不朽的思想家和思想深邃的革命者引起了我的关注。凡是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了解他的伟大的一生。使我受到影响的人物还有加迈尔·阿卜杜拉·纳赛尔,尽管我们的党对他的经验比较敏感,而他对我们的党也抱有成见,但我对他的性格特别感兴趣。此外还有戴高乐。戴高乐和纳赛尔都很有个性,有自己处理事情的风格。虽然两个人处理事情的方法不尽相同,但他们对自己的国家都具有杰出的民族主义的立场,对本民族起着带有某种“骑士”程度的特殊的民族主义的作用。戴高乐曾对英国人说过:“为在独立后履行诺言,你们对法国都做了些什么就请记录下来吧。”戴高乐为使法国重新站起来发挥了他的作用,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纳赛尔这个人表现在他的个性方面,而列宁则表现在他的思想和政治娴熟的方面。
问:在家里,您是如何实行民主的?您既作为父亲又作为丈夫,在日常生活中您是如何行使权利的?您的妻子作为一名家庭妇女,享受权利的程度如何?
萨:我们家里的钱主要用在教育上,具体家务几乎都由我的妻子承担,因为我们不能一同下厨房做饭,这怎么可能呢?但是一切家务,哪怕是小事,例如家具如何摆放,如果需要的话,我们都一起进行商量。
问:您是否对家庭内所有的政治倾向问题都加以干预?
萨: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教育进程中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使我的孩子们不要将自己看成是国王的孩子,高人一等,因此,我在家里时经常对他们讲这件事。有时候,我故意提出一些问题,让他们进行讨论,我从中给予指导。有时,让一个孩子主讲,我进行评论。因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使孩子们有优越感,而应使他们感到自己同普通人一样,从而使我的家人明白他们所享受的一切并非是特权,而只是工作的需要。例如,我的家庭有司机,配有汽车、厨师、服务人员,这些人只是为我所担负的领导职务服务的,并非是为他们服务的。我的两个孩子,指伊德和卡西,对此是明白的,并从小接受了这种教育。他们都加入了复兴党。
问:现在伊德多大了?
萨:现在16岁,1980年6月18日满16周岁。
问:易卜拉欣哈吉向我提起过,说您有时到欧加村去看望他。您作为阿拉伯地区一个最富国家的首脑,当您坐在易卜拉欣的泥土房子里时,您个人的感情如何?
萨:事实上,对此我是很珍视的,我还真的希望他们住在这泥土房子里,而同时,我又希望他们住到别的地方去,这是一种相互矛盾的心理,当然我希望他们住得更好些。我不否认我希望那些对我、对人民作出很大贡献的人能像别人一样生活得更好些。易卜拉欣哈吉现在已挖了墙基,准备建一座新的石头住宅。
问:您对爱情、婚姻、生与死是如何看的?
萨: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没有爱情地活着,我不认为没有爱情的生活就是平坦的,因为爱情不仅仅是同未婚妻或妻子相联系,它也同孩子和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但首要的是爱人民,与历史相呼应。当然我不否认同妻子之间的联系、同孩子们的联系,而且我认为这是最深刻的联系。
问:我从录音带里听到您讲过您生活中的一段趣事:“我没想到过我会死,尽管我遇到过死亡的危险……”
萨:是的。我一生中曾多次经历过死亡的危险,有时就在死亡的边缘上。
问:您对复兴党的思想坚定不移,您对将来的感受如何?
萨:是的,现在我关心的是500年后人们将会说我们些什么,而不是现在。一次,我在谈到阿卜杜拉·纳赛尔的经验和萨达特(埃及前总统,被暗杀——译者)行为的痛苦时,我曾对复兴党的领导同志们说过,而且不止一次强调:我们不应该倒下,我们不是怕死,而是害怕死以后的事情。因为我们还只是看到了生活中表面上发生的事情。我至今仍然相信这与信仰并不矛盾。我认为人是能够看到死后的事情的,尤其是同某项原则性事业相联系的人。为完成这项事业,需要他去死时,他对死后的事情是能够有所预见的。这就是我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