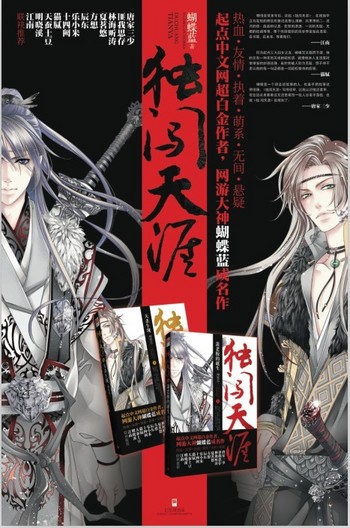曾在天涯 作者:阎真-第7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说:“孟浪,你说的话,句句都对。凭良心说我也认为你选择了回去这条路是对的,你呆在这里会活得很痛苦。只是对完了还是不解决我的题,你说怎么办?”我说:“我说怎么办,你是知道的。”她说:“问你呢,道理不解决我的问题,你说怎么办?”我说:“张小禾你逼得好紧,才知道你好厉害。怎么办?跟了我回去,保证你会幸福。”
她轻笑一声说:“仗着自己那几万块钱?”我说:“还有我的心,我一生都爱你,忠于你,还不行吗?你不信拿条手帕来,我这就切了手指写份血书让你收了,可以不?”说着站起来到厨房去拿刀。她拼命抱了我的腰,鸣咽着:“我信了,我信了。信了还不行吗?”我说:“你还要怎么样呢,一个女的?你的心到底有多大?是只天狗要把天地都吞了才够吗?”她说:“我的心也不大,还没有你大。可是我就是不能回去。来一趟多难啊,现在都移民了,倒要回去?我也不知道自己留在这里等什么,也许没有什么可等。”我说:“等什么你不愿说,等着过高级日子。”她说:“那我也不能说一点都不是。凭着来一趟这么难,半条命搭在里面,我也不能这么就回去了。我家里还睁了眼望着我呢。为了我出来,全家的钱都用光了。”我说:“我明白你跟了我回去是为感情作了牺牲,我这心里明白,我会在这一生中给你回报。现在是考验你的感情的时候了。”她说:“也可以这样说吧。如果我把这个话对你说呢?”我说:“张小禾你好固执!我还有什么办法说服你没有?”她马上说:“这句话应该是我对你说的。”
我也拿了那支圆珠笔,在桌面上一下一下地敲,说:“我有个想法,不知对不对。”她说:“你的想法反正都是对的,因为是你的想法。”我一笑说:“感情这个东西,谁说是万能的呢?男女有了爱就够了吗?在绝对真实的感情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真实的现实。”她说:“看了你我说早就想说这句话了,只是说不这么好。”我说:“感情是瓷的,现实是钢的。瓷那么硬也碰不过钢。”她望了我,眼神忧郁而凄凉,说:“怎么办你到底说最后一句。”我铁着心说:“跟我回去,你答应了我你就是救了我也救了你自己。”
她平静地说:“到底还有第二句话没有?”我不做声。她伸出双手做了着掐的动作,说:“恨得我啊,恨不得就这么掐了你的脖子,从里面挤出一句话来。”比划着双手掐拢去。我说:“你不要逼我,让我最后想一想。”她说:“你想吧,想好了告诉我一声。我自己也最后想想,明天我就写封信回去,向家里要求一下,看他们怎么说,也许就让我顺着自己的感情走了。信来回至少二十四天吧。如果二十四天以后还没有希望,就没希望了。”我说:“一定要听你家里的吗?说不定你家里考虑问题也不那么周全。”她说:“我爸爸想问题想得深远。”我说:“不相信!至少在这一点上,你对你爸爸的崇拜和对我的不崇拜同样是没有道理的。”
她说:“我暂时还不这样想。”我说:“张小禾,今晚我都不认识你了,好狠啊!”她说:“这样是我吗?我是这样吗?被你逼成这样。人呢,就是没有办法不狠心,人没有办法。狠得自己心里痛起来,也得咬紧了牙忍着。好残酷的世界,人没有办法,人别无选择。我倒想天天夜夜甜甜密密亲亲爱爱呢,可是行吗?总有个梦醒时分。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又何苦一往情深,你说,又何苦?”
我说:“你都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坏东西?”她说:“心里坏不坏,结果也是一样,给苦给人受。倒不如心里也是一个坏,干脆跟那个人一样,我心里还不会象这样刀子在一刀刀的割。”我心里一个冷颤,站起来双手扶了她的肩说:“张小禾,张小禾。”她坐着不动,仰起脸望着我。我避开她的目光,喃喃地说:“张小禾,张小禾。”她忽然“扑哧”一声笑了。我说:“你笑什么,你笑什么,好怕人的。”她笑着笑着,闭了双眼,挤紧了,眼角出现一线眼纹,下唇也慢慢卷进去,咬在牙齿之间。我看见一丝眼泪从她眼角渗出来,就用手轻轻抹去。又有泪不住地沁出来,我擦也擦不完。她身子不住地颤抖,牙咬着下唇一阵一阵地用力。我心里发抖,双手也抖起来,震颤着说:“还有二十多天呢,还有二十多天呢。”她的头慢慢垂下去,手轻轻移开我的手说:“你睡去呢,我也困了。”我在泪水摸糊中看见她唇下一排淡红色的牙齿印,又看见一丝血从嘴角流出来,不忍再看一眼,捂了眼睛呜咽着跑了出去。
九十
张小禾对我热情依旧,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想起那天晚上的情景,我不敢再提这件事。好多次我都怀着一种悲壮献身的心情去设想在加拿大挣扎下去:就在餐馆打工一辈子吗?找个地方开家理发店吗?真的就去了北方小镇开家小餐馆吗?在那种悲壮心情的推动下,我心中几乎就要转了过来,准备接受这样的现实,最终在细想之下还是否定了。这种种选择与我的内心的要求相距实在太远了。我去唐人街租了《渴望》的录像带来,每天晚上等她写完了作业,就一起看一两个小时。
我在心中一天天数着日子,盼着她家的信早点来,又怕信来得太快。我说:“这时间好折磨人的。也不知道你家里收到信没有,都快十天了。到南京的信可能会快一点。”又说:“你爸爸妈妈是开通的人不呢?”她说:“在别的事情上是够开通的。这件事谁知道呢?”快有两个星期的时候,她情绪突然低沉了,录像也不看了,有一次看见她偷偷地抹眼泪。我问:“是信来了吗?”她说:“这么快,怎么可能?”我想着也不可能,说:“南京的信怎么这么慢呢?”她说:“信你就别问了,不看我也知道他们会怎么说。”我说:“那我完了。”她说:“完不完要问你自己。”我抓了她的手说:“跟我回去是要你下地狱吗?老子掐死你!”说着用力握她的手,她痛得“哎哟哎哟”地叫,我松了手,她说:“你下毒手,不叫我活了吗?”我揪了她的耳朵说:“冤家,冤家,天下这么大,怎么就碰上了你。”她说:“冤家路窄这话真的没错一点。”我说:“也别等你家的信了,你今天就判了我的死刑吧!你家的信等得我太难受了,还有十二天!”她说:“我倒要问你一句,你的想法改变了没有?”我不做声,她说:“别说这个,说也说不出个结果,挺烦人的。”
过了两天她的情绪又正常了。我在心里算计着,是不是真的到北方去看看,也许真的就到一个镇上办家餐馆去,先看了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又想起自己到多伦多差不多两年,只去过千岛湖、蒙特利尔和尼亚加拉瀑布,也该去别的地方看看。一动心思就忍不住了,这天早上对张小禾说:“在这里干等着那封信我过不得,我明天去北方玩几天,回来等你的判决。”我没说看看能不能办个餐馆的事,我想真有可能了,回来再告诉她,给她一个惊喜。她说:“你也该去看看。”我马上就去灰狗汽车站买了一张通票,一百三十八块钱,十天之内可以在安大略省和魁北克自由地乘车。我把票拿给她看了,她说:“也真该去看看,老是呆在多伦多有什么意思。”我说:“多伦多有意思的地方又不敢去,夜总会几百块钱潇洒一次,只敢蒙在毯子里想一想。”她说:“说不定有一天你可以自由出进,你又不去争取!”我说:“明天我要去了,今天你该给我一个安慰吧。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到时候就钻进来了,我那么老实,总是忍忍忍的吧!”她笑着摇头,撮着舌尖吐出一个长长的“不”字,又说:“谁叫你那么固执?”我故意生气说:“还有条件,还有条件!”她说:“便宜了你,我怎么办?”我笑了说:“反正到时候我不走,一倒下去就睡在那里了。”她撒娇似地说:“知道你不会的。”我说:“我不会,我真的不会,到时候你看我会不会。”
吃了中饭她背了书包去学校,下午有两节课。我吻了她,放她去了。走到楼梯口她望了我迟疑着想说什么,又一笑,下楼去了。出了门,过几分钟又回来说:“今天我早点回来,你别出去了。”说完头也不回,“咚咚”地下楼走了。
五点钟她回来了,买了肉肠和草莓酱,还有烤得很好的面包。她笑吟吟地说:“今天你跟我走,出去玩去。”说着进了厨房,拿了几听可口可乐和几个苹果。我问:“到哪里去?”她说:“只管走就是,这么好的天气。”把东西塞在我手里,又去房里收拾几分钟,挎了个包出来。我听她的吩咐,单车载了她到学院街地铁站。我问:“往南往北?”她说:“往北,把单车也带上。”我也不问,推了单车下了往北的入站口。坐在车上她口里不停哼哼地在唱,我说:“欢什么欢,死活还不知道呢。”她瞟我一眼,哼得更欢快些。我说:“你还小吧。”她笑而不语。到了最北边的芬治站下了车,我扶着单车上了电动楼梯,她一手提着食品,一手扶在单车后面。出了站又沿着央街一直往北,又骑了好久,转了几个弯,我说:“出城了。”她说:“出城才好。”我说:“回来的路也记不得了。”她说:“到晚上一片灯火那边就是多伦多,丢不了你。”再往前骑,没有了房子,到处都是大片的玉米地,几台不知名的农业机器停在那里,看不见人。我说:“都到乡下了,还到哪里去呢?”她说:“到去的地方去,没人就好。”我说:“没人好,没人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的我忍不住要做那见不得人的事了。”她问:“那你想干什么?”我说:“你自己心里知道,就是那些你也想的事。”她一根指头在我腰上戳了一下。
路边有家小餐馆,我说:“看看乡下餐馆是什么样子。”我们停下来进去了,正是晚餐的时候,里面有几个人在喝啤酒。应侍小姐甩着金发走过来想招呼我们入座,她连忙一捏我的手,退了出去。又骑了车,我说:“不要说到北方去,在这里也会寂寞,都被世界忘记了,人总要有个文化背景。”她说:“在多伦多谁又记得你,回国去谁又记得你?”再往前去,张小禾指着前面远远的一座山说:“到山脚下去。”我说:“你就不怕强盗,天一黑,袜子套在脸上都从山里跳出来了。”她说:“你在说《水浒》吧,这里没有强盗,强盗都在城里。他们和你一样怕寂寞,哪怕是个强盗,他也要文化背景。”她说着又要我停了车,跳下来,把袋子塞到我手里,也不说话,钻到玉米地里去了。一会听到一种轻微的响声。我知道她在干什么,弯了腰斜着头去看,也看不见什么。我大叫一声:“我来了,我真的跳进来了!”她钻了出来,我说:“捉蚱蜢子呢。”她只管笑。我说:“哦,是浇地,浇地。”她说:“就想撕了你这张嘴,好痞的。没有几个人是你这样痞的,还算个知识分子。”我说:“也没有几个是我这样不痞的,凭良心说!”
再往前骑,野旷天低,四下无人,鸟儿虫儿发出极和谐的鸣奏。微风吹过,无边的绿浪从远处一波一波传过来,又一波一波传往远处。在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