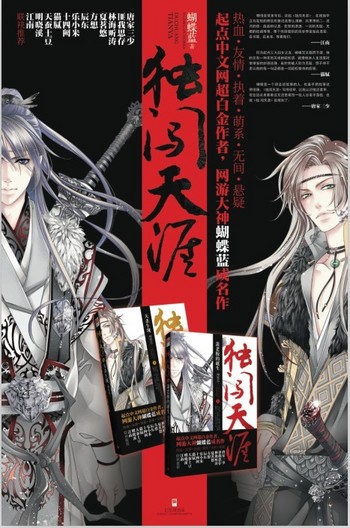曾在天涯 作者:阎真-第6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拉了我的手说:“你不敢望我!你站起来看了我的眼睛。”我站起来望了她,说:“我伟大领袖一样站在里,有什么呢。”她在脸上左右端祥,说:“你这么狡猾的人,我怎么看得出?也只好活活让你骗了。”我说:“你提高警惕,小心哪一天我会骗你这个人。”她真笑说:“你是个大骗子,大骗子在骗人的时候叫人提高警惕,人家就没警惕了。”
到两点多钟,我说:“睡觉吧。”她吃惊地望着我,象是不相信我会说出这样的话。我马上意识到她领会错了,以为我这么轻易地就提出了那个重大问题。我马上说:“我去睡了。”她说:“都随便你。”回到自己房里,我老是想着“都随便你”这几个字,到底是现在去等会去随便呢,还是去不去随便?我竟不明白。我又去回想她说话时的神态,却想不起来有什么意味。我感到沮丧。自己没有勇气留下来。有些东西也许说得了也就得到了,压抑了自己谁会说你是个圣人,人的自由空间其实很大呢。沮丧之后又感情以庆幸,毕竟自己没把事情做绝,自己这个落魄的样子,虚弱的本质总有一天要显露出来,到那一天可怎么办,怎么向她说明?在沮丧和庆幸之间徘徊了好久,反反复复地去比较,体会,最终庆幸还是占了一点点上风。渐渐的我有点佩服了自己的理智,到底还是有勇气离开。我在心里表扬了自己。
八十
这样如醉如痴有几个星期,我越来越明确地感到,尽管自己在顽强抵抗着,事情还是朝着那个固定的目标进展,那些想象终究会变成现实。这使我感到兴奋也感到恐惧。我不能装作在沉醉中忘记了冷漠的现实背景。张小禾在迷醉中靠自己的感情想象美化了我的形象,这是她的真纯,林思文也许就不会如此。但现实在不久的将来会显出自己的冷漠面孔。手中这份工作也许就在下个月就完了,这份收入就断了,我将重新陷入走投无路地境地。经济如此萧条,我根本不相信自己能找到一份稍微象样的工作。我现在走出了那一步,她将来会后悔会进退两难的。但我现在不走那一步,将来就更没有了勇气没了机会。在沮丧中我甚至有点遗憾张小禾投入得太真诚了,使我不得不为她想一想,又遗憾自己就这么动了真感情,生怕伤害了她一点点。我痛恨自己没有能力给她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也感到了自尊心对这种关系越来越强烈的反抗。
在这种关系中,我需要有精神的优势,有被依赖带来的满足,我太看重这种感觉,以至在找不到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宁可放弃。已经有迹象表明,我在Ho-Lee-Chow这份虽然不那么体面却收入还过得去的工作,也快要保不住了。当我违背了自己意愿,近乎讨好地向新来的老板提出节省一点经营成本的建议时,他的反应竟那样冷漠,使我感到了难堪,感到了自己的无耻。在萧条中一些人发疯似的想找到工作,老板只要出一半多一点的钱就可以雇到一个同样能干的人。毕竟他也是个艰难经营者,我并不恨他。我自己是老板也许早就下手了,不然晚上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钱在流失怎么睡得着觉。我早就作好了心理准备要去面对这个事实,现在却觉得打击将会格外沉重,这将把我和张小禾之间关系的脆弱性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无论如何,一个男人在社会处境如此尴尬的情况下,不会有足够的信心去展开一份浪漫的恋爱,特别是我。我越是意识到钱这个怪物的残酷力量,就越感到心灰意冷。这种心灰意冷是这样真实可感,它使那种浪漫情调变得空洞虚幻。我想象着虚无之中有着一个微笑的面孔,哪怕我闭了眼也无法逃脱它嘲讽的注视,那两道目光射得我如置身冰窖。
张小禾却似乎对这一切毫无感觉,她的一往情深一如既往。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暂时地忘记了内心的沮丧,给她的热情以热情的回报。最美好的日子是我休息而她又得空的那几天,我们坐在房子里,让春天的阳光照进来不知疲倦地说上一天废话,又做点好吃的。这样过了一天,她就说:今天跟过节一样。”我就说:“要是你愿意呢,咱们天天过节过一辈子。”她不接话却直管笑。
在这样的时刻在春天的阳光中她永远也不会忘记问我:“你是不是真心爱我喜欢我?”我相信世界上的女人在什么时候开了一个大会商量好了要拿这个问题来反复盘问男人。我答得厌烦了自己不好意思再说出那个“爱”字,说:“一个问题问九十九遍就可以了,第一百遍是多余的,你说是不?”她说:“我心里它老是不放心。”逗得我真想笑。她说:“你装假很会装,极少数时候露出真面目。”我笑了说:“我抱着你亲你的时候就露出真面目,不理你冷淡你的时候都是装假的。”她乐得倒在我怀中,额头在我膝上一碰一碰,说:“你嘴巴涂了油,我说不过你!”我说:“天天抱你抱厌了没有?”她说:“你才抱了我多少!”我搂紧了她说:“你可以做到三天不要抱不?”她说:“那你可以做到三天不吃饭不呢?”我说:“三天不吃饭我肚子饥饿。”她说:“那我三天不要抱皮肤饥饿。”
我笑得喘气,说:“我今天喂饱你。”就从上到下抚摸她的胳膊,她头埋在我腿上,一动不动。好久我拍她起来,她说:“快睡着了。”我点了自己的面颊说:“这里亲一下。”她亲了一下,我说:“还有这边。”她说:“一边还不够还要两边。”我说:“为人民服务嘛,还讲价钱。”她正把嘴唇凑过来,一口热气喷到我脸上,撑不住笑了说:癞壳子啊!说你是个癞壳子,你就是个癞壳子。”停一停又说:“别人都说你孟浪有才能,一挥手就是一篇。”我说:“别人更说我有毛病,混了两三年还没浮出水面,英语也是个结巴。”她说:“那也是的。”我说:“别人说我有毛病的时候,我虽然很愤怒,却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别人说我有天才的时候,我虽然很不好意思,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她指头在脸上刮着羞我说:“脸皮厚哟厚。说你是个癞壳子,你就是个癞壳子。”
有一次她拿了商店投递过来的一本时装广告在看,我把头凑过去,她指了上面的一个模特说:“这个胸脯大得吓死人,不好。”我说:“这才好呢,内容丰富,要不一览无余有什么好?”她说:“这有什么好,我一个同学的也有这么大,她烦恼得要命。”我马上笑着问:“她现在在哪里呢,她在多伦多不呢?快告诉我!”她把那本广告卷了敲我的头说:“知道你就是这样的家伙!”还有一次我说:“给你说个笑话你听不听?”她说:“听。”我说:“听了又要说我这个人不高级。”她说:“你说,我不说你。”我说:“从前有个卖布的上厕所把尺忘在里面了,回头去找厕所里已经有了人。他敲门说,同志,我要尺。里面那人说,要吃也要等一下。一会那人出来了,他说,布尺,布尺。那人说,不吃又说要吃,门敲这么急。”她听了倒在我怀中笑得直颤,说:“知道你就说不出什么好话,你这个人真的不高级,别以为自己是幽默就掩饰过去了!”又向上望着我睁圆了眼,嘴唇蠕动着,半天吐出几个字:“我咬你”。
到晚上天黑了我们出去,在夜色中牵了手走在春风里。因为对前景没有把握,我不愿有熟人看见自己和她走在一起。她似乎也明白着我的意思,顺从了我的安排,在天黑了才出来。躺在草地上我们看星星月亮,看飘浮的云,说些梦一样的话。春风给人以懒洋洋的温润的抚慰,树木在月光下透着微光,轻轻闪耀如披着梦。看不见的花朵在夜的掩护下沁出诱人的芳香向我们偷袭,不知名的虫儿在耳边轻轻诉说。沐浴在月光中说些梦话,叫人以为世界是为人精心安排的,为我们精心安排的。
这种慵懒的世俗的幸福更使人体验了生命存在的真实可感,每一个瞬间都是真正的瞬间,不论昨天今天明天,不论去年今天明年。存在的意义在这种平庸的过程中产生着又消逝着,没有终极的目的,也不需要最后的证明,它本身就是终极的目的,就是最后的证明,过去了就完成了。在这样的时刻,生命的暂时性渺小性是如此的清晰,使人怀疑那种超越平庸的渴望是不是真的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我知道自己在时间中沉醉,在一去不复返的消费着它,它正迅速离我而去。我只能如此,如此也就够了。至少,我知道了,这生命,今天,还存在着。
八十一
我始终不敢和张小禾痛快地谈一谈未来,她也不谈。她长时间的沉默使我感到意外,一个女人她不会想不到这个问题。开始我怀疑她在内心并没有作长久的打算,可是她的真诚她的热情和她说话的口气使我否定了这一点,并相信她对这种感情已经作了生命的投入。这使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渐渐的我意识到她正是为了减轻我的压力才保持了沉默的,我深心感谢着她却又倍感惭愧。
我为自己的拖延找到了一个很充分的理由,张小禾就要进行期中考试了。我担心一旦对前景进行的严肃的讨论,那一支浪漫曲就会嘎然而止。我内心深处还抱有一种愿望,希望她痴迷到这样的程度,宁愿放弃一切和我回国去。在感情上我已经完全接受了她,我愿和她携手同行直至那遥远的生命终点。这种投入使我很痛苦,无论如何我不能以一种逢场作戏的态度对待这件事,我担心着她会受到伤害。在事情刚开始发动的时候,我还希望她能够轻松地看待这件事,在这天涯海角暂时地互相安慰排遣寂寞也算不得一种欺骗。而现在,这种想法已经自动地完全消失。
这天我休息,准备了晚餐等她从学校回来。吃完饭已经暮色四合,在夜色苍茫中看不清对方的脸。我觉得这正是一个机会,在暮色的笼罩中更有勇气把话说出来。她站起来要把厨房的灯开了,我说:“别开也好。考完了吧?”她说:“考完了,还算可以。本来可以考得更好一点。”我接下去说:“被我耽误你的时间了。”又突兀地叫一声:“张小禾──”她听出我声音的异样,催促说:“有什么话说出来就是,吞吞吐吐!我们到今天还有什么话要吞吞吐吐!”我说:“我又不想说了,不好。”她越发性急起来,说:“我偏要你说。”我说:“你今天考试时间是多久呢?”她隔着桌子抓住我的手直摇说:“不是这句话,是刚才那句话。”我说“你一定要我说,我就说了。不过现在说这些事,辜负这么美的夜了。”
她在桌子那边支着脸,说:“你说。”语气中多一点严肃。我看不清她的眼神,这样也好。我说:“张小禾你怎么就跟了我呢?有那么多老板,博士,什么人。我连一份象样的工作也没有,心里很抱歉。你可能是一时冲动了。”没料到她嘻嘻笑起来说:“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呢,手心都捏出汗了。”说着张了手伸过来要我摸。又说:“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我说:“你先别笑嘻嘻的,我跟你说认真的。”她跑去开了灯说:“说黑话不舒服。我知道你跟我说认真的,我竖了耳朵听呢。”我说:“我想着我们的事有点奇怪,在多伦多大陆过来的女孩子毕竟少些,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