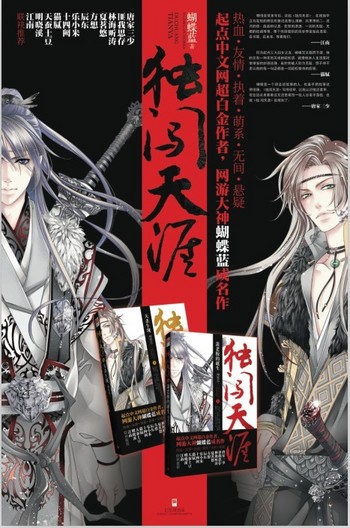曾在天涯 作者:阎真-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速地化作一种抗拒的心理冲动。到加拿大来这些日子,我在屡屡碰壁之后,已经在心里承认了自己的无能,承认了现实的冷酷,任何一件事在尚未开始之前我就准备接受否定的结果,只有对思文我不是这样想的。毕竟她是我的妻子,我在心里很难以现实的态度去看待两人的关系,也没有任何随着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的心理准备。至少她可以理解,我的能力不必在这个社会得到证明。现在我觉得现实又以不动声色的冷漠向我逼近了一步。
我默然望着她,把她的举动看作一种表演,平静中带着一点忧伤一点嘲讽。她怒气冲冲地望着我,用挑战的眼光回答我的冷漠。我不动声色,心想,她一点都不傻,她能够理解我目光中的冷漠和轻蔑。我知道她在期待着我的反击,这样她的怒气的进一步爆发就有了足够的动力。我偏不生气。对视了一会,我干脆把目光转开了去,又开了门准备下楼去。她挡到门口,把门用力一拉,压得我手指生痛。我火气一冲,点着了似的要燃烧起来。但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又压了下去。我从容地走到字纸篓边,弯了腰想把那些资料捡起来。她象终于发现了挑战的方向,冲过来推开我,把套在字纸篓上的塑料袋扎起来,“蹬蹬”地跑下楼,丢到垃圾桶里去。我抱了头坐在椅子上,脑中空空洞洞一片麻木。她也坐在那里,怔怔地望了灯出神。桌上的小闹钟合着心脏跳动的拍节,发出清脆的声响。我斜了眼去偷看她,觉得她是另一个人与我没有关系。怎么可能呢,我的妻子我却毫无办法。这事情何其荒谬又何其现实,荒谬得难以理解又现实得无法摆脱。人世间一定有许多这样的故事,两个最亲近的人却相距最遥远最难沟通最难理解。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呵欠涌上来,我又感到了自己的存在。我开了门走下楼去。和衣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我冷落她,也折磨自己,我在这含蓄的报复中感到了快意。窗外几个小孩敲着窗子,鼻子贴在玻璃上,举着手中的啤酒瓶,想问我有啤酒瓶没有。我对他们做个吓人的鬼脸,他们也对我吐舌头做鬼脸。我又嘻嘻地笑,他们也做了笑脸。我拉上窗帘,他们又敲一敲玻璃,走了。我轻手轻脚走进厨房,把思文丢掉的塑料袋打开,把资料拿出来,压在沙发下面。三楼的那对少年男女从外面逍遥回来,安妮嘻哈着问我为什么这么晚了还躺在沙发上。我说,学你丈夫的,吵架了就在这里过夜。两人爆发出一阵大笑。男的说,今晚我们不能吵了,再吵我只能睡地毯了,“So dirty!”说着两个搂抱着上楼去了。
半夜的时候,我被一只冰冷的手触醒了。朦朦中看见思文站在那里。我又闭了眼装睡,她说:“都看见你眉毛动了。”我忍不住要笑,说:“别吵,我睡得好好的又被你吵醒了。”她说:“上楼去,这会着凉的。”我说:“着了凉也不关你的事,我自己凉自己的。”她说:“不关我的事,谁带你去看医生呢?跟你说好的,你就别再固执。”我还赌气说:“你以为我是小孩子,你拍拍左边我就左边走,拍拍右边我就右边走。”她说:“你躺在这里,我也睡不着。你不生气了好不?你生病了买药又要花几十几百块钱呢!”我说:“我身子骨棒,病在我身上扎不住。”她说:“跟我充什么好汉!”说着把我用力一拉。我起来跟她上楼说:“把我瞌睡吵醒了。”她说:“说什么都没有用,求你也没有用,一说要花钱剜你的肉你就怕了。”我挣开她的手说:“那我还睡回去。”她一把拖住我,笑着说:“高力伟,你好玩,真的很好玩。”
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思文不在了。我走出去,听见厨房里有琐细的声音。我轻轻走下几级楼梯,弯腰探头一看,思文正在垃圾桶里翻找。我心里好笑,故意弄出点响声,又把楼梯踩得“咚咚”响走下去。她马上回到电炉边,从冰箱里拿了牛奶去煮。我说:“干什么呢?”她说:“煮牛奶。今天早上吃牛奶麦片粥好不?”我望了窗外说:“哦,煮牛奶,牛奶在垃圾桶里。”
她不好意思笑笑说:“那些资料呢,你捡到哪里去了,我想再看它一看。”
“还看什么,Garbage,all garbage。”
“你是男子汉胸怀就宽广点,跟我这样的人认什么真生什么气呢,你知道我一气起来就什么都不管了。”
“这倒是你的新脾气,在加拿大培养起来的,你别急,马上我就会适应了。昨天还是有收获,起码我知道了,你一生起气来就什么都不管了。”
“高力伟你不要太敏感,我是,是心里着急,只想赶快写完论文离开这鬼地方。你不也想早走?”
我说:“你急找我生气,我急又找谁,找逊克利尔成吗?──资料在沙发底下。”
喝着麦片粥她又说:“明年你真的准备走?”
我说:“跟你开玩笑呢!这里再多呆一年,我得不得神经病也难说。”
“书你也不读了?”
“读?读个鬼屁!奖学金能骗多久骗多久暂时就这么骗着。”
“那太可惜了,你会后悔的。”
我说:“要后悔只后悔到这鬼屁地方来了。心呢,天天下油锅一样,煎也煎焦了。要不挖出来你看看,真的焦了。”
她笑了用勺敲着碗说:“吃不下了吃不下了!这么说是我害了你了!”
“别的都算了,你把论文快点写完就是做了善事积了德。我恨不得今天就到多伦多去。”
“那你不走!”
“要是我英语好有手艺,我不走?那么大的城市,好恐怖的。”
她说:“不是放不下我呀?”
“放不下你,你气得我好!”
“你个男子汉呢,记仇记这么久!”
说着丢了碗把头伏在我大腿上说:“这次我不对,你胸怀好宽广,原谅了我这一次,我下次改正好不?”我看着她的后脑勺心里挺不自然,又没想到她会这样,含糊着说:“好,好,好啦,好啦。”她侧了头仰起脸说:“你真的原谅我没有你说清楚。”我说:“好好好,就这样了。我洗碗去。”她抬起身子说:“你说清楚一句话,就让你去了。”我说:“我本没往心里去,这些小事我还放在心上?你一定要我说,我反而就不说了。这你是知道我的。”
她说:“变得好倔个人!反正你已经答应我了,下次再提昨天的事,你就不是男子汉。”
“绝对的,绝对。你现在又记得我是男子汉了。再别说什么男子汉男子汉,太羞人了。这三个字,我都担当不起了。”
十六
那一阵子思文每天伏在桌子上看那些资料。她说:“高力伟,我怎么办?材料都看完了我也不知道写什么。”我说:“别看你是留学生,你的思维能力我一点都不佩服。”她说:“那你帮帮我。”我说:“民俗学我听都没听说过,我怎么懂!我开口都是胡说八道。”她说:“那你胡说八道我听听。”我说:“你不能写纯理论的题目,这你没有优势,承认不?”她说:“这是事实。”我说:“今天倒挺谦虚的。还有,你不能用北美的资料去做文章,这你也没有优势,承认不?”她说:“我才来一年多,北美我知道多少呢。”我说:“承认就好,那你说怎么办?”她说:“那我用这里学的理论分析中国的事情。你一说我心里就清楚了,我题目也有个方向了。”
她又伏到那里去看那些材料。到了晚上忽然拍了桌子说:“有了有了!”说着拿了一篇给我看,是分析中国现代离婚状况的历史变迁的。我说:“这也算民俗学吗?”她说:“算的算的,我把它转一下就变成我的论文了。”我说:“硕士论文,混一混就过去了。”她说:“至少要保证拿到文凭。我自己写一点,这上面抄一点,再到图书馆抄一点。我最会抄了,别人不查对原书看根本看不出痕迹。谁会那么勤快找原书查对?几次作业都是这样得了A。”我说:“这篇论文还不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她说:“你答应我了你又提它,你不是男子汉。”我说:“那就把我的脑袋剖开把那件事拿走好不?她说:“今天我再向你赔一次礼好不好?”说完诡秘一笑。
她把桌子让给我看书。有些单词我带的小词典查不到,就用她的《新英汉词典》。她说:“这多不方便,读研究生没本正经词典。要你家再寄一本来。”我说:“值得寄吗,豆腐盘成肉价钱!”她说:“说起钱又触到你的痛神经了。”我望她一眼,她不再说话。过一会她扔了手上的书说::今天早点睡好吗?”我说:“才十点钟呢,十点钟!”她说:“你就今天一次早点睡不行吗?”我在心里笑着,嘿,倒撒起来娇来了。于是说:“睡觉的时间也要由你决定。”
我从水房回来,她已经睡到毯子里去了。我说:“这么快就睡了!”她把毯子拉到眼睛下面,只露出双眼追随着我,一声不吭。我说:“我再看几分钟书引一引瞌睡来。”一边把衣服脱了,钻到毯子里看书。偶然瞟她一眼,她望着我,眼神好奇怪。我说:“把鼻子嘴巴露到外面!里面有香气吧。”她不做声把毯子退到脖子处裹紧,眼睛依然望了我。
我用眼角去瞟她,想起自己很多次在灯下观察她的侧影,她现在也观察我了,只是不知她想什么。恐怕她看久了,也发现了我的毛病。又想着还不至于,自己鼻子长得直,还经常跟她开玩笑说是“国标的”,以前的侧影相张张都成功。看她眼神怪怪的,想问一句,马上又觉得没意思,搞不好又引出“喜欢不喜欢”这种永无休止的令人难堪的话题。在这世上有很多男人,他们对婚姻生活已经麻木疲惫甚至厌倦,在内心渴望有一种出人意料的艳遇再次激发起如火的热情;但他们在妻子永无休止的追问中,仍然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千百遍不厌其烦地回答那些毫无意义的追问。我做不到这一点,我被追问着说出那些缠绵的话,就会感到心里受了损伤。我觉得那些花言巧语说了出去虚伪透顶可笑之至,飘在空气中有一种金属般空洞的轻响。虽然我也明白,那些话尽管已经重复千百遍,在妻子的耳中却永葆青春。我内心那种执着的清高,阻止着我违背自己的意志去逢迎他人。有时在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势下,偶尔说了几句,脸上就热烘烘地发烧。
我打着哈欠说:“好瞌睡了。”马上又意识到这话说漏了嘴,又说了她最不喜欢听的一句话,于是默默熄了灯,一片浓黑马上布满了四壁。在黑暗中我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在夜的掩护下,我可以自由地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我在睡觉之前经常有这种期待,这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我忽然听到了一阵沉重的吸气声,渐渐地化成了一阵抽泣。我吃了一惊,翻身去摸思文的脸,湿漉漉的一片,显然她已经默默地哭了好久。我把左手伸到她脖子底下去搂她,心忽地“咚”地一跳,我的右手顺着她的肩膀一直摸了下去,天啊,原来她赤裸着身子躺在这里,而我却根本没有去碰她一下!
我身子挨了过去说:“思文,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怎么不告诉我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原谅我好吗原谅这一次,你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