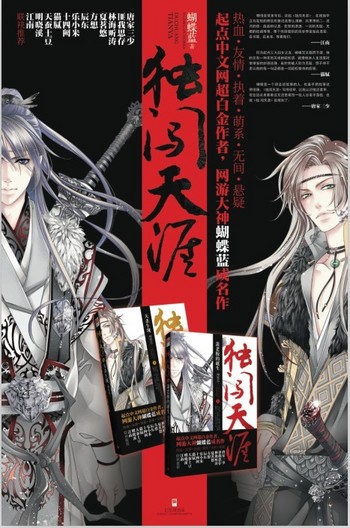曾在天涯 作者:阎真-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邢该幻蚜礁龆逡幻兜牡鋈ィ涯切┪宸忠环值奶统隼矗终坪掀鹄匆〉没┗┑南欤职延沂帜蟪梢桓隹招娜罚侔涯切┣〉没┗┑南欤煜蛄怂K呱侠丛谖胰废律炝诵∈帧N胰糜脖乙幻兑幻兜卮邮址熘新┫氯ィ柯┫氯ヒ幻锻6僖幌拢ハ硎苣且簧嵛⒌拇嘞欤睦镉凶乓恢盅餮鞯目煲狻S幸幻抖宓穆┑剿种形也趴醇炝俗笫窒胱セ乩矗『咽忠荒舐#钡娇诖チ恕N乙∫灰∪坊瓜熳牛稚炝耸帧W詈蠹父鑫彝涎幼牛晕挥辛耸窒胨趸厝ノ矣致┫氯ヒ幻叮詈笪沂种锌樟巳栽谒中纳闲牛茸偶挥卸玻醚实哪抗馔盼摇N衣趴烦恍λ担骸癗o more。”他说声“Thanks”,就马上跑开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计算着刚才大概送出去了有一块钱,有点后悔起来,但又觉得一块钱也值得,到底还是值得的。
(以下略去1800字)……
我正策划着怎么把发豆芽这件事好好做一下,这天思文回来兴冲冲地说:“今天有好消息,真的好消息。”我问她她不肯说,要我猜。我说:“会有什么好事轮到我?最大的好消息就是豆芽有人要了。”她还要我猜。我想着是不是奖学金有希望了,却说:“别弯弯绕了,你!”她说:“你只管往最好的方面去猜,胆子大一点。”我心想,你弯弯绕我也绕弯弯,于是说:“那一定是家里有信来了。”她摇头得意地笑。我猜来猜去就是不猜奖学金的事,她自己忍不住了说:“奖学金得了!”我问:“你见到逊克利尔啦?”她说:“见了!”逊克利尔是历史系主任。这些日子思文一直与逊克利尔联系,总是告诉他说,高力伟就会来加拿大了,却不让我出面,怕一见面我的英语露了底就没有希望了。在国内时我按历史系的需要设计了课程,编造了成绩单,又在杂志上找一篇论文请别人翻译了自己抄一遍,把中文原文上别人的署名用自己的名字贴了,复印后作了技术处理再复印一遍,毫无痕迹,然后几样东西一起寄出,得了录取通知。没料到现在奖学金也有了。思文说;“逊克利尔一见我就说,keep smile ,我知道奖学金有了,马上告诉他你昨天已经来了。明天陪你去见他。”我沉默不语。她问:“又怎么呢?”我说:“我的英语出不得场还是出不得场。结结巴巴的英语也讲不来倒敢去见他,那不是不要脸吗?”她说:“我已经说了,你的口语不好,读和写没有问题。”我说:“那又能骗几天,暴露是迟早的事。外国人他再也想不到,成绩单和论文还可以编造,连文凭是造出来的还不知多少,我至少还有文凭这一样东西是真的。”她说:“现在都定下来了,你再出面也不怕了。”我说:“我心里畏怯,压力好大。别人在心里笑呢,这种水平还读研究生!我一辈子也没做过这么不要脸的事!”她说:“你呢,你呢!你那张脸是什么脸,倒比总统的脸还威武些!你那么多自信都到哪里去了,恨不得就吹口气把你吹起来。反正人都不认得,你怕什么怕!”我说:“我跟自己心里说,不怕,不怕,可还是怕,这是没办法的事。”
她生了气说:“跟你搞好了现成的还不敢上阵,那现在连我都要靠你这个男子汉怎么办?”我心里一动,象有什么东西要拼着冲出来,又象被什么压住了,吸一口大气把闷气强压下去。她说:“出国,拿到奖学金,别人拼了半条命才得得到呢,你倒是坐在这里就有了。好多人要他少活十年他也会愿意!生在福中要知福。”我说:“好怕听不懂课,丢了中国人的脸。”她说:“别想着自己就代表了中国人,你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英语不行不会学吧!万一拿个文凭也好向国内交待,万一不行了退出来再找工作,就当是拿了钱学几个月英语,进语言学校还要交钱呢。”我心里沮丧得要命,豁出去说:“明天一定去,坚决彻底去!大不了不要我,会死人呀!”思文笑了说:“看,看,这个人!要你去读书又不是要你去上刑场,有那么可怕吗?”我说:“只是我又欠你的了。”她上来捂了我的嘴说:“你我是什么人,说什么欠不欠的!”她就在我身边。我想一把搂了她,含蓄地表现一下感激,可心里那鬼鬼怪怪的力量在反抗着。她顺势在我腿上坐下来,搂了我的脖子撒娇着说:“只要喜欢我就什么都有了。”我抱了她倒象抱了什么,别别扭扭着很不自然。她凑在我身边说:“到底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也应了说:“天无绝人之路。”一下子我想起二十年前,文革中学校不上课,我和另一个孩子去捡玻璃卖钱,有一天看见一整块玻璃碎在地上,欢呼起来说:“天无绝人之路。”都二十年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正想着思文仰了脸问我:“又怎么呢?”我掩饰着搂紧了她,在她肩头一下一下拍着。她闭了眼一动不动。看看她的脸,我想,不知别的男人是不是也象我一样,没了心理优势就没了情绪?现在我是死鱼一条了。有什么办法,我想活,可活得起来吗?
十一
见到逊克利尔把奖学金的事最后定了下来,但见面时的尴尬我事后还心虚了好久。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逊克利尔从安乐椅上转过身来,我按照思文在门外交待的,说:“Nice to meet you。”又上去握了握手。他也不起身,指指沙发要我们坐,思文坦然坐了,我也在沙发的边沿坐了,欠着点身子,似乎这样就能表示一点谦卑,对自己的资格不足有点弥补。思文跟他说话,说得很快听不明白。我竭力想去听懂,又装作明白了似的不断微微点头。逊克利尔两个指头不停地在桌面上敲着,目光转向我的时候,进去的双眼象是在很远的地方审视我,我鼓了勇气坚持着迎了他的目光也不避开,仍然点头微笑。墙上那幅东方仕女图,是去年跟思文在王府井买的,不知思文什么时候送给了他。我装着去看那幅图避开逊克利尔的目光,怕点头点不到点子上。思文说话时很快地夹了一句中文:“别看着别的地方。”又把英文很快地说下去,眼睛并不望我一望。我又把目光移过来看着逊克利尔,点头微笑。有一次我得了机会以为听懂了,插问了一句,问原来那个得奖学金的人还会不会来?思文挨着我脚的那只脚用了点劲给我一个提醒,我再也不敢插话。逊克利尔拿出一封打印的信,飞快地签了名递给我,一边吩咐什么。我听不懂但知道是告诉我奖学金的事,站起来双手捧了,微笑着深深点头,一边说着Yes。
出了门我问思文碰我一下是什么意思,她说:“我急得要跳!他刚说了那个人不会来了你又问。他说你听力还是有问题,要我快帮你提高。”我说:“读小学我也许差不多,读研究生!他以为英语几个月就可以过关的!”她说:“他又没欠你的,你还抱怨他。”我说:“怪只怪自己争不了这口气,还怪谁呢?拿了这份奖学金通知我心里铅球一样坠沉沉的。”她说:“怎么办你自己想好,该做的我都做了。路在你脚下你自己去走。注册就在这几天了。千辛万苦得来奖学金,你又犹豫了。”我说:“真的我宁肯去做工。”她说:“做工好啊,可谁要你呢,找工作你试也试过了。”我心里憋着气默默走着,走到公路边,在来来往往的小轿车喇叭声掩护下,我冲着天空喊着:“它妈的它妈的它妈的!”思文冷冷瞟我一眼,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笑意。我装作没有见,心里却是恨恨的。走了好久思文说:“反正就是这样,你自己决定,不想读书在家里学几个月英语也可以。到了北美英语反正要过关的,反正又不是没有饭吃。”我说:“是的是的,反正加拿大没有饿死人这一说。”心里想着:“吃你的饭,这口饭我能咽得下去吗?”
思文不再提这件事,每天仍然是早出晚归,我决心在注册之前再挣扎一下。每天思文一去了学校,我就去买份报纸,看上面的招聘广告。看了三天有几个稍微沾点边的,我鼓了勇气打电话过去,又结结巴巴讲不清楚。放下电话我就跟自己生气,对了镜子呲牙咧嘴地作出种种嘲笑的表情,又指了镜子里的影子,手指一点一点的,在心里骂那影子是猪是狗,是豆腐渣,又撮了嘴唇作势要唾。骂了自己又伤心起来,几乎要落泪,闭了眼强忍住了。还有两次,通话后我说要找工作,对方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懂,没等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心里象做了贼似的跳得厉害。又想象那边的人拿了电话筒在发怔、生气,觉得自己还有点用,能够害人,又偷偷地笑。想来想去唯一的出路还是找中国餐馆,就把电话簿上中国餐馆的地址抄了满满一张纸,标了东南西北几个方向,骑车过去挨家去问。有时推门进去,应待小姐以为我是食客,笑盈盈迎上来引我入座,我连忙申明是来找工作的,马上就收了笑脸,淡淡地往里面一指。这时我心里象被钝器打了沉重的一下,隐隐作痛。心想,我是来找工作的,又不是来讨饭的,恨恨的想踏这些香港台湾来的小姐一脚,骂一声“狗”,又不漂亮,傲什么傲呢。那种神态一次次打击了我最后一点信心,明白了找工作原来是一件讨人嫌的事。每次被拒绝我都羞愧得无地自容,觉得自己一钱不值,根本就不配来问什么工作,也不配在这个世界上活什么命。
有一家老板会说国语,问我会不会炒菜,我回答说会。他见我回答不坚决,很和气的一笑说:“跟家里炒菜不同呢。你在餐馆做过大厨没有?”我只好说没有。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厨师下个月去多伦多,想招一个新的。我厚了脸皮说:“让我试行吗,不行了你把我炒了我不说二话。”他说:“冒不起这个险呀,顾客一次没吃好就再不回头了,中国餐馆太多了。”我看他好说话,问他要不要豆芽。他说有人送了,要我留了电话号码,下次要了打电话给我。我说声谢谢准备走,他说:“不忙坐会嘛。”又问我在国内干什么,我说:“教书的。”他说:“同行,同行!”我以为他是台湾人,他告诉我是上海人,姓顾,都来有九年了。又说:“听说国内变化很大,九年没回去,也不知上海怎么样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九年前上海什么样子,这次在上海上飞机看了,很繁华的。”他眼睛向上翻着,似乎在想象着上海的繁华,自言自语说:“该回去一次了。”我想跟他拉拉关系留条后路,干脆多呆一会,说:“你当老板了,回去威风很大呢,现在国内摸着外字的边就吃香,什么时候你也回去把威风抖一抖。”他说:“有这么个理想,过几年吧。”我说:“你们回去还不容易,今天想走明天就到上海了。”他说:“走不开呀,自己的生意要自己守着,一下不守就砸了再扶不起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早上十点晚上十二点。No choice 。”我说:“要是我有这赚钱的机会,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可以,有钱赚了还睡什么觉!”
他又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是鲜水路二十一号,他惊奇地说:“是吗?九年前我刚来就住在那里,八二年博士毕了业才搬走。”我有点激动说:“那春夏秋冬的年历画是你贴的?”他说:“山水画,还在吗?都六年了!”又摇摇头,“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