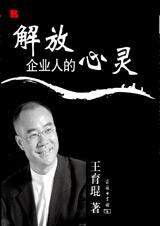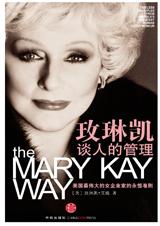奧德利夫人的秘密 [英]瑪麗.伊麗莎白.布雷登-第6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用法语说道,一面用她的脚轻叩着那呈亮的地板。
“啊,不,夫人,”那女人锐声否认道。“这是个最最舒适惬意的机构,人们在这儿自得其乐──”
她的话,因这个最最舒适惬意的机构的头儿的到来而打断了,他手里拿着已经打开了的、莫斯格雷夫医生的信,面露喜色地走进房间里来,喜气洋洋的微笑使他容光焕发。
得以认识先生,他是多么荣幸,他可没法儿说了。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准备亲自为先生效劳的,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愿尽心竭力为先生去完成的,既然先生是他的熟人的朋友,十分杰出的英国医生的朋友。莫斯格雷夫医生的信已经简要地把病情通知了他,他放低声调告诉罗伯特道,他已经准备好负责照料这位迷人而十分有趣的──夫人,──夫人。
他客气地擦擦手,瞧瞧罗伯特。奥德利先生第一次想起来了,医生曾经向他建议过,要为他所护送的薄命人用一个假名。
他装作没听见老板的问题。想到一大堆姓名看来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从中随便选一个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然而奥德利先生突然变得把他所听见过的任何人的姓名都忘记了,却只记得他自己和他的失踪的朋友的姓名。
也许老板觉察、理解了他的窘态。无论如何,他来给他解除窘迫了。他向那接待他们的女人转过脸去,喃喃地说了些关于14号套间的话。女人从挂在壁炉台上方的一长排钥匙中取了一个钥匙,再从房间角落里一个托架上取了支蜡烛,把它点亮了,便领着大家穿过铺着石头的大厅,走上一个宽阔而光滑的、打过蜡的木头楼梯。
英国医生已经告诉过他的比利时同行:为了使那位委托他照料的英国夫人生活舒适,不论作什么安排,花钱多少是个次要的问题。根据这个暗示,瓦尔先生打开了一套富丽堂皇的房间的大门,其中包括一个走廊,(地上铺着黑白相间菱形大理石,可是廊内黑得阴沉沉的、象地窖一般;)一个雅致的会客室,(里边挂着暗淡的丝绒帷幕,呈现出一种丧葬的光采,那可并不对振奋心情特别有利;)一个卧室。(里边有张制作得很奇怪的床,看来盖在床上的东西都没有个出入的口子,除非用一柄小刀将床罩划破。)
爵士夫人沮丧地瞪眼望着这一系列房间,在唯一的一支蜡烛的逐渐微弱下去的残光里,房间显得够凄凉的了。这孤独的烛焰,本身就是苍白得象幽灵一样的,它又繁殖出了成倍的更加苍白的幻影幢幢,在房间的各个地方闪烁明灭;在上过蜡的地板和护壁板的朦胧深处闪烁,在玻璃窗上、穿衣镜里闪烁,在装饰房间的大块闪光物体上闪烁。爵士夫人曾把后者错认为昂贵的大镜子,其实它们不过是用呈亮的洋铁皮作成的、可怜巴巴的仿制品。
在这破旧的丝绒、黯然失色的镀金虎饰和上蜡擦亮的木头所构成的一切已经衰败的豪华陈设之中,这女人一屁股在扶手椅子里坐了下去,双手遮掩着自己的脸。白皙的双手,在手指附近晃动的钻戒的璀璨星光,都在灯光幽暗的房间里闪闪生光。她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绝望、生气、愤怒;而罗伯特和法国医生则退到了外边的房间里,互相低声谈着话儿。英国医生已经替奥德利把话都说在信里了,而且表达得远比他亲自说的还要体面优美,所以他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他在大伤脑筋之后,终于想到了泰勒这个姓名,要用这个又安全又简单的姓名,来代替那个唯独爵士夫人有权使用的姓名。他告诉法国医生,这位泰勒夫人是他的一位远亲──她从她的母亲那里继承了疯狂症的遗传因子,正如事实上莫斯格雷夫医生已经告诉瓦尔先生的:她已经显示出了隐藏在她脑子里的潜在因素的某些可怕迹象,然而还不能称她为“疯子”。他要求尽量温柔体贴地、富有同情心地对待她,让她享受一切合乎情理的任性放肆;但他让瓦尔先生牢牢记住: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她离开这个房子和这个场所,除非有个可靠的人保护着她,而这个人要对她的安全负责,不可任其走失。他只提出另外一个强烈要求:据他了解,瓦尔先生本人是位新教徒,──医生鞠躬──希望他能同某一位温和仁慈的新教牧师作好安排,以便为生病的夫人取得精神上的忠告和安慰;罗伯特还严肃地补充道,夫人特别需要这种方便。
这一切──以及有关金钱支付的必要安排,由奥德利先生和医生两人随时随地直接解决,无论如何用不着任何代理人的帮忙──便是这两个男人谈话的范围,大约只用了一刻钟光景。他们重新进入卧室时,夫人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姿态,带着钻戒的双手仍旧遮掩着自己的脸。
罗伯特俯下身,凑到她耳朵边低声说话。
“你在这儿叫泰勒夫人,”他说,“我想你也不愿意人家知道你的真姓名。”
她只是以点头回答他的话,甚至连双手也没有从脸上放下来。
“夫人将有一个完完全全专门为她服务的侍者,”瓦尔先生说,“夫人的一切愿望都可以得到遵从;她的一切合情合理的愿望,那当然是不用说的,”瓦尔先生优雅地耸耸肩膀,补充道,“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使夫人在维勒布吕默斯的盘桓舒适惬意,既是舒适惬意,同样又是大有种益。住院的人们,愿意时,就一起用餐。我有时也同住院的人一起用餐;我的副手,一个聪明高尚的人,经常和大家一起用餐。我跟我的妻子和子女住在这儿的一个小楼里;我的副手住在院里。
夫人可以信赖我们会作出最大的努力来保证她的舒适安逸。”
瓦尔先生擦着手,容光焕发地对罗伯特和他所护送的人微笑,正在反来复去说许多意思差不多的话;这时,夫人突然站了起来,从脸上放下戴着钻戒的手指,人站得笔挺,十分愤怒地叫他闭嘴。
“你替我走开!”她咬紧牙齿嚷道,“你让我和这个带我上这儿来的人单独谈谈。”
她用一个非常专横的姿势指点着房门,动作十分迅速,她举起手来时,她胳膊上的绸衣服发出一种羽翼扑动似的声音。她说话时,法语音节嘘嘘地从她牙齿缝间迸射出来,似乎比她一向说惯的英语更加适合她这时的脾气和她这个人。
法国医生耸耸肩膀,走到外边儿黑暗走廊里去了,他嘴里咕咕哝哝的说些“一个美丽的魔鬼”的闲话,还做了个配得上“战神玛尔斯”的手势。爵士夫人迈着快步走到卧室和会客室之间的房门边,把门关上了;手里还握着门上的把手,她转过身来瞧着罗伯特。奥德利。
“奥德利先生,你把我带到我的坟墓里来了,”她大声叫喊道:
“你卑鄙地残酷地使用了你的权力,把我带到一个活人的坟墓里来了。”
“我办了件我认为对其他的人公正、对你仁慈的事情,”罗伯特平静地答道,“在乔治。托尔博伊斯失踪和城堡旅馆发生火灾以后,如果我还让你逍遥自在,我就是社会的叛逆了。我把你带到了一个地方,那儿的人们对你的经历一无所知,他们无权奚落你或责备你,你会得到他们和蔼仁慈的接待。爵士夫人,你将过一种安宁平静的生活,在这个天主教国家里,不少善良神圣的妇女自由自在地接受了这种生活,而且幸福地坚持到底。你在这个地方生活,其孤寂不会超过小说中某个国王的女儿,她为了逃避当代的罪恶,乐于托庇于一个象这儿一样安宁的宫室。你犯了罪,无疑这是我要求你作出的一点儿小小的弥补,这是我要求你完成的一项轻微的仔悔。在这儿生活和悔过吧;没有人会加害于你,没有人会折磨你。我只是嘱咐你,悔过吧!”
“我不能悔过!”爵士夫人大声喊道,猛烈地把头发从白皙的前额上推开,张大眼睛盯住罗伯特。奥德利,“我不能悔过!岂不是我的美丽把我弄到这种地步的吗?我千方百计、出谋划策来保护我自己,我在漫长的死寂的夜间睡不成觉,颤栗着想到我的危险,难道是为了落到这种地步吗?既然这种地步就是我的下场,我还不如立刻屈服认输的好。我还不如在乔治。托尔博伊斯当初回到英国时,就屈服于落在我头上的祸殃,就死心塌地逆来顺受的好。”
她抓住她那羽毛似的金色鬈发,仿佛要把头发从头上扯下来似的。那灿烂闪光的头发,那么高雅地同眼睛的温柔的天蓝色互相映衬的、金黄头发的美丽光轮,归根结蒂,对她可毫无用处。她恨她自己,她也恨她的美丽。
“如果我敢作敢为,我就会嘲笑你,公然反抗你;”她大声喊道,“如果我敢作敢为,我就会杀了我自己,向你挑战。然而我是一个穷苦的、可怜巴巴的、懦弱的人,一开头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害怕我母亲的可怕的遗传病;我害怕贫穷,害怕乔治。托尔博伊斯,害怕你。”
她沉默了一会儿,但她仍旧守在门口的老地方,似乎决心要留住罗伯特,随她高兴要把他留多久就留多久。
“你可知道,我现在正在想什么?”她随即说道。“你可知道,在这房间的朦胧光线里瞧着你的时候,我正在想什么?我正在想着乔治。托尔博伊斯失踪那一天的情况。”
她提到他失踪的朋友的名字时,罗伯特吃了一惊,他的脸在暗淡的光里变得煞白,他的呼吸变得又急又响。
“他就象你现在那样,站在我的对面,”爵士夫人继续说道。“你说过,为了寻找你死去的朋友,你要把古老的府邸夷为平地,把花园里每一棵树都连根拔起。你无需那么大费周折了;乔治。托尔博伊斯的尸体,就躺在菩提树幽径尽头灌木丛林中的那口古井底里。”
罗伯特。奥德利高举双手,在头顶上方互相握紧,发出一声响亮的恐怖嗥叫。
“啊,天哪!”可怕地停顿了一会儿,他说,“我曾设想过种种阴森可怕的情况,可万万没料到最后弄明白的事实真相,竟是这么阴森可怕!”
“他在菩提树幽径上碰到了我,”爵士夫人重新讲下去,用的是跟她自白平生罪恶经历时用过的、同样生硬、固执的语调。“我知道他要来的,而且我也尽我所能地作好了准备,来当面对付他。我下定决心要收买他、哄骗他,公然反抗他;什么条件都可以很快答允,但决不放弃我所赢得的财产和地位,决不回去再过我从前的旧生活。他来了,他责备我在文特诺搞的诡计。他申明,他有生之年,决不宽恕我那使他心碎的谎言。他告诉我,我已经把他的心从胸膛里挖了出来,踩在脚下了;所以他现在没有心来感觉到一丝一毫对我的怜悯之情了。我在世上做的任何错事,他都可以原谅;唯独我对他所做的那一件深谋远虑、无情无义的错事,他是不能原谅的。他说到了这件事和其他许多事情,他还告诉我,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改变他的意图;他的意图就是要把我带到我所欺骗的男人面前,逼我把我罪恶的经历讲出来。他不知道我吃母亲的奶时所接受的隐性遗传因子。他不知道他那么做可能把我逼疯。他刺痛我,就象你刺痛我一样;他铁面无情,就象你对我铁面无情一样。我们是在菩提幽径尽头的灌木丛林里。我坐在井口断裂的石栏上,乔治。托尔博伊斯的身体靠在废弃的绞车上,车上生锈的铁轴在他移动位置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