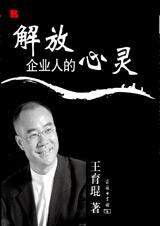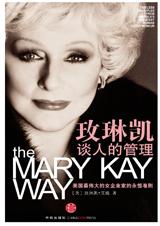�W�������˵����� ��Ӣ�ݬ���.����ɯ��.����-��43����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Ժ�������ü����ж�����˹С��д�˼��仰����������ǰ�ڴ�ʥ�������������ˡ�
����������Խ�ʡ��һ���ʱ�䣬�����������Ƕ̼������������ܾ�ʱ�����������
������д�Ÿ����������ж�����˹��ѯ������������ξ����������Ů�����Ǹ�����С������ƣ���Ϊ���������������˺����ܣ����ء�
�����µ����������Ѷ̴ٵ��»������ϸ��ȴ֪֮���١�
�����Դ����Ρ��ж�����˹�ڡ�̩��ʿ�������������������ȥ����ѶϢ��һ�������ͱ���������ô�п���ж��˵�����ʷ������������ô�ڰ��ظ�Ĩ�������ܾ����ˡ�
�������Ƕ̶̵Ĺ���������ô��ʹ����������飡�ڻ������ҳ���һ�����������ô���������Ǵ�𣬶������ڼ���ȴ��ֵȴ�����˵����������ҳ��߱ض����Եö���ʮ���������ģ����ء��µ���������һ�㣬���������ѵļ�Ĭ���Բ����е���֡������˶������ĵ����¶����ղ����رܿ��ˣ�������ȫ��֪������ͬѧ��һ����IJ�������������Ǵ���û���Ѻõ�һ��ס����Щ���������ʥ�����������Ƶġ�
�����������ڻ��һ������д�������ж�����˹С����ţ��Ǵӹ��ո��آ�ij��ġ������ɴ˵ó����ۣ����ո��ر����������������µĵط�����������������������ո����DZ�Լ�˿�һ��ʱ�ֵ�����ʤ�ء�
�������ء��µ�������������õ籨�ش��������⣬��������������ɵ�����������ʧһ���ʱ�䡣
�����ڶ���ʮ������֮ǰ���ص�㴫�͵���������Ժ�ˡ�
�����Ǹ�����С�����Լ�˿��Ļ����¶�����
�����µ��������յ���籨������һ����ͷ���㵽�˹���ʮ�ּܳ�վ��������һ��һ�����̿��������¶������ر�쳵Ʊ��
����������Х�ŵĻ�ͷ��������������ȥ�ij�����;���������ڻ���ƽ̹�IJݵغ�ͺͺ�ġ���Ⱦ����������������ϼ��۶���������λ����Ĵ���ʦ��˵���ⱱ���ĵ�·�Ǽ��������İ������Į�Ķ���ľ�ɫ������һ�����еĻļ���Ŀ��ʹ���Ķ����ˡ�����֪���е�Ŀ�ģ��ɴ˶�ʹ��Ƭ��֮��ãȻ��Ŀ������ÿ������ѷɫ���٣���ֻ�ǿ�һ�۱�����ת�۲����ˣ�ֻ��ת������ȥ���Ƿ������Զ�������������������ġ�ԶΪ�ڰ��ľ����ˡ�
���������յ�վ�ն�ʱ����ɫ���ˣ����µ�����������;���滹û����ᡣ��һ��Ⱥ���˷�����߰����һ�ѶѲ����͡���������ַ����ÿͱ��˵������м䣬ϡ���Ϳ�ء����Ѱ�˯�أ����˼�����������һ�л����������������֧����ȥ����֧���Ǿ��������¶����������ն�������ı�Եǰ���ġ��������������������ն�������������
�����뿪�ն�վ�����ͷ����Ӵij��ᴰ���ﴵ�����������ɴ˸о����˴Ĵ������ζ��������Ϣ��һ����ͷ�Ժ��г���һ�������ij�վ��ͣ���ˣ��վ����һ����ɳ�Ļĵ��ϣ�վ��ס�������������ѻ��Ĺ�����Ա������һ���ڻ��н�ʱ����һֻ�����̶��������ó����˵�������
����ֻ�аµ�������һ���ÿ��������������ij�վ�³�������������������ľ�ɫ��ȥʱ������ʦ��û�����ü��ѻ�㱵���˼��������������������Ƥ������������������Ƥ�����ں��q�q��������У�ֻ��һ֧��������������������Щ��������
�������Ҳ�֪�����������ޱ�Զɭ�ֵش��������Ƿ����ҽ�ҹ�����е��¶���İ�����������������ںڰ����Ŀ���ӵ�ʱ�������������
��������һ��������Ա���˸��к�������ָָ�Լ�������Ƥ����
�������ɷ��������Ұ���Ƥ���õ�������ù�ȥ�𣿡����ʩ������ҵ���˼��˵������������Ƕ��㵽һֻ�ô�λ�Ļ�����
�������˿�������Ƥ��ʱ������Ц�ˡ�
�����������������Ҫ�Ļ����Ҹ�˵������ʮֻ��λҲ��õ��ģ���
������˵������һ�������ʱ�䣬�����ڻ����¶�������̫æµ��������ߣ���������
�������˷�ѳ�վǽԫ�ϵ�һ��ľ�Ŵ��ˣ����ء��µ�����ͷ����Լ������һ��Ƭƽ̹�Ĵ��ľ��Ϸ����ɫ��ƺ����ƺ������һ����ķ��ν�������q�q�����ڶ�ҹ������������������ǰ����ŨŨ�ĺ�ɫ�������ֻ�����������ŵƵĴ��ӣ��˴������Զ���·��Ǻڰ���ָʾ����Ļ���űꡣ
����������ά�������ùݣ������������˷�˵������������������ÿ�ӵ����ʢ�������ֱ�������ŵġ���
�������ǹ�ͺͺ�IJݵء�������Ӱ��ľͷ��ͤ���Լ��ù���ڳ����Ĵ��ӵ���Щ����ϣ�ȷʵ���������ĵ���������õ�������������ط�Ѱ�����ֵ����־������ء��µ���������Ը�����Ű��˷���������κ����飬ͬʱѱ���ظ����������߽��ǼҴ��ùݱ��ϵ�һ��С�š�С��ͨ��һ�����ʵľưɼ䣬������ļ��Ϊ���ݲ��ߵĹ˿��ṩ�۸�ʵ�ݵ����ϣ��������ȥ����Щվ�ڴ����ﴩ����ױ��ĵ����ߵ�������
�������������͵Ķ�����ù������µ�����ȴ���٣��ù��ϰ������д������߽���һ����������ķ��䣬��߷��Ź������һ���ľ���Ӻ������ص��ӵ����ӡ��ϰ����������֮Ϊ�����ҡ�
�����µ����������ڿ�����¯��Χ���ĵط����������ε�˫������¯ǰ��̺�ϣ���ʱ�ϰ��ò��������ú����ͱ�˼��£����к��Ļ����¡��¡������ֱð�����ڵ��̴���ȥ�ˡ�
���������������Ҫһ���ľ��ķ��䣬�����������ϰ忪�ڵ���
�����������ˣ�лл���������䵭��˵��������ǰ�ⷿ�俴��ȥ���ľ����ˡ���������ҽ�һ�����ţ�һƷ��ѩ���ƣ��Ҿͺܸ�л�ˡ���
��������������������
�������������в�֮ǰ����ͬ���ļ����ӣ��Ҿ��Ӹм�֮���ˡ���
�������dz����⣬���������ϰ������º͵�˵������һ��֮�У�����������Ǽ����Ŀ��˼��٣��������Ƕ����õ���ʿ������������Ȼ�����ġ����ڻ����¶������������ἰ���������κ�����Ҷ����������ṩ�����ϰ岹���������֮�����������ھưɼ���۵��DZ�����ʤ���ֲ��еĻ������ҽ��dz����⩤����
���������Ҳ���֪�����ڻ����¶���������������κ����飬�����ز���������ϰ�����ϲ�����ʾ���顣����������ѯ�ʼ������⣬�ǹ���ijЩ���������ס�������ǵġ���
�����ϰ�Ϲ�Ц��������������������СС���۵����о����С�������г�����ֻҪ�µ��������������������Ҫ��Ļ���
���������������ס����ˣ��������ʵ���һ��ӿڴ����ͳ��ʼDZ�����������ҵ����������Ļش����������ʼǣ��㲻����ɣ���
������һ��Ҳ�������������ϰ������������µ�ׯ����Ҫ������ʾ��������ϲ֮�顣�������ṩ���κ�����������ܼ��м�ֵ���ǵģ�лл���ˣ���������˵��������˶Է��ĶԴ����������������ס�˩�������
������ס�������ˣ���������
�����������������ס������ˣ���
��������һ�������ʮһ�����������ڴ���ǰ�����ںն������⡣
�����ⴱ����������ס������ǰ��ʮ�²ſ����ġ���
��������ɼǵ�һ��������ξ��������������������ʱ���Ǹ����н�ġ���
��������������������ξ�𣿡�
�������ǵģ�ͨ����������������ξ���ҿ����Ǽǵ����ġ���
�������ǵģ���������������ξ��������õĹ˿�֮һ����ʱ�����ⷿ������ĥ�ƻ裬������ʱǽͷ�dz�ʪ�ģ������Ǽ������ڹ���һ���Ժ���ܺ���ǽֽ������Ů������һ��������٣�������һ�������ʥ����ǰ���������һ��������ġ������������Ļ飬������Ȼ�����ǵ�ŷ��½ȥ�����������£��ٻص���������ǣ�����λ��������Ӥ����һ�������ڣ���λ�����㶪�������ܵ��Ĵ�����ȥ�ˡ�
����������ڻ����¶�����Ϊ�䶯�������������˩������˩����Ұ��������˩�����
�������ж�����˹���ˣ���������ʾ����
��������Ȼ�����������ж�����˹���˵õ������¶������ǵļ���ͬ�飬�������һ�Ҫ˵��ȥ����Ϊ������ʮ�ֿ��Σ���������ô�����Ӯ�����ĵ���������������ÿ����ʶ�����˵ij������
���������ܸ����ң�����������������Ů�������ж�����˹�����뿪����֮�������ڻ����¶����ж���أ��������ʵ���
������Ŷ�������˵�����������������ϰ��˼��һ�����˵��������û����ȷ��˵���ж�á���֪�������������������������������������������Ů�������������ˣ�������������һ����ʮ������������С������ƭ�ˣ�����˵�������Ǵ��˶�ò��뿪�����¶����ġ����ǰͿ��������ܸ�����ģ����������ϰ����ز������
�������Ϳ������ˣ���
�������ǵģ��Ϳ��������DZ���ʮ�ߺŵķ���������������������Ů����ס��������������Ǹ��Ͱ��ġ�˵��˹�ĵġ�����ĸ��ˣ���������Ҫ��֪�����κ����飬�ҹܱ������������ġ���
������лл�㣬������ȥ�ݷðͿ������ˡ����һ�©����һ���һ�����⡣���������ж�����˹���ˣ�����ϵó������𣿡�
��������Ȼ�ϵó��ģ��������������ϵ��ҵ�һ������Ů��һ�����а��ա���
�������ء��µ����ѰͿ������˵ĵ�ַ�������ıʼDZ�������һ�˳������ˣ�����������ѩ��ƣ�����һ֧ѩ�ѣ���ص�����������ȥ�ˣ��Ƕ��Ѿ����˸��𣬹������ܡ�
���������þ�˯���ˣ�������������ϵ��Ƕ��ģ��������ƣ��֮������������˯��������ȵ�˯�ߣ������ü����ڶ�ɳ�ĵ����������ֵ����ʣ������IJ�����ƽ̹�ĺ����ϵ����ع���������Щ�������������������û�л��ֵ�������������������˼�룬�������ϵ��Ա�ò�������ʽ��������������˯�����ӵĻ�����������ϴ����������ڹ���Ҳ�����ܴ��ڵĻ��������ָ�˯�������ǵõ���ʵ����������ij���������ʵĹ�ϵ��
��������Щ���˷��յ��ξ���������µ���ׯԺ�ĸ�ۡ���Ӱ�����˹�IJԴ������Ϻ������������Ա������������ˣ���ͺͺ�ء�������������ڻ����ı��������ϣ��ܵ�������Ѹ���dz�����в�����˷·��ھۼ�£������ӿ���ϣ����������Ȱ���������ۡѹ��������Ҫ�����弤�÷��顣���⼱��ææ�IJ��˷������������ӽ����ûʵĸ�ۡʱ��˯���߿���һ�������ǰ����������ɫ����ĭ�������������������������Ǿ�ʿ���˱����һ�������㣬���к������IJ�����������ڲ�������Ĵ��棬���д��������ƣ�����ڵ�īˮ��Ҫ�ڣ�����ڵ�ҹ��ҪŨ�����͵͵�������˯���ߵ��۾��ϣ����������������������ĵ�ƽ��ʱ������������������طֿ��ˣ��ڰ��г�����һ����խ���ѿڣ�һ�����ߴ��ѿ�к�룬��������������IJ����ϣ����������أ��dz�������ȴ�ˣ������ǹ��ϵĸ�ۡ��ȫ���ι̵������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