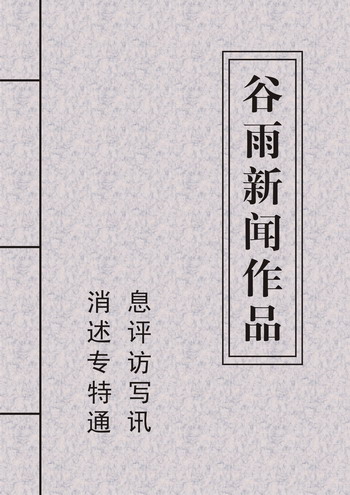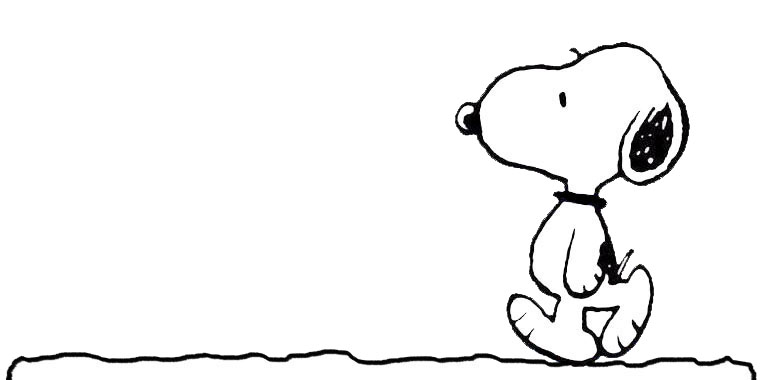作品评论-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就会了解,王雄之所以猛吃一惊,是他猛然之间发现丽儿长大,突然她不再能十分符合凝固在他心中的“小妹仔”的影像了。果然不久她真的开始摆脱他。丽儿一天长大多少,两人间的距离也就增加多少。作者用丽儿拒坐三轮车上学的事实,来影射她不再需要“宫车”;她已开始伸向尘俗世界,不肯再接受王雄精神上的卫护。
丽儿之开始舒伸向俗世,在小说情节里是埋伏着证据的。入中学之前,她是百分之百的真,百分之百的纯。她的心,如同一块洁玉(“活像一个玉娃娃”),不掺杂一丝尘世的污垢,喜怒哀乐完全出乎自然。她表现的,是天性,而非人性。她对王雄的感情,也不混杂丝毫世俗价值观念,两个人是完全平等的游伴。然而进入中学后,她开始“长大”,像所有身心健全的孩子那样长大。她开始接受俗世的价值观念,因王雄只是一个仆佣而变得看不起他,练习英文时指着他说“You are a dog”。又因王雄长相丑陋(“像一头大猩猩”),怕被人笑话,而拒绝他的保护。
丽儿脱离王雄后,王雄变得格外沉默,孤独徘徊花园内,完全退缩到自己里面去了。他不修边幅,“满脸的胡子渣,头发长出了寸把来也没有剃,全头一根根倒竖着,好像个刺猬一般”。把根根头发倒竖的头颅,喻为“刺猬”,诉诸视觉,异常生动。但作者亦存心用“刺猬”这个意象,影射王雄的心理状态。刺猬是极端孤独的动物。极端内向的动物。它素食,不侵犯别的动物,但受到重大威胁时,会为了自卫而冒死反伤威胁者。在这样一个看似平易无奇的意象里,作者暗示出王雄当时的绝对孤独,并隐约预示王雄对喜妹威胁的反攻。
然而这篇小说的首要意象,是舅妈家的那个大花园。我们注意到,故事情节多半在这个宽敞的花园里进展。一开头,作者即通由叙述者向我们交代说明,舅舅生前是做大生意的,死时留下了一大笔产业。所以我们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人口拥挤的台北市,舅妈母女居然住得起这么一幢“三百多坪的大花园洋房”。让我们看看这大花园大致是什么样子:
舅妈家的花园十分宽敞,新植的草木花树都打点得非常整齐,中间是一块绿茸茸的朝鲜草坪,四周的花圃里却种满了清一色艳红的杜鹃花,许多株已经开始打苞了……那丛芭蕉树……
这里的描绘,以及这之后又几次的描绘,使我们看到一个红颜绿色,一尘不染,充满春日朝气的人间天堂,而故事的大半,实际上也发生在杜鹃花开放的春季,值得注意的一点,即作者每每让童稚的嬉笑与纯真的欢乐,弥漫在这春日的花园里,这人间的天堂里。如此,叙述者首次进入花园,“便听到!丽儿一连串清脆滑溜的笑声”。丽儿把王雄当马骑,“乐不可支的尖笑着”。在绿茸茸草地上,丽儿赤足跳山地舞,王雄也一同蹦着跳着,“在刀”片红红的花海里,载歌载舞起来。小说末段,叙述者听了舅妈的“鬼话”,来到花园,发现杜鹃花异样盛开。这时,丽儿正和一群女孩子在园里捉迷藏,“女孩子们尖锐清脆的嘻笑声,在春日的晴空里,一阵紧似一阵的荡漾着”。
这个大花园,在本质上,可比《红楼梦》的大观园。同样彩色鲜艳,同样整齐美观,而最重要的,同样给人一种印象,觉得它象征永恒童稚与纯真,是一个不被俗世或肉体污染的灵性世界(即连不见在花园走动的舅妈,也和李纨一样是寡妇)。这样一个世界,便是王雄拼命想抓住,想固定为永久的。然而,“肥壮”“肉颤颤”的下女喜妹,时时闲荡花园里,成为这个童真世界的一大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他与她“对峙”,视她为“死对头”,丽儿拒受他的“卫护”后,他变得沉默孤独,但还是不肯放弃心目中的生存使命,每天垂头弯腰在花园里,“哗啦哗啦……灌溉着他亲手栽的那些杜鹃花”,固执地要保持这个“人间天堂”的原貌,不准它枯萎变质。但当有一天,喜妹连浇杜鹃花的水都不给他用,严重威胁到杜鹃花所象征的“生命之春”之持续,王雄再也忍受不住了。正如王夫人因痛恨傻大姐抬得的绣有色情图画的五彩香囊,而大抄大观园,撵出威胁处女童真的“罪人”,王雄对花园里这一个威胁灵性世界的肉性罪人,痛恨之余,进行剿除。于是他掐杀喜妹,把她肉体“掐得一块一块的淤青,她颈子上一转都是指甲印”。
然而,喜妹毕竟没死;“肉”,毕竟不能消灭。这是小说的反讽。由于时间永远前流,一刻不停,没有人能够永久保留完整的童真;没有人能长期保持婴童一般洁白的心,不受世俗气息、世俗价值观念的污染。大观园终必垮废,灵性世界不能常在。即连摆脱了肉体桎梏的王雄“灵魂”,也不能改变这个残酷事实,因为,尽管他(它)暂时把喜妹逐出花园(她吓得逃回宜兰),她还活着,随时可再回来;尽管他(它)天天夜里浇水,呕心沥血,使园里杜鹃花“开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但花之“盛开”,正是“凋落”之前奏,春天一过,季节一变,任凭怎样努力浇水,亦是枉然。故事叙述者,首次见到花园时,杜鹃花还只在“打苞”。丽儿的童稚纯真,那时还有一段前途,但两三年后的今日,“全部爆放开了”的花朵,所能预期的,就只是枯萎的开始。正如园里女孩子们尖锐清脆的嬉笑声,“一阵紧似一阵”,紧到极点,必将绷裂。
如此,我们钻人这篇小说情节结构的外壳,体味到深藏在内的核心——灵肉对立之主旨。然而,关于文中表现这个主旨的隐喻与象征,有一点,特别容易使人困惑。我就此提出来讨论一下。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篇小说里有许多“性”象征。这些性象征,当然,时常随伴代表“肉性”的喜妹出现。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里,潮湿闷热的夏夜,常影射肉欲的饱和状态。叙述者描绘的花园,虽然多半牵联春日,与纯真女孩子的嬉笑,但有一段描写的是夏夜的景象。这时出现的角色,可想而知,是肉颤颤的喜妹。她“摇着一头湿淋淋的长发”,“把那挂烤就鱼往嘴巴里一送”,“躺了下去”。园子里“一轮黄黄的大月亮”刚爬过墙来,照得那些“肥大的芭蕉树叶”都发亮了。面对着这等样难以抗拒的“肉”之威胁,拥抱“灵”而排斥“肉”的王雄,当然只得“霍然立起身来,头也不回……向屋内走了进去”。我们亦注意到,躺在靠椅上的喜妹,摇着一柄大薄扇,“拍嗒拍嗒的打着她的大腿在赶蚊子”。这使我们惊觉:这花园原来也有蚊子!到底不完美,不是人间天堂!(然而,生为人,而非仙,谁能没有瑕疵!谁能不受肉体现实的沾染?)
话说回来,这篇小说的性象征,用在喜妹,固然很可理解,但使人困惑的,是作者在加强暗示王雄对“灵”的执著时,有时也取用隐约的性意象来表征。譬如小说叙述者首次看见王雄时,王雄“手脚匍匐在草坪上,学着兽行,丽儿却正跨在他的背上……腿子……不停的踢蹬”。这种可以使人联想到性行为的描写,呈现的却是不含丝毫肉意的完整的童真。又如王雄被丽儿舍弃后,每天沉默不语,垂头弯腰,“手里执着一根长竹竿水瓢,一下又一下,哗啦哗啦,十分迟缓的,十分用心的在灌溉着他亲手栽的那些杜鹃花”。王雄全神贯注灌溉杜鹃花的含义,当然,是王雄不肯让花谢掉,要抓住春天,长保灵性世界。然而他浇水的方式,用“一根长竹竿水瓢”,“一下又一下”,规律地灌入花丛内,亦可能使人联想到性交动作。此外,作者用“血”字形容杜鹃花,固然是取“杜鹃泣血”的含义,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血”这个字和肉体攸关,而杜鹃花,在这篇小说里,主要是象征生命之春,象征“灵性”。还有,最后王雄对喜妹的施暴,旨意是剿除“肉”,以获“灵”。但他施暴的方式,却像是保弃“灵”,以获“肉”。
然而,这种看似矛盾、令人困惑的灵与肉之交相隐喻,却正微妙地暗示出灵与肉之间极端暖昧复杂的关系。作者显然爱灵而恨肉;他显然认为,没有“灵”的肉身,就像走脱了灵魂的王雄肉尸,算不得“人”,只是腐臭得叫人作呕的“庞大的怪物”。一般人,随着年岁的增添,肉性加重,灵性减少。“肉”与“灵”仿佛相克,“肉”一旦成熟发达,就有歼灭“灵”的趋势(就比如男女之爱,一旦越过肉身结合的高峰,就从互相追寻心灵印证的精神阶段转入共享或共担现实生活的肉体阶段)。然而,可悲的是,我们既然降生为“人”,而非神仙,我们的“灵”就又必须寄生于肉,附属于肉。首先,如果没有男女肉体的交媾,生命根本就无由产生。我们的灵魂绝对不能超脱肉体而独立存在,若要独立存在,就必须像王雄那样,毁灭自己肉身,成仙或成鬼(或什么都没有),而丧失“人”的身分。所以灵和肉,一方面互相排斥,一方面却纠缠一处,不能分解。
佛洛依德认为人类有两种基本上互相矛盾的本能:一种是性的本能,即延续肉体生命的求生本能;另一种更深匿于潜意识内的,是死的本能,即破灭肉体生命的自毁本能。细想起来,佛洛依德的这一大套道理,其实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灵肉之争。灵,要挣脱肉,人就不得不自毁;肉,要继续生存,人就必须满足性欲,不断繁殖。
所以,《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采用的虽是简易文字和客观写实的架构,作者却透由隐喻与象征的高明使用,把人类与生俱来的神秘错综之困境(dilemma)赤裸裸呈现我们面前。
《秋思》的社会讽刺和象征含义
《秋思》是《台北人》中最短的一篇,全文仅四千字左右。这篇小说不但字数少,情节动作的规模也小,整个故事,只是主角日常生活的一小切片,以及她片刻之间的流动意识。
然而这个“袖珍”短篇,却也和别篇一样,具有《台北人》整体的一贯特色,兼具生动的社会写实和深刻的象征含义。《秋思》同时也是《台北人》里社会讽刺意味较浓的一篇。
情节动作之推演,所占的时间,大约不出半小时。主角是上流社会的华夫人——抗日时期一位大将军的未亡人。华将军显然是在抗日胜利之后大陆沦陷之前的一个秋天,在南京患喉癌去世。撤来台湾后,华夫人住在台北,依旧过着富裕豪华的生活。她有一个女儿,住在外国,显然已经结婚生了孩子。华夫人常和同她年龄相近的几个上流社会太大,相聚打麻将。其中一个万大使夫人,由于丈夫不久要外放日本,十分勤快地学着日语,并模仿起日本人的举止风俗来。华夫人免不得和她社交周旋,内心却对她怀着轻蔑与妒恨。
小说开始时,华夫人正准备赴约,到万公馆打麻将。年轻的美容师林小姐,已替她做完脸,正在小心翼翼替她修剔手指甲。两人随意交谈,林小姐十分羡艳地称赞华夫人皮肤的美色,并悄悄告诉她,万夫人不久前动过拉面皮的美容手术,结果不大成功,最近额头又有点松下来了。又说万夫人涂眼圈膏,是为了遮掩眼袋子。两人说着发笑。她们对照着华夫人要穿戴的宝蓝色真丝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