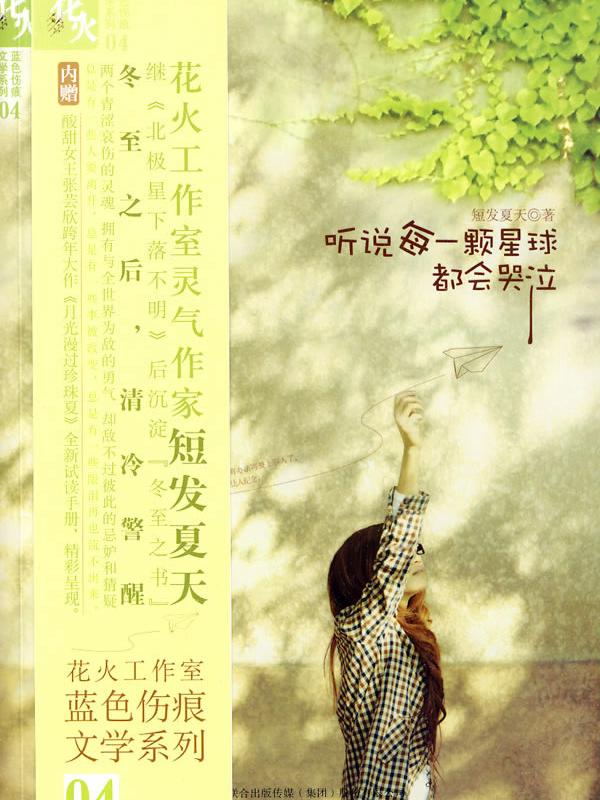一颗铜钮扣 作者:[苏] 列夫·奥瓦洛夫-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ぷ魃狭恕�
至于普罗宁做了什么,我就不敢讲了。如果说热列兹诺夫每天都在参加这种需要他以特别的勇敢与机敏来对付的工作,那么,我想普罗宁做的事情一定就更多了。
可是我每天早上却不慌不忙地起床,喝咖啡,同杨柯夫斯卡亚会晤,到街上去游荡……
我尽量争取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害怕暴露自己,然而我觉得,我根本不适于做演员。
有时我和扬柯夫斯卡亚到早就该枪毙的各种坏蛋家里去做客、有时我也接待那些只提供一些无足轻重的情报的姑娘。不过,这些姑娘都不常来了,她们找我的次数越来越少,无论对她们所提供的情报,抑或是对她们本身,我都不大感兴趣……
不错,生活的表面就是这个样子,假如热列兹诺夫不在我身边,假如我没有意识到普罗宁就在附近,假如我不清楚我的地位的不稳定和动摇性,我就会自以为是上个世纪一位作者笔下的某种庸俗小说中的人物了。
这一年来,我和热列兹诺夫处得极其亲密,我们两人只差一岁,我们两人道去的生活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他是彼得堡一个工人的儿子。他父亲在反对尤登尼奇的战斗中牺牲了。维克多尔·热列兹诺夫在少年时代就认识了普罗宁。普罗宁在他父亲死后就担负了自愿经常帮助这个孩子的义务。维克多尔读了书,学了很多的东西——普罗宁在这方面对他是相当严厉的。维克多尔受过教育以后,因为对他的保护人很有感情,就到国家保安机关工作去了,因而在他青年的早期以及其后的年代里,普罗宁在一切方面都成了他学习的榜样。
我对普罗宁到里加的来历很感兴趣,子是热列兹诺夫就把这件事对我讲了——虽说不十分详细。
指挥部决定派普罗宁到希特勒匪徒后方去,他就自己拟定了投敌计划。
他是用加什凯这个姓到部队去的。至于这个人究竟是谁,知道的人只有团长、团政委和他所在的那个连的连长。普罗宁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时机。有一天,弹片打死了团参谋长,于是他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因为当时那几天也正计划将我军的一批部队调动到新的阵地,所以普罗宁就弄到了一些两天以后就过时的命令,他也记熟了一些部队的配备——而这种配备情况过两天就需改变——于是,他就准备动身了。
军侦察科科长给这个“叛徒”来送行。
为了防备德国人在我们这方面派有谍报员,为了更好地伪装,我方就散布了谣言,说加什凯钻进团部,打死了参谋长,并且偷走了一些机密文件。
等到敌我双方互射停止,暂时平静下来以后,侦察科长和普罗宁就到了连队阵地的前沿。
他们藏在金银树的树丛后面。普罗宁用眼睛最后又量了量他要跑的那段距离,就同送他的人握了握手—一他通过他同自己为之冒险的伟大祖国告别——他刚从树丛后往外迈了一步,就在这一刹那,德国人又开枪射击了。
不,这不是向投敌者开的枪!他们这时还没有看到他,可是,普罗宁却被打中了一枪。
他摇晃了一下就向金银树的树枝靠去,其实那些树枝是根本支持不住什么的。
“您受伤了吗?”侦察科长惊惶地喊道——其实事情是十分明显的。
“好象是……”普罗宁说,“好象是在锁骨下面……”
“唔,既然如此,那就住院去吧。”侦察科长提议说:“这次行动只得取消了。”
“绝对不能!”普罗宁反驳说,“还应当去。
“那末伤口怎么办呢?”侦察科长问道。
“也许它会成为一份最好的介绍材料呢。”
他皱了一下眉头,推开了结着深红色金银果的树枝,往前一冲,就向敌方跑去。
我方自然是要向投敌者开枪了。普罗宁冒的险是很大的,因为不论是敌方或我方都可能有实弹击中他。
德国人立刻明白向他们那里跑去的是个什么人,于是就停止了射击。
以后的一切就部清楚了。普罗宁实现了自己的意图。他跑到德国人阵地的紧跟前倒下了。他流血过多,筋疲力尽,但是,由于到底跑到了“自己人”这里,因而感到十分幸福……
普罗宁满可以成为一个天才的演员,他在医院里的表现就使我确信了这一点。
在这一冬天里,我同普罗宁本人只见过一次,而且,如果不是爱丁格尔使我陷进了所谓无可奈何的境地,那么,就是这一次恐怕也见不到。
爱丁格尔变得越来越固执了,他常常要求我拿出实际的证据来说明我确实是在同德国人合作。他们对我的指望很大,因此待我也有些宽厚。但是归根到底我必须交出我的间谍网和我的通讯工具,只有交出这些东西才算我对叫做“德意志帝国”的商号做出了贡献。
果然不出所料,爱丁格尔把我逼得走投无路了。
“最亲爱的布莱克,您无视我们对您的宽厚。”有一次他请我去了,对我说,“但是,我们可不打算再等下去了。我们懂得,为了使您的间谍组织执行新的任务,应当做好准备工作,重要的间谍不能象皮球那样,从这个人的手传到那个人的手,但是我们现在就要把您同伦敦的联系放在我们的监督之下。我希望您把电台交给我们。在星期三,或者就在星期四吧,您要拿出这种证明您同我们合作的证据来,否则我只得把您转送到柏林……”
晚上,我把爱丁格尔的这项要求对热列兹诺夫讲了。
“长官先生这一次大概一定要纠缠你了。”维克多尔说,“我报告给上级,想个办法。”
第二天,维克多尔转告我,说普罗宁要同我见面,并且约定会面的地点在“斯普林吉特”电影院。
我在指定的那一天去看最后一场电影,每天这个时间观众很少,因为十点以后在城里通行需要特别的通行证:我买了一张票,是第二十排,座位在右面。座位在哪一排哪一面,都在事前通知我了。大厅里漆黑,最后一场已经开演了;过了二十多分有一个人坐到了我的身旁。
“晚安。”普罗宁悄声说道,他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唔,发生了什么事情?爱丁格尔跟您又要什么电台?”
我尽可能简要地把问爱丁格尔的谈话叙述了一遍。
“唔,是了。”普罗宁听我讲完以后,沉思默想地拖长声音说,“您那次外出的借口想的倒不错,但是,不难预料,德国人对电台一定会发生兴趣……”
根据普罗宁说话的口气来看,我觉得他一定是责难地摇着头——虽然在黑暗中我看不见他。
“不过,您不能退出这场戏,只得把这个小东西给他们。”普罗宁说道,“但应当同德国人把时间拖得尽可能更长些,以便等待,等待……”
“等待什么?”我抑制着上升的怒气,问道:“您不以为我这是白白消磨时间吗?我周围的一切都在沸腾,我觉得,热列兹诺夫过的是一种十分紧张的生活。可是,却让我处在这种蛰伏的状态。”
“请放心,这种蛰伏状态很快就要结束了。您问我们等待什么吗?您要知道,忍耐——一这是一个侦察人员的重要美德之一。只有在电影或小说里,侦察员才能不断地参与惊险事件,而实际上,他们有的时候要等待好几年,才能查明某种秘密。”
“但是,这样等呀等呀,很可能等不出任何结果来。”我反驳说。
“是的,也可能等不出结果来。”普罗宁立刻表示同意说,“但,这一点您就不必担心了。既然命令您等待,那么您的任务就是等待。您还要装作布莱克。应该尽可能把布莱克这个角色扮演好。您查明布莱克的底细,研究他住宅里的每一本书,每一张纸,地板的每一块木板。您要装作布莱克,并且要等待——这就是我能同您讲的一切。有朝一日,生活会把布莱克的秘密揭示给我们的。假如我们不在三百六十四天里等待这一天,那末,揭开这桩秘密就会是偶然的了。总要有一天,他的间谍组织就可能落到我们的手里!”
他又握了握我的手。
“请回吧—-还要沉着。您自己也明白,您是站在刀刃上。但是您应当保持平衡。我们绝不能放弃这场斗争。我们要想些办法。明天热列兹诺夫会把命令转达给您。夜安!”
他离开之后,就象我眼前银幕上那个侦探影片里闪过的镜头一样,消失在黑暗中了。
第二天,热列兹诺夫叫我告诉爱丁格尔,说长官先生一定能得到那部电台:但我需要拖一星期再同爱丁格尔见面。
我就按照热列兹诺夫说的做了。
“长官先生,您一定能得到您想要的东西。”我挂电话告诉他说,“但是我不能马上就离开里加。我请求把我们的外出拖一星期。”
“好的,贝尔金先生,就按您的意见办!”爱丁格尔用威吓的口吻回答说,“但是,您要记住,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您想再延期一天也不成了。”
我把爱丁格尔的回答转告给热列兹诺夫,他满意地透了一口气:“别担心,普罗宁不会使我们上当的!”
果然,在我同普罗宁会见以后过了四天,热列兹诺夫就来对我说:“一切都准备好了。电台可以交出去了。星期天我们自己先检查一下,下星期三您就可以把爱丁格尔带去。”
星期天,我们到海滨去了。
天气阴暗,暗蓝色的乌云在空中翻腾,从海上吹来一阵阵讨厌的冷风。
我们沿着那枯燥的、盖满了大雪的道路前进,经过了好多没有人住的别墅——别墅的主人已经被战争的风暴弄得各奔他乡了。
“仿佛又有人在我身后跟踪了。”我对热列兹诺夫推测说,“爱丁格尔眼看又沉不住气了。”
“您说的很对,其实他一直在注意着您。”热列兹诺夫表示同意说,“他怕您掩灭通往电台的足迹。”
“那末说,后面真有人监视我们?”我问道。
“当然罗。”热列兹诺夫证实说:“哼,就让他监视去吧。我们让德国人认为胜过英国间谍而感到满意吧。”
热列兹诺夫在一座最凄凉、最难看的别墅前面停住了车。
大路的远处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个瘦长的人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热列兹诺夫没有管他,打开了那扇没有上锁的小门。
“进去吧,要记住一切,记住每一件小东西,并且要尽可能地记得仔细!”热列兹诺夫警告我说,“应当使爱丁将尔一下子就感到这里的一切对您都不是生疏的。”
我们走到前廊,热列兹诺夫从口袋里取出钥匙,打开了通往户外的门,然后又打开了从前廊通往屋里的门。别墅的里面就显得不那么荒凉了:朴素的家具摆得很整齐,仿佛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只是不久以前才离开这里。
我们从厨房进了地窖。热列兹诺夫打开了电门,电灯亮了,他挪开靠墙放着的一个大桶,露出一个通往隔壁房间的小门。
我们钻进了那个房间,我看见在一个用厚木板钉的大箱子上有一台无线电发报机。
“天线呢?”我很感兴趣地问道。
“看见门口那只大公鸡了吗?”热列兹诺夫反问我,“那只公鸡的用金属棒制成的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