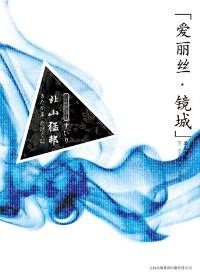新爱洛伊丝-第4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看到一出既有教育意义又使人感到愉快的表演。在伯尔尼,在苏黎世,在海牙,人们演
奥地利王室过去的暴政,演人民对祖国和自由的爱;我们觉得这种戏很有趣味。不过,
有人问我;在这里演高乃依①的悲剧有什么用?还问我:庞贝②或塞尔多里乌斯③与巴
黎的人民有什么相干?希腊的悲剧演的是著名的真人真事,观众看到的就是当时的情景,
而且有史事可稽。但是,纯洁的和英雄的火焰,对大人物的灵魂能起什么作用呢?有些
人不是说爱情和美德的斗争往往搞得他们夜里难以安眠吗?不是说爱情在国王的婚姻中
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吗?请你根据那么多以虚构的题材为内容的戏剧的真实性和所起的作
用,去判断他们的话对不对! ①高乃依(一六○六—一六八四),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
②庞贝(公元前一○六—四八),古罗马将军和政治家。
③塞尔多里乌斯(公元前一二三—七二),古罗马将军。
至于喜剧,它本来就是为人民而编的,因此,它应当如实给观众表演人民的风尚,
以便他们在看戏之后,能像人们对着镜子擦去脸上的迹印一样,改正他们的过错和缺点。
德朗士①和普鲁特②把他们写喜剧的目的搞错了,但在他们之前的阿里斯多芳③和麦兰
德尔④给雅典人演的却是雅典的风尚;后来只有莫里哀还能比较客观地描写上一个世纪
的法国人的民风民俗。画面变了,画家也就不再来了。现在,戏中的对话,都是从百十
来个巴黎人家中的对话抄来的。除此以外,戏中根本看不到法国人的风尚。这个大城市
有五六十万人,然而这五六十万人的生活,戏台上就压根儿没有演过。莫里哀既敢描写
有资产的市民和手工匠人,也敢描写侯爵;苏格拉底把马车夫、金银匠、鞋匠和泥瓦工
的生活也搬上了舞台。但今天的剧作家却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觉得自己如果描写商人
柜台上的交易和工人作坊里的劳动,那是很丢人的。今天的剧作家笔下的人物都是知名
人士;他们靠他们笔下的人物来表现他们本身所没有的才华。观众也变得很精明,他们
担心:去看喜剧,就等于是去拜访了剧中的人;那是会贬低自己身分的,因此,他们不
愿意去看戏中所演的那些比他们身分低的人。他们好像是世界上唯一的居民,他们根本
看不起其他人。有一辆四轮马车,一个看门人,一个厨师,这才像一个上流社会的人;
为了要像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就必须像很少数的那么几个人行事。出门步行,那不能算
是上流社会的人,那是小有产者,是普通人,是另一个社会等级的人。我们可以说:他
们之所以要有一辆四轮马车,其目的不是为了乘坐,而是为了生存。有那么一小撮狂妄
的人,自以为天下就是他们这些人的。其实,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坏事,他们是不值
得人正眼去瞧他们的。喜剧演的就是他们这些人;他们在戏中既被人表演,同时也表演
了他人,他们两边都沾边;戏台上演的是他们,坐在观众席上装模作样的人也是他们。
这样一来,观众和剧作家的距离就缩短了;这样一来,现代戏就离不开它那一套令人厌
烦的神气样子,靠漂亮的衣服来表现人。你也许会说:这是因为法国只有伯爵和骑士这
两种人,老百姓愈穷苦,我们愈应当把他们的生活表现得很美好。这样做,其结果是:
在表演那些对他人起模范作用的等级的人的可笑的事情时,不仅没有起到痛斥它们的作
用,反而把它们加以扩散;人们都成了猴子,总想模仿有钱的人:他们到戏院去,目的
不是拿戏中富人干的那些荒唐事开心,而是去研究富人的做法,学富人的样子,最后变
得比富人更荒唐。这种情况的造成,始作俪者就是莫里哀本人。他本想纠正宫廷的习气,
结果反而拿宫廷的习气去感染了市民;他笔下的可笑的侯爵,反倒成了那些将成为侯爵
的小有产者们学习的第一个榜样。 ①德朗士(公元前约一九○一—五九),拉丁喜剧作家。
②普鲁特(公元前二五四—一八四),拉丁喜剧作家。
③阿里斯多芳(公元前四五○一三八六),希腊喜剧作家。
④麦兰德尔(公元前三四二一二九二),希腊喜剧作家。
一般地说,在法国戏台上,台词多而动作少;的确,法国人说得多而做得少,或者,
至少是:法国人重言而不重行。有人看了《暴君德尼》这场戏之后出来说:“我什么也
没有看见,只听见许许多多人在台上说话。”你听,这就是人们看了法国戏之后的结论。
拉辛①和高乃依尽管有天才,但他们本人也只不过是能说善道的人罢了。那位继承他们
衣钵的人②,还是头一个敢模仿英国人那样在戏台上偶尔表演一下剧中人的心情。他们
的戏,通常都是用漂亮的对话来进行,对话的句法很严谨,用辞也极其华丽。人们一眼
就可看出,每一个对话者首先关心的是如何引起观众的注目。几乎所有的台词都用的是
很空泛的警句。不管他们是多么激动,但他们心中想到的是要观众叫好,而不是如何表
现自己的内心;他们重台词的道白,而不重感情的表演:除了拉辛和莫里哀的戏③以外,
在法国戏剧中,如同波罗亚修道院的文章一样,一律不用“我”这个字,因此,凡是在
谈到人的情欲时,尽管你基督徒的谦卑那样克制,也通通用“人们”来代替“我”字。
此外,在表情和道白中还有某种矫揉造作的成份,使感情不能通过语言确切地表现出来,
使作者的思想不能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得到体现,并在台上加以表演,结果,使作者必然
要受舞台效果和观众的反应所制约。因此,在最生动的场面上也要精心安排演员说几句
高雅的话和做几个漂亮的姿态。如果表演一个人因绝望而自杀的话,尽管他已在自己的
胸口上捅了一刀,他也不会像波丽克丝娜④那样直挺挺地倒下去,他死了也不倒,他死
了之后也要昂然挺立;所有那些表演人死的演员,明明刚才已经断了气,却又猛地一下
站了起来。 ①拉辛(一六三九—一六九九),法国诗人和剧作家。
②指伏尔泰,卢梭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往往和伏尔泰的看法相左,两人成见甚深,
笔战不已。在这一句中的“模仿英国人那样”七字,在卢梭赠卢森堡元帅的《新爱洛伊
丝》手抄本中是没有的,很显然,卢梭的这句话,意在讽刺伏尔泰虽在诗剧的创作上有
所改进,但不是他个人的独创,而是学英国人的样子。
③在这一点上,不能把莫里哀和拉辛相提并论,因为前者和其他的剧作家一样,爱
用箴言和警句,尤其是在他的诗句中更是这样。但在拉辛的剧作中,通篇都注重表现人
的感情;他善于让每一个角色说自己的话;在这方面,他在法国的剧作家中的确是独一
无二的。
④波丽克丝娜,传说中的特洛伊国王普里亚蒙斯和王后艾卡柏的女儿。特洛伊被攻
破后,阿基里斯的儿子要把波丽克丝娜作为牺牲,杀死在阿基里斯的坟前。她的父亲告
诫她“死要死得威严!”事见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德斯的悲剧《文卡柏》。
这些情况的产生,是由于法国人不喜欢在戏台上表现自然和幻想;他们偏重于精神
和思想的表现,他们重视乐趣而不重视模仿真实的生活;只要看得痛快,就是因此而受
到引诱,他们也不在乎。他们到戏院去,不是为了去看戏,而是为了去看人,为了让别
人看他们,为了收集戏散之后可供闲聊的话题,因此,他们之所以对他们所看到的东西
动脑筋思考,那纯粹是为了先揣摩一下别人将说些什么。在他们看来,演员就是演员,
而不真正是他们所表演的人。那位以世界的主宰的口气说话的人,是巴隆,而不是真正
的奥古斯都①;庞贝的遗孀是阿特里茵扮演的,阿尔齐尔②是高苏小姐扮演的,那个高
傲的野蛮人是格兰瓦尔③扮演的。在喜剧演员方面,他们也根本不知道幻想是怎么一回
事;他们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动脑筋想过幻想的来由。他们把古代的英雄放在六
排年轻的巴黎人中间;他们仿照罗马人的服装剪裁法国人的衣服。观众发现哭得很伤心
的高尔勒丽④脸上还搽了一层薄薄的胭脂,卡托的脸上扑了白粉,布鲁土斯身穿一条用
裙环撑开的裙子。所有这些,谁也不觉得不好,对戏剧的成功也无影响。观众表面上看
的是剧中人,而实际看到的却是演员;同样,人们看的是剧本,实际上看的是剧作家。
既然衣服问题并不严重,则其他一切也都可以原谅了,因为人们都知道:高乃依不是裁
缝师傅,克雷比翁⑤也不是假发师。 ①奥古斯都(公元前六三—一四),古罗马帝国皇帝。
②阿尔齐尔,伏尔泰的悲剧《阿尔齐尔》中的女主人翁。
③阿隆、阿特里茵、高苏和格兰瓦尔,四人都是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一七三一年
卢梭第一次到巴黎时,曾看过他们演出的戏。
④高尔勒丽(公元前一八九—一一0),罗马将军塞皮翁之女,从很年轻的时候起
就孀居,以美而贤,教子有方著称。
⑤克雷比翁(一六七四—一七六二),法国剧作家。
所以,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一切全是胡言乱语、晦涩难懂的词儿和无关紧要的
废话。在戏台上也如同在社会上一样,听台上的人说的话,也是自听,学不到什么东西,
再说,学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只听一个人讲话,你就能知道他的品行吗?他什么事都
没有干过吗?他就没有被人家议论过吗?其实,此间的所谓好人,并不是指行为端正的
人,而是指说话漂亮的人;一个人只要不加思索地脱口说出一句不得体的话,就足以给
他造成今后做四十年好事也弥补不了的过失。总而言之,尽管他们做的事不符合他们说
的话,但我发现,他们观察一个人,也只是听其言而不观其行的。我还发现,在一个大
城市里,上流社会的人似乎比行为不故意矫揉造作的人显得更平易近人,甚至更牢靠;
然而,他们是不是真的就更通情达理和行事更公正呢?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所看到的
这一切,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在那些极其光明和文雅的外表下面,他们的心比我们的心
更深,更阴险。我,一个外国人,与任何事情没有牵连,与任何人也没有关系,对他们
的那些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过,我现在也觉察到:这纷纷扰扰的生活也使我像那些过这种生活的人一样地感
到陶醉;我深深地陷入了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我眼花缭乱地仿佛看到有许许多多东西
从我眼前飞快地过去。虽说在使我吃惊的事物中,没有一样曾打动过我的心,但它们加
在一起,就使我的心混乱了,不知道爱什么好了,甚至有时候竟忘记我是什么人,我为
谁而活着。我每天在走出住处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感情深深地藏在我心里,同时表现出
一副能适应一切我将遇到的无聊事的样子。我听别人怎么分析和判断事物,我不知不觉
地也学着他们那样分析和判断事物。虽然我有时候试图摆脱他们的那些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