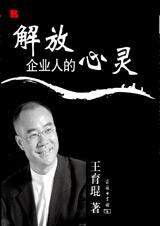走过心灵那一端-第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刘德望扫好了土,翠妮使用铁锹铲上倒入筐中。每装满一担,他便挑着倒入冬天里沤粪的大堆上。
翠妮虽然个子跟刘德望差不多,但她由于常常生病,身上皮包骨头不见肉,不过她还是咬着牙去为清洗罪名而拼力干活儿,她认为只要她自己受的苦越大,罪责就会越小。
刘德望没有怪怨任何人。他活了四十个春秋从来不会说一句责怪人的话,既不同于沉默寡言但心里做事的兄长刘德贵,也不同于愤愤不平、牢骚怪话联编的弟弟刘德喜,刘德望听老人们讲:“共产党是真命天子领导的人。毛泽东是上天的星宿下凡。”刘德望不怎么信神信鬼,但他相信“老人嘴里无虚话”,他坚信“雪化了要见山,水落了要石出”,刘德望的清白一定要挣回来,清白就是清白不会跑掉。坚强的信念真正属于一个人的时候,坚强的意志与人就结合了,刘德望就是意志。
有意志就什么也不怕了。
尽管生活有时像一块死沉沉的铁压在身上,把人性与脾气都压成了一条缝,人就生活在一条缝中了,但意志是不容易被压死的,一个人的意志是难以消灭的,再渺小的人他的意志是不可蔑视的。老天爷给了每个人最公平的东西就是意志——生命的意志,守住意志的人与天地同在,与万物世界共存。
“远小哥,你起的真早,忙吧?”
()
听到街门声响。刘德望停住扫帚,但扔保持扫姿,小心地问候。
按说,刘德望是刘瑞芬的远房兄长,刘德望却不能称张鸿远为妹夫,而只能依着张鸿远岁数比他大六岁而称“远小哥”。
张鸿远被刘德望谦卑而低缓的问候声打动了,同情之心油然而起,他说:“刘德望,以后我家门前这段路你就不要扫了,等瑞妮起来扫吧。我家门前的道应该我家扫。”
“不,不,不不不!远小哥,可不能这样,应该我来扫,该我扫。没什么,我能扫得了。”刘德望不知说什么才好,他的表情和心情太复杂了,决不是语言能表达清楚,但他的话里充满了亿万分的感激之情。
天已明了,刘德望不敢与张鸿远多说话,只好压住心中的话儿,加快扫街节奏。
张鸿远望着刘德望矮胖的水桶般晃荡着的身影沉思了好久,叹了一口气。
是谁发明了扫垃圾这个构想?让五类分子——这些社会的“渣滓们”清扫街道上的垃圾,已“渣滓”清扫垃圾,这是多么文雅的处罚,然而文明的处罚往往更残酷、更阴毒。是谁首先懂得:对灵魂摧残要比对肉体的摧残更具彻底性?!
以“渣滓”扫垃圾,以垃圾取“渣滓”,这是多么巧妙的构思?!
然而,张鸿远幸好没有沦为这些扫垃圾的“渣滓”,这是值得宽慰的事情。当他和这些渣滓们童年时节光着屁股在河里耍水时,谁会想到日后成为两个对立阶级的人呢?
从刘德望的身上,张鸿远找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宽慰和平衡:不知是由于刘德望更大的不幸相形之下使张鸿远的不幸显得无足轻重了,也不知是刘德望身处逆境中那种虔诚坚韧的精神感召了张鸿远,遮盖在张鸿远身上的沉郁的不幸渐渐缓解了。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张鸿远笑了。
麦收之后,建忠媳妇林巧珍也参加劳动了,但出勤极不正常,经常隔三差五请假休息,渐渐小两口不时小打小闹发生一点争吵,张鸿远一来二去也有耳闻目睹,但装个糊涂,也不放在心上。
霜降之后,队里该分的粮食都分配完毕了,看看临近农闲时节了。
一天上午,有一个黑瘦黑瘦、腰背有些驼的小老头,像幽灵一般溜进了张鸿远的院子,小老头,五十二三年纪,看上去足有六十好几,进了院里,飞快地瞅了瞅南窑和正窑,那目光非常狡猾,之后溜进了建忠屋里。
“妈,妈,座山雕来啦。”
这时爬在窗户上玩耍的建刚正好看到了来人,忙向刘瑞芬报告。
“什么座山雕?谁?”
刘瑞芬正躺在炕上休息,近一段时期她身体欠佳,老是没精打采,听得儿子的话,便坐了起来。
“他,东沟我嫂嫂的爹。”建刚压低声音说,“是那个‘搅茅棒’。”
刘瑞芬明白了,是说建忠的岳丈林大金。
“别胡说!没告诉你们别叫人家外号?”
刘瑞芬吓唬了孩子几句,静耳听时,听到了林大金——那个‘搅茅棒’沙哑的说话声和不时发出的干咳声。
“叫你爹去吧!”刘瑞芬赶紧让建刚叫张鸿远。这个‘搅茅棒’很少上门。肯定是有事儿。刘瑞芬打心眼不想见这位亲家,她有点怵怔。
林大金随说算不上盖世闻名,但绝对是盖村闻名,在一千多口人的东沟村,林大金能成为男女老少皆怕的人物,也算得上是个非同寻常的材料。
世上有两种人能成为人物,出奇的好人和特别的坏人。而好人成为人物,说明坏人太普遍了;坏人成为人物,说明好人太多了;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的社会绝对是最好的社会,信不信?
林大金荣幸地生长在一个好人居多的时候,于是因为特别恶劣的脾性成为当时盖村闻名的“人物”。他成为“人物”主要是得益于特别的性格:一方面也是个头脑简单的人,而另一方面他又极爱逞能,总认为自己是个大能人,别人办不到的事儿他却能办到,这种矛盾的性格,加上他几次让人哭笑不得的表现,使他名声大振,赢得了‘搅茅棒’的非凡称号。
林大金年轻时就是一付瘦小驼背的丑相,一张上粗圆、下尖窄的锛炭镢脸;一双杏仁眼中黑眼仁小,白眼仁多,看其眼,便知其人心术不正。有一天,跟林大金一起在煤矿干活的伙计们故意说:“谁能去煤场上问买炭的人要二块钱?咱们下了班喝一壶去。”几个伙计故意推说:“咱不行,没本事儿。咱们几个人里恐怕没有个能耐人。”林大金一听,二话不说,站起身来到煤场上。煤场上到处是买炭的人和驮炭的牲口,林大金走到一头黑铁青骡子后边,突然大叫一声爬在地上:“哎呀,踢死人了,操你八辈祖宗,哪个狗日的做下这牲口,踢死老子了。”林大金一阵急似一阵的哭骂,惊动了骡子的主人。骡子的主人一看自己的牲口踢着人了,忙问:“后生,踢着哪啦,厉害不?”林大金也不管数九寒天,解开裤带裸出又黑又脏的臀部让人看。骡子的主人捂着鼻子看了好一会儿,不知是眼睛不好,还是林大金的皮肤太脏太黑,看不出伤在什么地方“后生,到底哪疼?”骡子的主人急着问。“不知道,反正到处疼。哎呀,疼死大爷了——”林大金拼命地号。这时,骡子的主人明白了,认倒霉吧,遇上不要脸又不说理的混球了,于是拿出五毛钱给林大金。林大金看也不看眼前的五毛,还是号,骡子的主人又拿出三毛,接着是二毛,总数一直加到两元,林大金的号哭戛然而止,伸手拿住两块钱,裤子也顾不上提好,裸着一半臭屁股,屁颠屁颠地跑走了。
后来林大金竟然娶上了媳妇,那是个又黑又丑三大五粗的女人,村里人称“松树皮”很能干活,胆大有劲儿。两口挺对眉眼,感情也不错,一切都不错。一天,几个人闲扯淡,这个说:“世界上人人怕老婆。”那个说:“就是老婆不怕我。”林大金听了之后,回到家平白无故将“松树皮”揍了一顿。从此每天一顿揍,幸好“松树皮”体格粗壮能经得住几次操练。揍得日子长了,终于抗不住了,于是“松树皮”丑脸一拉,大嘴一扯,哭问道:“你怎么老打我?”林大金吊着个杏仁眼睛说:“你怎不怕我?”松树皮说:“怕!”从那天起林大金再也没有揍“松树皮”。
村里人知道林大金是个混球儿,一般人凡事让他三分,林大金便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一天,村里发救济金,于是也跑到队部要救济款。革委主任说:“林大金,你不够救济标准,不能跟三歪比,三歪家的孩子们连过年的棉衣都没有,数九天还穿着褂褂拾煤渣。”林大金一听,二话没说,回到家脱了棉衣棉裤,换了身夏天穿的破褂子,来到了队部。革委主任一看势头不对,便说:“你等几天,我们几个村委开个会吧,大伙同意了就给你发。”林大金二话没说,坐在队部的凳子上等开会,从上午等到天黑。林大金的老婆“松树皮”叫吃饭,但林大金不吃,可也受不了冻,便叫老婆拿来一斤白酒喝着等开会。晚上八点半,会开完了,经研究救济林大金两块,林大金一听把喝了一半的酒瓶摔在了地上。
“呱——”一声响,林大金便一头往革委主任身上撞。别人上来拉他,他就又抓自己的脸又打自己的鼻子,脸也抓破了,鼻子也流血了,于是林大金疯也似的又打又骂,又咬又撕,仿佛是一条疯狗。村里的人全轰动了。
治保主任带着两个基干民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来镇林大金,林大金不但不怕,反而往刺刀尖上撞,仿佛要跟刺刀叫板儿,刺刀只好退了下去。
这时惹恼了革委主任的远方弟弟,车把式林玉虎。林玉虎三十五岁,个子不高,但粗壮豪迈,一杆比他个子还长一倍的大鞭捏在他手里“叭、叭、叭”三声脆响,三鞭子驯服过村中有名的儿骡“黑紫红”,于是人称“三鞭杆”。
三鞭杆,见林大金借酒煞疯,便怒气冲天,从家里拿来长鞭,手捏鞭杆“叭——”一声清历刺耳的炸响便惊摄了在场的人群。当年,也是这一声炸响使狂奔的儿骡“黑紫红”浑身一栗。此时的林大金耳边仿佛一声巨雷,便惊呆了。
“闪开了——”三鞭杆一声呐喊,接着是“叭”一声脆响。当年,这第二声脆响,抽在了儿骡“黑紫红”的耳根上,“黑紫红”霎时呆立不动。此时,第二鞭抽在林大金手中的算盘上,那个算盘刹时破碎。
“X你妈的——”三鞭杆大骂一声,接着“叭”又是一声。当年这第三鞭抽在了儿骡“黑紫红”的大腿软肋下,“黑紫红”被抽的屁滚尿流。此时,第三鞭直抽到林大金的大腿上——那只是鞭尖点了一下,林大金大腿上产生了一股剜肉抽筋般惨痛便跌在了地下。
三鞭杆一脚踩在林大金胸膛问道:“敢不敢了?”林大金虽然站不起来,但嘴还硬:“我X你公母祖宗!”三鞭杆一看,这家伙比牲口还难制服,便从家里拿来一瓶煤油,捏住林大金的鼻子一气往嘴里灌,林大金被灌得哭笑不得,叫喊不得,气恼不得,求饶不得,脸憋得黑青,泪如泉涌,一瓶煤油灌罢,四肢连挪摆得劲儿都没了。这时,有人说:“三鞭杆,算了吧,看出了事儿。”林大金一听,便装死。
三鞭杆看林大金用装死来吓唬他,好!三鞭杆拿条长绳,将林大金双脚捆个猪蹄疙瘩,“噌”一声,将林大金头朝下吊在了大队部旁边仓库的房梁上,整整吊了一夜。次日清晨,人们来到仓库,从梁上放下林大金。林大金在地上躺了半个时辰。人们见他一动不动,便说:“坏了,弄死人了,三鞭杆也不在了,怎办?”这时地上的林大金突然爬起来大骂:“三鞭杆; X你万十倍公母祖宗,我——”突然林大金眼发直,嘴也合不上,也骂不出口,原来三鞭杆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