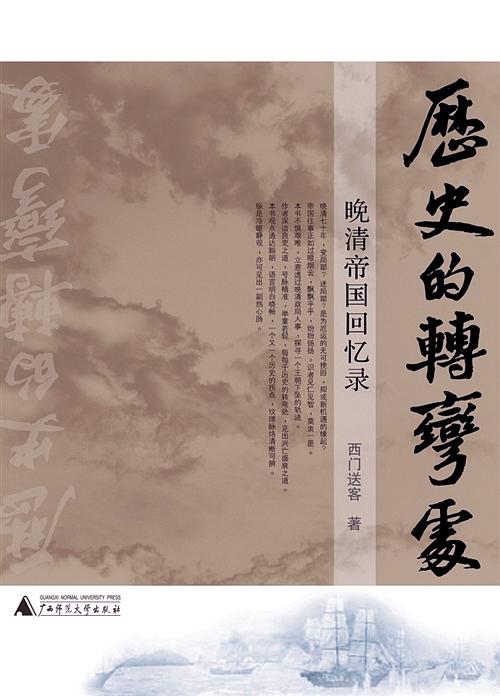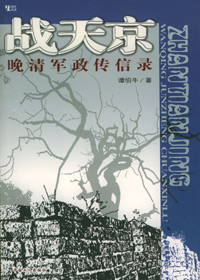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1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剔除两个欠通之英文字,及将当初手民误植「叔夷钟」及「素命镈」之铭文加以改正之外,余率任其旧,虽因事忙,无暇改作,亦见三十年来,流落异邦,学无寸进之可悲也。
一九七〇年农历除夕附志于纽约哥大
*载自台北《史学汇刊》第三期
原载于一九四四年安徽立煌之安徽学院院刊《世界月刊》创刊号
六、论帝国与民国之蜕变
我们治「当代民国史」的史学工作者,落笔的先决条件应该是对「传统帝国史」(尤其是晚清这一段)有个本质上的了解。因为「民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帝国」慢慢地转变过来的。帝国是父,民国是子。不知其父,焉知其子呢?
再者,帝国和民国的关系还不是生理学上鸡和蛋的突变关系;不是一只帝制的鸡,忽然生下一个民治的蛋来。它二者的关系,却是蚕之与蛾的关系在本质上,在制度上是一种抽丝剥茧的蜕变关系。两朝嬗递、藕断丝连,是不可以一刀两断的。
就以九〇年代大陆和台湾的现状来说吧:时至今日,大陆上的政治制度,可以说还是蛹在茧中、去古未远。毛泽东说:「千载犹行秦法政。」大陆上的问题,正是这个「秦制度」无法摆脱的问题。这也是一种苏联式的「革命后」(post…revolution)方向失落而回归专制的问题。
台湾的现状呢?它这只民主白蛾是破茧起飞了。可是飞蛾都有其扑火的本性。误把烈焰当光明,万一飞翔失控,扑火自焚,也就前功尽弃了。所以宝岛今日的情况,从历史中找前例,似颇近乎德意志第三共和时期。德国当年由于仇恨加暴力曾引发过一种「排犹运动」(anti…Semitism)。国人把复兴工作中所遭遇的困难和国内外的不平现象,都迁怒到一个少数民族头上;造成一种山雨欲来的「革命前」(pre…revolution)有「恐怖主义」(terrorism)倾向的群众情绪。这种情绪最容易升级。如不能适时加以抑制,以防患于未然,其前景也是未可乐观的。
长话短说。我们海峡两岸在民主政治上的努力,都还是在德苏两个模式中寻出路。双方距「民国」的真正目标,都还有其不同的距离呢!但是怎样的一种政治社会体制,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民国」呢,请先了解一下「民国」的本质。
「民国」政体的本质
丢开繁琐的西方政治哲学不谈,且看看我们自己的现代思想家如何说法。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上说他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他的目的是「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篇〈总理遗嘱〉原是那位颇有文采的汪精卫执笔的。汪氏为迁就他那「必须、务须、尤须」的行文腔调,代孙先生撰遗嘱,就不免以辞害意了。中山革命之目的,不只是在追求中国在国际间的自由平等;他还要全中国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上,彼此之间也自由平等呢。
当然从经济生活方面来说,孙先生所要求的并不是孔夫子「不患寡」,或红卫兵「反封资修」的「穷平等」。他一直强调中国人民的经济状况只是「大贫、小贫」。在大小贫之间求平等,是没有太大地意义的。孙氏所要求的是「富平等」用目前的辞汇来诠释,那就叫做「均富」吧!要既富矣而后均之,则我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包括附属于农业经济体系之内的手工业和小城镇)就不能胜任了。简言之,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民国」,则工业化的经济发展就是个必要条件了。
再者,搞工业化的经济起飞,是全国人民都要动脑动手的,少数人如滥用权力,从事包办,这个经济是永远「起飞」不了的。这样就牵涉到政治体制上的民主开放了。且放下「现代」人类社会行为中所应享有的「人权」不谈,纵使只从经济建设这一项更迫切的实际专题来观察,则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开放也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翻看当今「已开发国家」的进化史:未有政治封闭而经济可以「起飞」者;亦未有经济已经起飞,而政治仍继续其封闭者。这一对难兄难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也。所以一个真正的「民国」所应具备的第二个必要条件,便是一个真正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所代议的全民政治:林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是也。在政府运作上有任何蒙混,就不是真正的「民国」了。
有了个「民有、民治」的真民国,则民之所「享」的经济财富、教育水平、基本人权、四大自由是会与之俱来的。孙中山先生革命终生,他那个「尚未成功」的最后目标便是建立一个如上所述的真民国。
可是一个国家纵使能完成上述的两大条件如战前的日本和德国,究竟怎样才能把它维持下去,而不致走火入魔,也是个天大的难题。古人云「创业不易、守成尤难!」正是这个意思。试看日本「明治维新」诸贤苦心孤诣所建立的代议虚君制,是多么令人神往。殊不知前辈可以「创」之,而后辈却不能「守」之。等到少数暴戾无知的「少壮军人」,藉爱国之名,以暴力干政;振臂一呼,全国景从。勇则勇矣,其后果便要吃原子弹了。再看德国:一次大战后,它忍辱负重、重建共和,多么可泣可歌!不幸少数领袖,私心自用,利用群众报复心理,化仇恨为政治力量,德意志民族就重罹洁劫了。
日德这两个民族,在近代世界上都是最有效率、最有表现的优秀民族。但是为什么犯了如此愚昧的错误呢?我们读史者叹息深思之余,才悟解出,原来他们的犯罪之源是出自他们政党之内,狭隘的组织家压制了有远见的政治家;在他们近代文明中,偏激的理论家也挤掉了恢宏的思想家。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样就使我们在中山之后,又想起了胡适之先生孙、胡二人的思想是萧规曹随的。
适之先生早年就反对极权。认为民主政治不能走捷径。要想以法西斯、褐衫党一类的「速效」来建国救民是缘木求鱼的。胡适晚年鼓吹「容忍重于自由」。主张凡事都得想想,是人不容我?还是我不容人呢?只是单方面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那就是曹操了,还有什么民主呢?所以胡先生一生倡导民主的精义所在,便是一句话:「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二次大战前的德、义、日三国,在工业经济、代议政府两方面都已具备了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不幸的是他们万事俱备,只欠「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一阵东风。东风不来,他们就玩火自焚了。只知他人不民主,而昧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压根儿就不民主,从而滥用自由、滥用「多数制」(majorty rule),那就误尽苍生了。
话说至此,我们「民国」的本质也就显露出来了。本质为何?曰:「工业经济」也。非振兴实业无以富。曰:「代议政府」也。非有真正民选代议政府不足以言全民政治。曰:「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如生活方式不民主而多「财」(money)多「力」(might),则充其量一个小小「轴心国」翻版而已,民主云乎哉?
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我全国同胞、仁人志士,殚精竭虑所追求的便是这三个目标。但是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我们在大陆上可说是一个目标也未追到,甚至愈追愈远。台湾呢?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这一篑之土是否可以平安地加上去,而不致因一根茅草便压死一只骆驼。我们写历史的人,执简在手,每晚都打开电视,只有耐性地等着瞧吧!
「后封建」时代的中西之别
朋友们或许要问:民国之远景既若是之单纯,何以我民族苦学猛追了百余年,死人亿万,至今仍是前途未卜呢?这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千头万绪的。同时这一问题亦非中国所独有。大国如印度,小国如菲律宾和印尼乃至今日的整个「第三世界国家」,不都有类似的困扰?不也各有其不同的原因?但是困扰中国最大的原因,显然还是个中西「文化冲突」(cultural conflict)的问题。
须知我们的大清「帝国」是两千多年来,一脉相承,纯中国文化的产品;而「民国」则是个彻头彻尾西欧文明的延续。以古老中国的传统,一下要接上现代西方的制度,若只说是「凿枘不投」,我们还是小看了这个问题。事实却是它二者是「两极分化」、「背道而驰」,甚至是「水火不容」呢!因此要以中式「帝国」之蛹,蜕变出一个西式「民国」之蛾,其过程是痛苦不堪的。但是处此「后封建时代」(post…feudal period),在西方急剧发展的影响之下,我们又必须洗心革面,非变不可,这就是我们近代史上的难解之结了。
可是中西之别,究在何处呢?这问题,答来话长。这儿且说点简化的大略。
从比较史学着眼,可以说近两千年来世界文明之发展,大致可用东亚、西欧两大主流之演变以概其余。这两大主流本是各自发展,极少相互干扰的。两相比较,其成就盖亦在伯仲之间。可是在十七、八世纪之后,西欧文明就显然逐步领先了。当东亚文明还停滞在帝王专制、农业经济时代,西欧各国在政治上已扬弃了专制;在经济上也摆脱了以农为本而逐渐地发展出「重商主义」和「工业革命」了。
西欧文明何以在近代突然脱缰而驰呢?其关键盖为「封建社会」崩溃之结果。笔者在诸多篇拙作里,曾一再阐述中西社会发展之过程有其「通性」,如双方封建社会之发生与成长,便是通性之一例。然中西社会之发展过程,亦有其「特性」,如西方封建社会之形成,实发生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而中国封建社会之成长,则发生于秦汉大帝国建立之前。由于中西历史主观与客观条件之不同,而有其社会发展程序之先后;程序不同乃又导致这两个社会在近古与现代,亦有其本质之差异。
二者本质之差异又何在乎?曰:现代西欧北美社会发展之基础在「社会重于国家」也。「国家」(state)者,社会之「上层建筑」(super structure)也。国家之结构随社会之变动而变动。
我国则反是,我国社会发展之基础,则「国家强于社会」也。社会为国家之「上层建筑」,其结构之型态,其荣枯之动力,悉听命于国家之颐指气使也。
中西两社会之背道而驰,又何胡为乎而然呢?曰:双方发展中之主观与客观诸条件,均有以导致之。
西方中产阶级之自然形成
盖西欧于十五、六世纪封建社会崩溃之后,由于种种条件之限制(包括永远无法统一的拼音文字),他们因此也出不了一个秦始皇。其结果便形成一种小王国、小城邦纷立的局面。其小焉者大致如今日之港、澳与新加坡甚或更小。其大者亦不过如南韩、台湾或稍大,其最大者亦不过一四川耳。吾人如闭目试作遐想:当年西欧一隅之地,便有十数(甚或数十)新加坡、港、澳、台、韩,在商业上作激烈之竞争。它们的独立或半独立的政府,也被拖着勉力跟进(如近二十年之台湾与南韩);大家一致向钱看,一个「重商主义」,当然就不呼自出了。
社会繁荣带动了教育与科技之发展,加强了「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亚当史密斯之《国富论》,也就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