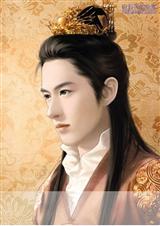幸福之路-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乐,再乘以两者的间隔时间所得到的就是远虑。个人的远虑与集体的远虑有差别。在一个贵族或富豪统治的国家,有人遭受目前的痛苦,而有人享受着未来的欢乐,这使得集体远虑更为容易些。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主义所有典型的工作都表明了高度的集体远虑:那些建造铁路、码头、轮船的人们所做之事的益处只在数年之后才得以回报。
确实,现代社会中没有一个人能比古埃及人在尸体防腐中所显现的有更多的远虑,他们这样做是希冀若干万年后死者的复活。这使我们想到文明的另一个基本要素,即知识。建立在迷信基础上的远虑不能说是完美的文明,尽管它也许可为真正文明的成长带来必需的。动灵习性。比如,清教徒将欢乐延伸至来生的习惯,无疑地促进了工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资本积累。由此,我们可以把文明定义为:申帕帕申军方冬的丁破车活方式。
如果我们回溯西方文明的起源,可以发现,它从埃及和巴比伦得来的东西,在主体上已成为所有文明的共同特征,而不是西方独有的。西方别具一格的特性始于希腊人,他们创立了演绎推理方法和几何科学。他们的其他成就,或者不太明显,或者在中世纪销声匿迹。在文学艺术领域,或许他们曾经辉煌一时,但与其他古老的国家相比,并没有什么调异之处。在实验科学中,他们产生了几个人,特别是阿基米德,他率先运用了现代方法,但这些人没能成功地建立一个学派或一种传统。希腊人对文明所作出的一个杰出贡献就是演绎推理和纳数学。
可是,希腊人是政治上的无能者,要没有罗马人的行政能力,他们对文明的贡献早已付之东流。罗马人发现发如何借助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来管理罗马帝国政府的运转。在以往帝国中,任何事情都依赖于君主的威力,但在罗马帝国可能为执政官所害,可能被拍卖转移,政府机构对此没有更多干涉——其反响之小,事实上,就如现在大选中表现的那样。看来罗马人开创了献身于非个人化国家的美德,意在抑制对统治者个人的效忠。希腊人确实高谈爱国主义,但他们的政府官员腐败逐项,几乎所有人在当政的某一时期都接受了波斯的贿赂。奉献于国家的罗马人观念已在西方成为产生一个稳定政府的基本要素。
在现代社会以前,完整的西方文明还有一个必要的因素,那就是政府同后来成为基督教的宗教间的独特关系。基督教的起源完全是非政治化的,因为罗马帝国的成长只是作为那些失却民族的和个人的自由的人们的一种尉藉,并且它继承了犹太教世界上的统治者的道德谴责态度。在君士坦丁之前的岁月里,基督教发展为一种组织,使教徒对之的虔诚远甚于对国家的忠心。罗马衰亡后,教会以一种独有的综合方式保留了那些在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文明中证明是最为重要的东西。从犹太教的道德激情中萌发了基督教的伦理戒律;从希腊人对演绎推理的热爱中孕育出了神学;从罗马帝国主义和法理学的典范中诞生了教会的中央集权政府和教会法。
不过,通过这样那样的途径而达到的政治上的凝聚成了西方文明区别于其他地区文明的明显标志。这主要归因于爱国主义,尽管它植根于犹太人的排外主义和罗马的效忠帝国思想,它在现代得到了发展,始于英国抵抗西班牙舰队,并在莎士比亚那里找到了最初的文学表述。自从宗教纷争结束之后,主要根据基于爱国主义的政治凝聚一直在西方稳步增强,并且目前仍在迅速地发展。从这方面看,日本已证明是最聪慧的学生。旧日本王室愚蠢而凶恶的封建贵族,无异于玫瑰战争时期肆虐英国的贵族老爷们。但是借助运载基督教传教士的船只被运到日本的火器和火药,幕府奠定了国内的和平;并从1868年起,通过教育和神道的手段,日本政府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与西方国家一样不屈不挠、团结一致的国家。
现代世界中社会的凝聚力,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战争艺术的变更,自从火药发明以来,所有这些变化已倾向增强政府的权势。这一过程可能绵延不止,但一种新的因素使其复杂化了:由于武装力量越来越依赖于产业工人,政府也就越有必要去寻求广大民众的支持。这是属于宣传手法的问题,可以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政府能在这一方面取得迅速的进展。
欧洲过去四百年的历史是一部兴盛与衰亡的历史:以天主教教会为代表的旧综合方法的消亡和尚大成熟丰满、但建立在爱国主义和科学之上的新综合方法的兴盛。不能认为科学的文明移植于没有我们先辈的地区能够具备我们这样的特性。科学移植于基督教和民生产生的效果,与移植于崇拜祖先和至高无上的君主政体产生的效果完全不同。我们敬畏基督教尊重每个人,而这是一种科学对立完全中立的感情。科学本身并不向我们提供任何道德观念,而且也很难确定哪些观念会取代我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传统膻变缓慢,我们的道德观念主要还停留于前工业社会的水平;但是,不能期望这一情况会延续下去。人们将逐步萌发与自然习惯融汇一致的思想,他们的理想也不会同他们的工业技术难以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速度已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在最近150年中世界所发生的变化远甚于先前4000年走过的路程。倘如彼得大帝有可能和汉漠拉比交谈一番,他们肯定相互心领神会;但是,他们都已无法理解一个现代金融巨头或工业巨头。这是一个怪异的事实,现代社会中种种新思想几乎都源自科学技术领域。只是在晚近,科学通过打破迷信的伦理信仰的任格,才开始促进新的道德观念的成长c凡是传统模式迫使人们受苦的地方(如禁止堕胎),一个比较善良的伦理观念就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结果是,那些允许知识影响他们伦理观的人们就被无知的信奉者视为邢端。然而,像我们这样依赖科学的文明,能否在将来成功地禁止假大地增加人类幸福的各种知识形式,正是值得怀疑的。
事实是,我们的传统观念既像个人神圣的观念那样纯粹是个体性的,又适应比现代世界中那些重要的社团小得多的群体。现代技术对社会生活最突出的影响之一,是在一个更大的程度上把许多人的活动组织到大群体中。这样,一个人的活动就时常与他所属的那个群体合作或冲突,而对与他关系十分疏远的那些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家庭这样的小群体,其重要性正日渐消失,只有一个大群体,即民族或国家,才能给予传统道德观的考虑。其结果,我们时代有影响力的宗教只要不是纯粹传统的,就会含有爱国主义的成分。百姓们甘愿为爱国主义贡献自己的生命,并且感到这种道德约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而对他们来说,反叛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看来,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自由主义整个时期中颇有代表性的个人自由运动,由工业主义导致的高度组织化而中断,这不是不可能的。社会对个体施加的压力可能以一种新的样式变得异常强大,就如在野蛮社团中。而各民族可能更以集体成就为荣,而轻视个人的业绩。这在美国已成为现实:人们为摩天大楼、火车站、大桥感到8豪,却把诗人、艺术家和科学家放在一边。苏联政府同样如此看待问题。尽管两个国家仍存在着对于个人英雄的欲望:在苏联,个人显赫当属列宁;在美国,应归运动员、拳击手和电影明星。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英雄们或是死者或是小人之辈,目前各种英明的事情,自然不与杰出个人的名字联在一起。
集体努力是否能比个人努力创造富有价值的事物,而这种文明是否具有最高的质量,思索这些问题是很有趣的。我想这些问题一时是很难有答案的。在艺术和学术领域,集体合作可能比过去个人的努力获得更大的成就;在科学领域,已有把研究工作与实验室结合起来,而不是单独搞研究的趋势;而如果这一趋势能够得到人们更多的注意,就很可能有益于科学事业的进展,因为它将促进合作。然而,如果任何重要的工作,不管它属于何种类型,都纳入集体合作的模式,那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个人的作用:他不再能够像长期以来天才人物表现出来的十足自信。基督教伦理道德讨论了这个问题,但在相反的意义上,它只是讨论了假想中的问题。一般认为,由基督教提倡利他主义和邻里友爱,它就是反个人主义的。然而,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错误。基督教诉诸个体灵魂,强调个人拯救。一个人为他的邻居做事,他做的缘由,完全是因为他该去做,而不是因为他在本能上是一个较大群体中的一员。在本源上,甚至在本质上,基督教是非政治的甚至非家庭性的,并由此而趋向使个体能比自然造就的自己更为自足自立。过去,家庭的作用在于抑制这种个人主义,如今家庭日趋衰弱,不再像以前那样扼制人们的本能。家庭的失去,正是民族的获得。很明显,民族所寻求的正是在工业世界中难以找到生存空间的生物本能。然而,从安定的方面考虑,民族是一个过于狭小的单位。人们可以希望自己的生物本能适用于全人类,但这在心理学上是不能成立的,除非整个人类受到某种严酷的来自外在的危险的威胁,如新的疾病或全球性饥谨。由于这类灾难实属少见,我看不出有什么引发全球性政府的心理机制,除非某个民族或民族集团征服这个世界。这在自然过程的发展中看来是不太可能的,也许在往后的一二百年时间内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在西方文明中,就如目前的状态,科学和工业技术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要比集中所有传统因素后的作用强大得多。然而不能认为这些新事物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已达到顶峰。现在的交通工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但是它们并没有达到无可指摘的程度。人类发展中可与工业主义发展相媲美的最近一次的事件,是农业文明。农业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才在地球上得以普遍推广,并且伴随它的扩展,一种思想体系和生活方式出现了。农业的生活方式仍未完全征服这个世界的贵族阶层。就像我们的狩猎规则所表明的那样,他们顽固的保守主义,很大程度上仍停留于狩猎阶段。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农业观点将在落后的国家和落后的阶层延续许多时代。
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西方文明的显著特征,也不是西方文明在东方所孕育的特点。在美国,人们甚至发现农业中带有工业的思想成份,因为美国本上没有农耕作业。在苏联和中国,政府具有工业思想观念,但是,必须让为数极大的无知农民满意。可是,在这一点上,有必要铭记:一个不会读写的群体,比像人们在西欧或美国看到的群体,更容易随政府的作为而转变。通过文化普及和开展正常的宣传,国家能够带领新兴的一代去鄙视长辈,其程度可以使美国最时髦的青年大为震惊,由此可在一代人中发生一种深刻的精神变迁。这一过程在苏联已全面展开,在中国刚刚开始。由此,可以指望这两个国家产生一种摆脱那些捆绑西方发展的传统因素的工业思想。
西方文明已经发生了变化,并正伴随着一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