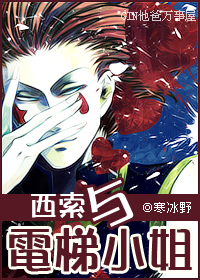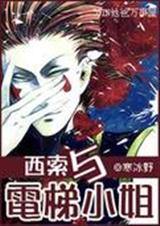���Ӱһ��˽��-��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ĵ����ߣ�˭�ֳܷ���������еȴ����������أ���һ����Ը�ij�������˵���ȴ�ֻ��һ����Ҳ�첻��ĵ绰������
�����ȴ��绰ʹ�绰�����Ļ���������һ�����ط�Χ�����й������εȴ��绰�ľ������ڵȴ��У��˵ľ�����������һ�־�ֹ��״̬��ʱ��·�Ҳֹͣ�ˣ��ȴ�������������������������Ļ�е�˶����Ķ�Ҳ����һƬ�հף��ڵȴ��У������ڴ��������⣬һ�ж�ʧȥ�˼��䡣���ȴ�����Ҳ�����ں��ϳ��Σ������ѳ��˱��������е��㡣
�����ڵȴ��������Ѿõĵ绰ʱ��ÿһ�ε绰�������𣬶��㶼��һ�ξ���尾�����Ȳ�������ץ����Ͳ��������ȴ������ȫ��ϣ�������IJ���֮�͵��������㻹Ҫǿ�̷���غ��ѣ���Ҫ�Ͻ��ҽ�ڣ��öԷ�Ѹ�ٹҶϵ绰���ȴ��绰ʹ�˳�Ϊ���ʵ�ū����ij��ij�µ�ijһ�죬�����Լ��ҵĿյ��Ŀ�����ȴ��ҿ�Ľ�Ѿõ������˵ĵ绰��������һ�ξ�������գ��Ҳ��ϵز鿴�绰���Ƿ�źã�������̫С���������������������䶼����ȥ�������죬������û���������ô��������������˵ĵ绰���������Ū�ˣ�������һ�쾹û��һ���绰������������֪����������ž�����·��ǡ�������õĵ绰��ͣ��һ�죬�������ɺϼ�ֱ���˷��衣
����1989��Ķ��죬���ں���ı���д��һ�����С��ȴ��绰����ʫ��д����ʵ���Լ���һ����ʵ���ܣ�ʫ�������ǣ�һ������һ����ڵ�ҹ�������Զ���������ʱ�䣬�ȴ������Լ��绰ǣ�ҵ�Զ������������Ůһ����į�ľ�ʱ�����Ų��ϵ�ǽ��ס̾Ϣ���Һ�ɫ������ȴ���ɫ�绰���õ�������д��д��д�����������ĵȴ������ڰ���������������һ�ԴԵġ��ܲݡ�������˵���ܾúܾ�֮�����ڴ����ˡ��ǽ�����������������ҿ�ϲ��һԾ����Ҫȥץ�ǰ�ɫ�Ļ�Ͳ��ȴ��֪����������������죬�����ڡ����ȶ������������
����ʮ���ȥ�ˣ��ǡ��������⡱����������Ȼ���ڶ��ߣ�������ȫ��ͬ��������Ϊ�����������Ϊһ�壿�ȴ��绰���ǵȴ�һ�ǡ��������⡱�����ǵȴ�һ�ξ�������У�
��
��������Զȥ��1��
��
����ʮ�����һ����������ڱ�������վ�ȳ�����������������һ�����µ����Ḿ����������վ̨���ⲽ�����ĸ߸�����ķ��ٺ����������Ź���ĺ�ɫԲ������£�ʹ���ľ��ͼ��ι��Եø���ף�����ҫ�۵ĸо������Ķ�ȹ��������߸�Ь����һϮ��ɫ��ͦ�ε�˫���ڱ����������Ҳ��������İ⣬��һ����վ�ͱ��������Ů������ס�ˡ�
������Χ�Ҵ���������Ⱥ�·����û�����������������˼�ؿ���ǰ�����е�ãȻ�������������������Ų��ӣ��߸�Ь�����ڵذ��Ϸ����������졣�����г������˼�������û���ϣ���վ������Լ����Զ��������һֱע����������������Ϊ���������Ų�����Ȼ����������һ���Ҷ�һ����֪�����������飬���Ļ�����ɫӳ���µ�ѩ�ľ�������������Ĵ���ʹ������ӿ����Ī���ĸж����ڴ�Լʮ�����ӵķ���ʶ���У��������ȶ��˷dz�Ũ�Ҷ�������˵�İ��⡣
��������������Ҿ��ǻ���һ����������ɬ�İ�������ע����һ����ȫİ����Ů�ӣ����ĸ߸�Ь�û�����ÿһ�����춼��ĵ������ҵ��ķ���
���������������Ÿ߸ߵ�̨���߳��˵���վ������Ȼɵɵ��վ�ڿտ���վ̨�����е�ʧ���������ݡ���ʱ�����ҵ����ֻ�е����Ĺ����������ĺڰ��У������������Ľ��������ĵ���⡣
��������ȥ�˶�ʮ�꣬����Ȼ�����ǵ������ɫ����һ��ת˲���ŵĺ���Ů�ӣ������ں�ɫ�����Ź������������Ҳ�������ҵ��Ժ������ҿ�����������߲�ɣ��Ư����Ԣ�⡣���������ڵ�һ�ס�վ̨����ʫ������������������ֵ��������������ķ��Ǻ���Ȼ�����һ���ǣ�������ŵ�����Զȥ��/������������ͷ��
����ֱ�����죬ÿ�����������Ӳ���������ʱ���Խ���ס����һ��������������顣����˼��Ϊ�λ�����������У�������˶Գ��Ӹ�̾ʱ�⡢���仨�����ഺ���������ܹ����ִ�����·�ϵļ�����������
�����ձ���������ɽ�������˵��������ʱ��һ��ƫƧ��ɽ�峵վ�Ȼ��ǻ��·���µĿռŵij�վ�������Ŀ̹ǵ�������������õĸ��ˡ�����ʱ���¾��ģ�һ��Ҫ�����ָ����õ�Ӱ�����Լ�¼�����������˺���ڶ�ӰƬ�У����������졢��Զ���������ͳ�վ������Ӫ�챳��������������ѳ��档��׳׳�������°桶С��֮�������һ�л��롰С�ǡ��ij�վ��ʼ����ֻ������ͷ��ȴ��ʮ�ֳɹ��ġ���Ļ�������龰��һ�¾ͱ������Ǹ��������ò������ͬʱ��Ȼ�ذ�ʾ�������Ǵӡ����桱��������ݣ�����һ����ʱ���ĸ��ˣ�Ҳ��������ӰƬ�Ļ���������ɫ����ƽ�ˡ�
������������Զ�������Ź��磬Ҳ���Ÿ�ңԶ��İ�������磬ͨ�����ϵľɾ�����ͨ��δ֪���µ��Լ�������̻�
�����������������ij�վ���ڵdz������е��ض��龳��������������ѩ�������ǻ�Ц�����������������ᡢ�����������������һ�����콫�˴�һ�����ϡ�����һ�����᳦��ϣ����е��˶������Ĺ��á�
����1999���ĺ�������ڹ���ʡǭ�����綱����������������ʩ���زɷã���������Ͽ�ȷ�������뵱�ذ��յ������ֵ�ƶ�����ҹ������ߡ���������ڳ�վ�뵱�ش��ӵİ��պ�Ա����ڻ����ѵij������У��Ҿ���������������Ѽ�Ԣ��������ij��ƶ���������ɽ��һ�ǣ��������������طꡭ����վ���˳���������ȥ�����е�����Ҳ������˦����ɽ�������һ�����촩Խʱ�ս����Ҵ����ҵ�����Ȧ�ӣ�������̣���������Ǽ�ʶ���Ķ��������ټ������д���������ǰ��������̨���Ǻܶ���С������綱�������Ǵ����������۵���ȹ��������ϸ���в���վ̨��������ˮ��ĮȻ�ؽ����ţ��������������ҿ�����һ��������������ʪ�����ģ�������ļ��䣬�������˵����ۡ�
�����ձ��Ľ��쿵����һ�����С�������ᡱ���������ݣ��й�Ӱ����Ϥ�Ĵ����Ǹֽ߲��������������������վ������ҹ�桷�͡�����Ա�����������Ȳ���������һ��ҹ��һ���������ˡ���վ���͡�����Ա����Ҳ������Ϊ�ڴ�̫�ߣ�������������˵�ӰƬ��������ʹ�����㡣�����ǡ�����Ա�����ⲿ��Щ��ܰ���������ӰƬ��������һ��С�����ʷʫ��ȴû����������ֵ����س������ϲ�ɣ���ֽ߲��·�������û�������������ע�ؿ̻�������Ŷ��ͱ�������ȱ����һ�����µ�����У�ʹ������Щƽ�滯����������еij���������˵ij̶ȷ�����ͬ���Ǹֽ߲����ݡ�ֻ�����������Ǻ�������ʱ�ڵġ���Ͽ����1999�꣬���쿵�������й����ʣ�����̸��������Ա��������ʱ˵����������Ա����������ͨ�ˣ������������桢����ҵҵ�ع��������ǵļ�į������û���ܹ����⣬�ⲿӰƬ�������ձ��������Ļ�������ϣ��������Ա��������ʹ������ʶ��ȥ��Ҳ�ܰ������ǰ������ڡ������룬����̫ע��ӰƬ�Ľ̻������ˣ���Χ������������ͻ����е�����ȱ�ٸ�ϸ�������������գ����߹��յò�����λ�����ϧ������һ�����õ���ġ�
��������������Գ�վ������Ϊ������ӰƬ�У���һ��û��ʵ������ĵ�Ӱ����ʮ�ֳ��ʡ�����Ǽ����µĽ�����վ̨����ӰƬ��һ�ְ����ķ�ʽ��������ڹ����һ���˳ɳ����������ˡ�û����Ƭ֮ǰ�������������������˼����µ����֣����Ƕԡ�վ̨�����������Ϸ�绯�㽺���������������ӰƬ����֪����վ��վ̨�Ǹ��������ڵģ���վ̨����������20����80�����һ�����и��������֣�ָ�������������ϵ�վ̨��ӰƬ��ʼ�������Ǵ����������ڱ��ݡ���������ɽ�ܡ�����ʱ����Щ������Ĺ���Ա������δ���������Ļ���������������Ѩ�ݳ��ľ����вſ�����ɽԽ��Ļ�Ϊ�˶�����質��
��
��������Զȥ��2��
��
������ij��������˵��ӰƬҲ����һ��վ̨��һ��20����80��������Ļ������Ǹ����Ĵ�վ̨��������ʫ�������衷�����ݳ�����������ɽ�ܡ�������̨���ڵص����и��������Ƽӿ��ȡ������Ƿ������ܡ������ɼ�˼�������Լ�������ӰƬ���ֵġ�վ̨��������˵�Ǹ�ʱ������Ҫ�������Ļ��ķ��Ŷ�һһ�ڡ�վ̨����չʾ�������¼Ƭһ����Ȼ�������д�£����˲�����ؿ������Լ��������ഺ����Щ��ɬ����Щ���֣���Щ�¶�����������궯�������˺����Ρ�����վ̨�������������ģ����ҵ����ڵȴ�����Զ�ڵȴ��������������������ģ�û��վ̨�ͳ��������ʵ��ȴ�ľߡ�վ̨�����ϡ�����������ζ�ĵ��������Ӱ�ľ��䡣
��������������������·�ϡ�����������ķ��Ż���ע�⡣���ҿ���������û���˰��������е�Ԣ�⼫�����˺��˵�������������������ĵ��ڴ��ţ���Ϊ��������˵ĸ���ȷʵ̫����ˡ�
***************
*�ڶ�ƪ
***************
���ڻ����о���ռ�ж���λ���أ���ij��������˵�����ǰ���ƽ�ȵĻ���֮һ��������Σ������������ǡ����������ǻ����к���Ҫ��һ���֣����ѱ�����Ķ�����������ͬ���������ںܴ�̶��ϣ����浽һ���ˣ����������˵����ϡ�������̨�庣��
��
������̨�庣��
��
��
õ�����ģ�1��
��
������ʮ����ǰ���Ҷ�������˹�з�˹������������õ�塷�����롶��Ǿޱ���������ⲿ����С˵����ɢ�ĺʹ������ǵ������У������Ҽ�����̵�����ƪ�����ij�������
���������ij�����������һ���¶����������ñ�����ʱ�仳���ף��һ��Ů����������¡���ƪ������Ľ�����ǧ���ֵĶ�ƪ���������������ı�����ϡ��ܳ���ί�У�����ʿ��ɳ÷�����ٰ����Ů����ɺ�ȴ��ط�������������ɺ�ȷֱ�ܶ����ɳ÷�����һ�����ҹ���ij�������һ�죬��ҹ�����űߣ�������ɺ�������ط��ˣ���ʱ�������������������밧�ˡ�������ɺ��һ�����������У�ɳ÷�е������г��������ĵ����⣬����ο�������뷽�跨����������ºͺá�����ɺ�����ڱ����˽��ߺ�ɳ÷��ʼ����ÿ���������Ƕ��ռ����ķ��������������յļ����ɳ÷ҹ�Լ��յش���Щ�ռ��ij����У�ɸ����ɳ������һС������������һ�侫�µ�õ�壬���ߵ�ϸ֦�ϻ��и�СС�ġ����Ļ��١�ɳ÷����ؼǵ��Լ���ĸ��������˵����������õ�������ϲ��࣬����˭Ҫ��ӵ��������һ���и�����ֻ������ˣ�����˭��һ�����õ�壬��������Ҹ���������Ҫ������õ������ɺ�ȣ�ףԸ���Ҹ���Ȼ����ֱ��ɳ÷�¶�����ȥ������õ��Ҳû���͵���ɺ�ȵ����ϡ�������������������һλ���ң����Ұ���д�������ǣ�������������˸еĹ��ºͺ��˵�줿�̾��
����õ���������ж��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