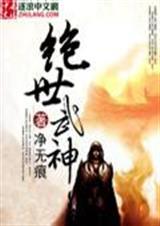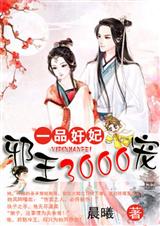当代-2005年第6期-第8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女同志一般见识。有得罪诸位的地方,我替她赔礼道歉了。武松准备痛打孙二娘时,张青不就跑出来说情吗。
这倒不是十字坡酒店的问题关键。关键是张青两口子开的这个酒店,是个黑店。经营的项目让人胆寒,有无营业执照且不说,他们明目张胆地图财害命真是骇人听闻。武松还算机警,也算万幸,否则真得给做了人肉包子。
读书读到这里,不禁会产生联想,如果按照现代观点来思考,这样的黑店,已经谈不到停业整顿,它的经营项目,已经超出了城管、工商、税务等部门的管理范畴,早就应该提起公诉,移交司法部门立案侦察了。可是看书中叙述的情节,孙二娘的黑店开得还真是平安无事。为什么没有人出面过问呢?
怎么回事?
是政府的问题。
读书至此,拍案惊奇。谈歌绝不会相信宋朝那个年代,政府管理社会的职能会差到哪里去,怎么着也是一个国家啊。总不能随便搞无政府主义吧?孙二娘开的这黑店(还是连锁店。三十一回写到武松被孙二娘手下拿住时,书中交待,原来这张青十字坡店面作坊,却有几处,所以武松不认得),杀人越货,血债累累,还卖人肉馅包子。官府如何就没有人管呢?按书中所写,大树十字坡酒店,地处一个交通路口,为南来北往的商客和游人必经之路,这应该是一个政府重点管理的地段嘛。但是政府在这里几乎没有派驻任何管理机构,连一家公安派出所都没有设置,如此失控,这里的黑店还不嚣张到了极点。人肉包子明着卖,蒙汗药随便用,无法无天到了这般骇人听闻的地步,政府的职能干什么去了?当地县里的领导干什么吃的?莫非一点耳闻也没有吗?而且总是有人在这一带失踪,就真的没有报案的吗?公安部门早也该立案介入了啊。如此这般太平无事,这里边就有官府与黑道儿联手的可疑。或许张青或者孙二娘的某个亲戚就是当地的某县长或者某市长呢。
好,就算你孙二娘或者张青先生有某个亲戚在政府的权力部门,那十字坡酒店就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进行违法的买卖?
就敢。而且太平无事。
依法经营应该是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倡导的一个商业规则,即便是最昏聩无能的统治者,也绝不希望自己的治下,出现无照经营、偷税漏税而无人管理的问题,更何况这种卖人肉包子、滥用蒙汗药的事情呢。
统治者的意愿归意愿,治下也就是两种情况。如果抓得紧些,治下便是清明些。如果无人抓,或者还有纵容,那么治下什么黑暗的情况都可能大面积出现,一部《水浒传》里,这样无法无天的买卖并不是一家,孙二娘的黑店只是一个例子罢了。有人可能要讲,这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结果,这是被压迫的生活底层人的反抗啊。可道理不能这样讲,孙二娘并不是这样干的,书中所写,大部分受伤害的,大都是过路的无辜商客和游人。武松发配途中,路过这里,也被麻翻了。武松和两个差人招惹谁了?谋害他们,就是与政府对抗?绝对不是。常常有这种嚣张的情况出现,即打着反政府的政治旗号,干着杀人越货图财害命的勾当。
读者千万不要用善良的心思去揣度这些好汉们,他们决非只是杀富济贫,决非只是对抗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政府官员,他们这样只是一种凶恶的生存方式。好,只要你们来到大树十字坡酒店下榻用餐,他们决不会耐心细致地检查你的身份证,也不会认真详实地寻问你的民族出身、家庭状况、政治身分。管你是张三李四,管你是穷人富人,管你是好人坏人,管你有党派无党派,一个字,杀。胖的做肉馅,瘦的去填河。这还叫什么好汉。
对十字坡这种酒店,政府应该坚决打击。有一个取缔一个,发现一个治理一个。否则,不仅仅会制造社会动乱,至少真要影响投资环境了。不要在意这种酒店给你县里带来的那点税收,也别在乎那点罚款。事实上,当代各地方的一些恶势力就是这样逐渐成形扩大并形成规模经营的。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联想一下,假如孙二娘的酒店再经营几年,再积累一些雄厚的资金,她手下的雇员也必然增加许多。以至于征地盖房,把酒店经营面积再扩大一些,盖一个十几层或者二十几层的“十字坡五星级宾馆”,再吸引一些外资进来,再享受一些地方性的优惠政策,地方上还能控制它吗?那时的孙二娘可能就有了几国的护照,出国考察还不得跟上厕所一样方便了。保不齐说,她还能在十字坡建立起一个超级人肉市场来呢。
别不相信。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孙二娘已经有了连锁店,再向外埠发展搞联营,强强联合,不是没有可能啊。
写到这里,谈歌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
诗人的失踪现象
李少君
李少君:男,1967年生,作家。现为海南省《天涯》杂志主编。
在一个变异多端、复杂动荡的转型时代里,诗人的命运总是令人揪心。因为,在社会大幅度的猛烈的急剧变迁中,单纯而率直的诗人似乎适应能力是最差的。就像自然界的那些敏感而娇弱的小动物,在地震来临之前总是惶惶不安,四处乱窜。诗人也似乎具有这样先知先觉的预兆能力,总能预感出时代即将爆发的猛烈的震荡,因此比较常人,他们总是很早地最先表现出一种特别的不知所措、无能为力的软弱。
因此,从诗人的命运中,常常能窥见时代的秘密与真相。有人说得好:诗人的命运里,浓缩了时代的隐私。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代诗歌史上那些最先逝去的诗人:海子,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诗人,在寒冷的冬季来临之前,在洪水般的混乱泛滥之前,将自己横卧在山海关前的铁轨上;昌耀,一个高原上的被视为生活的硬汉,最终忍受不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一走了之;顾城,一个梦幻般的童话诗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世外桃源,试图躲避冷酷的现实与矛盾,但最终走向疯狂,走向毁灭;还有马桦,本是浪子班头,混迹于豪华都市,有一天突然顿悟,要去过一种实在而宁静的生活。马桦去了云南边地,在一座小学的课堂里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然而风云不测,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永远地失踪了——这真的是一个暗喻:那些想寻找自己内心安宁的人,不得不从我们的世界里永远地失踪。
人们将这样的一些现象,概括为“诗人之死”。在二十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诗人之死更是被作为一个重大的事件,一个突发性的重大事件。诗人的死亡宛如突然爆发闪耀的绚烂的烟花,瞬间即逝,却又提醒着人们什么,预示着什么。
与诗人们的死亡同时发生的,是诗人们大规模的失踪现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是凌空蹈虚的时代,是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大肆流行的时代,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诗人无疑是舞台上的主角。到处响彻诗人高亢洪亮的声音。诗歌界高潮迭起。朦胧诗、第三代人诗歌;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等等等等,无人不知。但一转眼,时风忽变。似乎仅仅一个夜晚,诗人们不见了,消失了,失踪了。代之而起的是商业大潮汹涌而来,时代突然变成了一个巨型搅拌机,将所有的人和物都搅进去了,然后冷酷地不动声色地将那些不适应者像废渣一样吐出来。这是技术时代里机械的逻辑。这是弱肉强食的物质时代的逻辑。而作为心灵的守护者的诗人,在这样的生活和世界里永远是弱者。
当然,诗人们的突然失踪有各种原因与各种情况。比如食指,无论是诗歌黄金时代的八十年代还是诗歌低迷的九十年代,他都主要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除了那些不时去看望他的老朋友或仰慕他的年轻诗人,他大部分的时间据说是发愣,偶尔也写写诗。社会和时代似乎渐渐将他忘记了。除了偶尔将他请出来亮亮相,作为一种点缀与追忆。前年我在杭州“纪念诗会”上遇见他,他刚刚安稳下来,看上去像一个朴实的老人,但对当下有很多的不解与迷惑,他在餐桌上说出自己的疑虑,无人可以回答。诗会上,食指的诗歌朗诵得非常好,赢得了礼貌而热烈的掌声,但恰如那个诗会的名字“纪念”,一切仅仅是为了纪念。我呼吁颁发一个“纪念诗歌奖”给食指,获奖证书上签满所有与会诗人的名字,这一动议得到所有诗人认同。朗诵会一完,食指坐火车悄悄离去。他不参加其他的游玩活动,他是为诗歌而来的,与诗歌相关的活动一结束,他也就离去了。当地诗歌网站上的标题很准确,写着“食指来了,又走了”。还比如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被追认为朦胧诗第一人的多多,更算得上某种意义的自我失踪。本来,在八十年代的诗歌大潮中,多多就是一个相对被忽略的诗人。与其他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多多的影响力仅限于诗歌界内部。这一则是由于多多本身比较低调,二则是由于多多的诗歌充满超现实的神秘主义色彩,充满呓语般的预言,切中了那个时代的某种本质,但在当时的时代,人们反而看不明白。多多的诗显得比“朦胧诗”更“朦胧”。比如关于1970年代,他写道:“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那阴魂萦绕的古旧的中国的梦//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在这座漆黑的空空的城市中,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击声……”(《回忆与思考》),还有:“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携带着烟草和干燥的喉咙/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屁股上挂着发黑的尸体像肿大的鼓/直到篱笆后面的牺牲也渐渐模糊/远远地,又开来冒烟的队伍”(《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这些诗句,隐晦地表达出某种强烈的情绪。这样的诗句,比起后来的一些仅限于简单的表面的控诉、揭露与斥责的诗歌来,显然更得现代派精髓,也更曲折地直面了那个荒诞而恐怖的时代的真正本质。也因此,这样的诗句也更能传递出真正的对于时代的切骨感受。现在读来,这些诗句仍然使我们感觉身临其境,或许,这就是诗歌的魅力,也是诗歌的生命力,它比它的时代活得更长。但在当时,口号般的诗歌更受欢迎。诗歌活动家比诗人更走红。因此,先是真正的诗人从自己的时代里失踪,接着,朦胧诗的主要诗人们纷纷出国,诗人们又从自己的土地上失踪了。一去十多年,等他们回来时,一切都变样了。多多也是,在荷兰居住了十五年,过着一种与世隔绝也自我隔绝的生活。回来后,对于母土的变化一度显得迟钝,在离家乡仍然遥远的海口住下来后,就哪里都不想去了。他知道自己还在边缘。但他已安心于此了。诗人与诗歌不再像八十年代那么风光、受关注了。诗人们再次在人们的视野里失踪。他们如今居住在一些偏僻的角落里,还在默默地思索,默默地写作。
没有出国的诗人们在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差不多都失踪了。比如八十年代中期以狂飙猛进风靡一时的莽汉主义诗人李亚伟,是那个时代的强力诗人,他宣称:诗人“‘抛弃了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