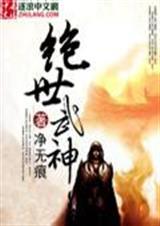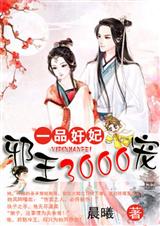当代-2005年第6期-第7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样贸贸然问起来,失了礼数,公公是要怪的。
如果是他的信,公公应该不会瞒她。每一次,他的信都是写给父母的,不过在信里都会提到她和孩子,公公看了都会念一遍给婆婆听,然后让婆婆把信给她,说,你收着吧。她每次都因此暗暗感激,这样她就可以背着人独自细看他的信,每天看,一遍遍地看,像按时吃药,吃了这个药,她才能该做针线就做针线,该教孩子识字就教孩子识字,该吃饭就吃饭,该睡觉就睡觉。多亏了这帖药,一天一天的,才能往下捱啊。
公公把丈夫的信交给她,而且说:“你收着吧。”老人看上去威严,其实是个菩萨心肠呢。
今天有信来,公公不该不给她看的。除非,是凶信?她心一紧,觉得浑身的血都倒流了。再看公公的脸色,不像是刚接了凶信的样子。那么,是自己多心了?不是那边来的信?
她去婆婆房间,看婆婆的脸色没有异样,心里稍稍安定一些。如果是那边出了事,就算公公还能掩饰,婆婆却不可能不露声色。他还活着!那么,那封信是谁来的?为什么不让她知道呢?会不会是他受了伤?还是……这一顿饭吃在嘴里,好像嚼的是泥是沙。
晚上,三个孩子玩累了,都睡下了。她心里发空,又从梳妆台的抽屉里拿出那些信来看,上次的信的末尾,他说“驱除日寇有日,返家团聚有期也。”这是对父母说的,但是她知道,这团聚里面,有她。这差不多是对家里人的一个承诺了,他既然这么说了,就会回来的,那个遥不可期的“团聚”会降临的,自己没有必要怀疑,更没有必要被恐惧吓倒。她觉得此刻他就在房间里,隐了身,在偷偷看她,准备嘲笑她的胆怯,没见过世面。
一觉得他在,她的心马上静了下来。听见小床上“咚”的一声,知道是又踢被子了,起身过去给孩子盖被子,女儿突然喃喃地叫了一声:“爸爸。”她一怔。这孩子生下来只见过爸爸一面,心里应该都没有爸爸的模样,难道是爸爸在梦里来看她了吗?他果然来了吗?看女儿的表情,父女的见面是愉快的。
可是对她就不是这样,好不容易在梦里来一趟,还要那样吓唬她。她低低地说:“你呀,也就会欺负我。”
还是睡不着,好像要找什么似的,她出了房间,一个人来到院子里。天空暗着,残月跌进云里,有几颗星星像垂死的眼睛。她的心情本来就恍惚,走进这样的夜里,越发的像梦了。祖宗祠堂那边有灯光。怎么会?真的是在梦里吧。她轻飘飘地走过去,却冷水浇头一般清醒了。供着祖宗牌位的长案前,公公跪在那里。他点了祭祖时才用的龙涎香,香烟袅袅上升,奇香扑鼻。
“列祖列宗,我今天跪在这里,要向你们禀报一事。国难当头,如今孩子奉命死守三峡门户,长江要塞石牌,若是日本人攻下了,重庆危矣,中国危矣。托祖宗余荫,孩子不愧是我们家的子孙,今天托人送来诀别书信,决意以死报国了。我一生碌碌,只生了这么一个儿子,他能为国而死,总算不辱没先人,我没有半点不舍得。只求祖先英灵保佑,此役关系重大,一定让他们守住了,就是死也要守住了,不要再让日本人夺了要塞!只要守住了,就是他死得好!”
老人说到这里,声音变了,变成了压抑着的嘶喊。
她腿一软,瘫在了门边。
不知过了多久,昏黑之中,她听见公公的声音:“孩子。”
她睁开眼睛,看到公公铁塔一样站在她的面前。
“孩子,好孩子,你是个明理的,你要挺住了。”
她看清了公公的脸,那张脸的每条皱纹都是痛楚,她失声哭了。
“爹,他真的回不来了吗?”
“回不来了!”
“万一这一仗打胜了呢?”
“那也是用命打出来的。他是军人,战死疆场,那是他份内的事!”
她如遭雷击,整个人一萎,伏在了地上。
“小声点!你婆婆还不知道,她那个身子也没几年活头,我们就瞒着她,让她走个安心吧。”
她噤住了声音,但是身体抽搐得更厉害。
她想起梦里他来告别的样子,原来那是真的。早知道是真的,她就会告诉他,如果他死,她一定也要跟着去。他知道吗?从嫁给他的那天起,她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如果哪一天他先死了,她绝不独自活在世上。
不过没关系,梦里来不及说,她可以追到阴间去告诉他。夫妻缘分到不到头是老天爷作的主,可是活不活,总还能自己作主。她是说过要好好奉养老人、养育孩子,可是那是为了谁?那个人既然对她说话不算数,她也可以不算数。
这样想定了,她止了哭,仰面对着老人,清清楚楚地问:“让我看看他的信。”
这倒要看看,到了最后,他对她就没有一个明白发落吗?
老人慢慢走回长案前,拿起一封开了口的,说:“这是写给我的。”又拿起另一封没有开过口的,“这是他给你的。我不该瞒你。”老人放下了信,迟缓地站起来,从她身边走过,回房间去了。
祖宗祠堂里,就剩了她一个人。对着一排祖宗牌位和丈夫的两封信。
她带着凄凉的微笑,站起来,走过去,伸手向桌上拿起一封,坐到那把从来没坐过的椅子上,仔细地舒展开信纸。
果然是他的笔迹。
“父亲大人:儿今奉命赴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恳望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
她静静地拿起另一封,细细撕开。这封笔迹潦草多了。“绣云吾妻:今奉命死守要塞,日军集结陆海空三军来犯,而我军孤军处死地,死国在即,身为军人,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教养辛劳,尽托付吾妻。十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今生已矣,惟望来生得报深情。”
她把信丢回桌上,嚷了一声:“我不要!”真的不要啊,不要一个人辛辛苦苦忍辱负重地活下去,没有他,她还有什么盼头,日子还有什么意义?他如果疼她,就应该让她跟了他去,让她从此轻松解脱,可是他这样狠心,这样逼她,这样强人所难!她捂着脸,重新抽泣起来。
过了半晌,好像听见远处传来什么声音,她停住了哭泣,侧耳倾听,却又没有。她勉强定了定,又把信拿了起来,仔细再看。
“今生已矣,惟望来生得报深情……今生已矣,惟望来生……惟望来生。”她拿出手帕拭眼泪,一点一点,拭得格外仔细,仔细得就像这辈子都不准备再哭,都不会再有一滴眼泪了。然后她抬起了头,眼睛里已经恢复了宁静。对着那个看不见的人,她低低地说:“你既然说好了下辈子,那这辈子我就为你守下去,守到死。”
看了一眼祖宗牌位,她走了出来,对着天空,她跪了下去。“苍天在上,四方神明……”
昏黑的天空中,有一颗原本暗淡得几乎看不见的星星,此刻,突然星光暴长,放射出惊心动魄、透人骨髓的光芒。
写于2005年8月
附记
从《中国国家地理》2005年第8期“山河抗战”特辑,读到以下史实:
1943年5月,日军为了打通长江,集结陆海空三军七个师团,向鄂西宜昌、石牌要塞发动猛攻。石牌这个当时不足百户的小村,成了当时中国战场最关键的要塞之一。年轻的守军统帅胡琏,在回答陈诚上将“守住要塞有无把握?”之问时,回答了一句:“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他抱定必死的决心,给家人写了诀别书信。(小说中的两封信来源于此,略有改动。)正是这种决心,使中国军队置之死地而后生,经过一个多月的血腥厮杀,终于奇迹般地守住了三峡门户。
谨以这个短篇小说,献给六十年前死守国土的英雄们,和同样死守信念的他们的家人。
雁山云影
程绍国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朱自清到温州中学教国文的时候,温州中学学生郑振铎、夏承焘、王季思已经毕业离校了。朱自清为温州中学写下校歌,唱到今天:
雁山云影,瓯海潮踪,看锺灵毓秀,桃李葱茏。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坐春风。英奇匡国,作圣启蒙,上下古今一冶,东西学艺攸同。
当时一个学生有回忆:
朱先生来教国文,矮矮的,胖胖的,浓眉平额,白皙的四方面。经常手提一个黑皮包,装满了书,不迟到,不早退。管教严,分数紧,课外还另有作业,不能误期,不能敷衍。同学们开头都不习惯,感到这位老师特别硏唆多事,刻板严厉,因而对他没有好感。但日子一长,看法起了变化:说起教书的态度和方法,真是亲切而严格,别致而善诱。那个时候,我们读和写,都是文言文。朱先生一上来,就鼓励我们多读多写白话文。“窗外”“书的自叙”……是他出的题目,并且由我们自由命题,这在作惯了“小楼听雨记”“说菊”之类文言文后的我们,得了思想上和文笔上的解放。朱自清还创造了特别记分法,他要学生在作文本首页的一边,将本学期作文题目依次写下,并注明起讫页数,另一边由他记分,首格代表90分到100分,次格代表80分到90分,如此顺推下去。每批改一篇就在应得分数格里标上记号,学期结束时,只要把这些记号连接起来,就出现一个升降表,成绩的进退就一目了然了。这种记分法,大大诱发起学生对写作的兴趣,激发起他们学习的进取心。
林斤澜无缘听朱自清上课。1923年,杜鹃花开的春三月,朱自清抵温,二个月后,林斤澜才诞生。十二年后,林斤澜就读温州中学,这时的朱自清,正抵清华大学了。但,朱自清给温州中学留下的影响有直接,有间接,但都是深刻和深远的。
比如,就林斤澜个人而言,写过散文《校歌》,并在《校园生活》、《山深海阔》、《雁山云影》、《读雁山云影》中对朱自清有所叙述,甚至在小说中也隐约提到。
林斤澜与马骅、唐湜、赵瑞蕻都是温州中学三十年代的学生。这是继郑振铎、夏承焘、王季思之后,照亮文学星空的又一拨人物。两拨人物联系不多,郑振铎生在温州,长在温州,好像从来不认自己是个温州人。他似乎只认祖籍福建。有联系的只是唐湜和王季思、赵瑞蕻与王季思。唐湜是王季思的外甥,有血缘,后者对前者的指引不必赘述,而赵瑞蕻是王季思的学生,有诗为证:
在中山大学茂林繁花的深处,
我们品尝家乡美酒,促膝谈心;
春草池边的笑声仍在我心上淹留——
是您首先把我领进了文学的迷宫。
王季思《从春草池边说起》也说:
这温州城里原十中初中部的春草池边是赵瑞蕻童年学习的课堂,也是我大学毕业后最初上课的讲堂。
年龄赵瑞蕻最大,在温州的友人中,他和马骅的关系最密切。马骅在《烂漫的梦魂永在梅雨潭》中写道:
我和瑞蕻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我们从十中附小、十中初中到温中高中一直在同一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