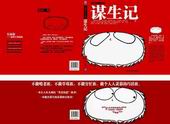风动红荷 作者:张丽-第3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几年中,于莺一直受着良心的折磨。她经常偷偷地在夜里摸进郭庄,在大宅附近转来转去,向老乡打听九九和正信的生活情况,知道他们过得挺好,就放心地回城里去了。
一直到1975年那个火辣辣无雨的夏季,她有天夜里进村,却发现大宅里没有一点灯光,死气沉沉,门窗紧闭,好像屋里的主人不复存在了。
她终于打听到九九死去,正信被送去荣军院的坏消息。她在暗夜中跑上公路,丢下自行车,坐在黑漆漆的公路边放声大哭了一阵子,便爬起来,连夜骑自行车往城里返。天亮之后,她回城找到了荣军院。
正信在那里的状况让她更加痛苦。
正信已经苍老得更加可怕,半截身子已萎缩得惨不忍睹,每天靠在轮椅中,不说不笑,有气无力,从早到晚沉默,好多人都以为他除了肢体严重残缺、双目失明,并且又聋又哑,没有零件是好的,只剩下鼻子喘气,嘴巴喝水吃饭。
于莺鼓足勇气上前去与正信相认了。她向他忏悔了自己许多年来内心所受的折磨,还有不可磨灭的对他的思念与挂牵。她向他哭诉了这一切。正信听着,也失声痛哭,反复说着“我从来没有怪过你,我希望你和孩子过得好”这句话。
于莺决定这次一定接正信回自己家,决定照顾他的余生。正信坚决的拒绝,并要于莺答应他,在他死后把他的骨灰送到九九身边,把他们夫妻合葬。他一定要于莺亲口答应他。
之后于莺母女就轮流去荣军院照顾和陪伴正信。但终也没留住正信,一天夜里,正信离开了这个世界。
清晨护士们发现他死去时,她们靠近他的床前,看到他很安详地睡去。
他去与九九相伴了。他们将在一起长眠。
于莺忍住巨大的痛苦,带着女儿援朝办完了正信的后事。
在一个细雪铺满山间的银色冬日,娘儿俩把正信的骨灰捧回郭庄山里,在崔支书等人的帮助下,葬入了九九的墓穴中。
回忆到这段伤心的往事,于莺阿姨忽然一阵脸色苍白,双手不停地抖动,声音微弱地喊了一声:“秋儿,拿药来。”喊声虽弱,小阿姨秋儿却听到了,从楼内闪身跑出,边跑边已拧开了小药瓶的盖,数出几粒小药丸迅速塞到于莺阿姨的嘴里。我紧张得一阵手足无措。秋儿说,阿姨心脏不太好,服了药,扶她去躺一会儿就会好。
我望着这位七十多岁体弱的老妇人被搀扶进楼门,那白发闪闪地隐去了,眼泪不知不觉地流出了我的眼眶。
第二十一章
秋儿安置于莺阿姨躺下后,就过来招呼我到客厅坐,又给我上了点茶,洗了一盘“血桃”,是胶东半岛最甜最软硬适中的桃子,在北京三十多年从未吃到过这种桃子。北京只有家乡的阳梨,北京人和其它地方的人不甚喜欢,因为它的样子有些疤疤拉拉,而现代人吃东西往往也像选恋人选衣服一样只注重外表的光鲜。其实产于胶东半岛的莱阳梨是皮糙肉细,香甜脆口有之,面软密齿有之,是其它任何单一品种的梨所无法比拟的美味梨。反正我这个生活在北京几十年的胶东人,顽固不化地只对烟台苹果莱阳梨情有独钟。这些年又有了半岛大樱桃、小香瓜之类的水果在北京市场热销,我曾去采访过的胶东部队单位,同那里的领导成为好战友好朋友,一有车来,他们就给我带来大樱桃苹果什么的,我分送给大家尝,人人都夸赞说从未尝到过有哪种樱桃能赛过你们胶东的大樱桃,个儿大如小杏,甜蜜蜜里透着点酸! 有“血桃”诱惑,我就根本不想吃午饭,这种桃一口气吃上十个八个就饱了。于莺阿姨毕竟是七十多岁同我母亲年龄相仿的老人,应该让她好好睡个午觉,伤心的事慢慢再聊,等她精神体力都好一些时再说。
我掰了“血桃”吃,老家人吃“血桃”都是掰成两半来吃,我也是打小养成的习惯。秋儿给我打开电视,怕我寂寞,然后就去厨房忙活。
电视里正播放歌会实况,我喜欢音乐与戏剧,任何流派的中外音乐和任何地区的戏剧都喜欢,从不排斥哪一种,各有各的风味儿。现代流行曲正在进行中,舞台造势神奇而充满着缤纷的迷眩。六首歌曲的微醺恰似六段不同的恋爱故事,恣意得狠。《算你狠》的浪漫绝对够味儿也够狠,当然也只有如此嗓音才可以在表达被爱捉弄的伤痛时透出格外诗意的伤感。
我把电视音量调低,既怕吵醒老人又盼她快些休息好,再继续那个没有结局的故事。郭璋这个被取消了户口的亡者,是如何活过来的? 是压根儿公安局就搞错了? 他这些年,整整三十六年啊,他在哪里生活? 难道他就没有回过一次老家看望自己的爱女爱婿? 他是怎样同于莺联系上的? 既然他能够同于莺联络上,那他为什么不同九九夫妻联络? 他一定早知道九九夫妻在1975年的夏季和冬季相继死去……还有,从他家挖出来的那批古董到底是为什么人保存的? 这么一大笔财产,人家为什么五十多年都没有来找过? 件件同治年间康熙年间的宝贝,如同被遗留在隔世的梦里。
我突然脑子闪出一大串猜测,比耳边的音符跳动还快。财宝的主人是旧社会的资本家? 地主? 国民党大官儿? 郭璋是解放前带着这批财宝回乡下的。那么有可能财宝的主人逃去了台湾至今无法回到大陆? 也可能在逃去台湾的海上被人丢下海去。因为在那时的仓皇逃亡中,每艘船上都严重超员,遇到风浪时,经常有人被丢下海去以减轻船的负载恢复船的动力。再不就是留在大陆,早就死了? 你想,经过了从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到后来的“肃清革命”、“四清运动”、“整风反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运动,一场场人民战役,什么样的鱼还能漏网? 旧社会的大资本家大地主大官僚,有血债的不是给枪毙了就是专了政,剩下的留给历次运动去修理,“文革”中被斗死的也有,跳井抹脖上吊的也有。如果还留有一条命,五十多年了,他总该露头儿吧?而这个郭璋,没有死仍活着的郭璋,历经苦难五十多年还在为别人守着财宝的人,在许多人看来,会认为他精神很可嘉实际上是傻瓜。
但是我却能理解他这半个世纪多的守望。胶东人的传统,道义最为先,别人钱财绝不会往自己腰包装,别人的永远是别人的,别人托付的事,至死都要守着这份信用。少年时,在郭璋大书房的炕上读书时,每每抬眼都能看到一面墙上的一幅字:厚德载物。那时候我还不太明白这四个字的意义,只知道那是他把自己的座右铭挂在书房,时时提醒自己如何做人。
时间过去了一小时,于莺阿姨的房间还没有动静,估计她正睡着。
我换了一个频道,正播放外国摇滚乐队的演唱。人在心情沉闷时,听听摇滚和爵士乐便可以振作起来。画面上是那个几乎具备了拉丁男人所能拥有的最完美的外形和气质的摇滚歌星,脸形粗犷,腮与双唇间的胡须连在一起,散射一种难以言说的气质,眼神坚定而深邃、纯正却暗藏火热,嗓音略带沙哑而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因上军校学的是英语专业,我对摇滚、爵士、交响乐这类艺术特别偏好,一听就上瘾。
又是一小时过去,我陶醉在节奏狂放的音乐里,没有杂念,也不觉等待的时间有多久,其间秋儿为我供应了三菜一汤一碗面条的可口午饭,我就这样边欣赏音乐边进餐,完全忘记已吃进了四个大“血桃”。
摇滚热闹之后,是一部情感电视剧,以前看过十几集,大概给我的认识是,只要男人和女人尝试过什么叫做嫉妒,整个人都可以变得阴险狠毒。
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好不容易相见,也只来得及交换脆弱的誓言,还不知道有没有兑现的可能,我就关了电视,心想,所有的箴言都已落伍。唉,海上花已谢,太平洋不再伤心。
我听见楼上于莺阿姨房间的门响了,她拖着软底的拖鞋走下楼梯。我站起身迎上去,吃惊地看到她的脸色十分苍白,这一觉睡的,好像使她老了十岁似的。我搀扶她迈下最后一节楼梯。秋儿闻声立刻从保姆房出来,问奶奶在哪儿吃饭,于莺用手指指院子的小花园。
我搀扶她重又坐到草坪上的休息椅上,下午的阳光基本被头顶上的梧桐树叶遮住,只从空隙里射下道道金丝线样细柔的太阳光,令人感到很舒服很惬意。退休老人每天坐在这里听着山风松涛,呼吸着新鲜空气,身沐柔和的阳光,挺养身修性的,有利于长寿。坐在这里不禁又使我忆起那片荷塘,塘边摇曳的石榴树与绿柳的枝叶以及那两个相依相偎享受阳光的男人女人。
秋儿给于莺阿姨端上一碗小米粥,几块小地瓜,一碟咸菜丝上面泛着芝麻粒儿。老人就细嚼慢咽地吃起来。我怕她着急,就起身跟秋儿去欣赏院里的鸢尾花。这种花为高雅的蓝紫色,花形似翩翩起舞的蝴蝶。这高贵的花儿令我兴奋,赞不绝口。我看于莺阿姨的脸上略微扫过一丝兴奋。秋儿说这些鸢尾花是奶奶一手照料的。
于莺阿姨小声地似自言自语道:“正信上高中时曾是个腼腆男孩儿,追风少年。到了大学,他就变得神采飞扬,活力四射。那时候,我就用鸢尾花比喻他。所以他就只喜欢这一种花,还霸气地命令我也只能喜欢这种花。所以我这一辈子就只种一种花,甭多管它都活得神采飞扬活力四射。我种别的花,种什么死什么,没有一种能活,更不用说开花了。”
鸢尾花……荷花……鸢尾花……荷花……这两种花在我心中交替闪亮着。鸢尾花,正信他喜欢,而且能观赏,只是好花好景不长远。
从战场归来之后,他就再也见不到这种花的美丽了,只能把它留在记忆里风干起来了。而那一池与他相伴了二十多个夏秋的红荷,他都无缘亲眼欣赏它们的花姿,他只能听九九给他描述那些荷花在风中如何地点头,如何地绽开笑脸,然后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听荷、感悟荷! 而在他的生活之外,却有一个人一直在种他心爱的鸢尾花,一直在他辞世后的三十年里依然在种着、欣赏着、陪伴着。正信在天之灵会知道吗? 于莺阿姨吃完饭,又继续上午的故事。
往事尘烟。她的续篇令我非常吃惊也非常压抑。幸好在我眼前的这个院落是宽敞的,一切也都是透亮的,否则,在狭小阴暗的小屋里听这样的故事,非得控制不了大哭一场不可。
1977年的秋天,刚同丈夫孩子们一起搬进这里的于莺,每天都是心情愉快地忙进忙出营造新的温馨家园。房子够大,花园够大,收拾起来都让人孜孜不倦。孩子们都不小了,各占各的领地,自己的天地自己做主。
忙了两个多月,天气有些凉意,楼内楼外都已秩序。这天上午,老两口出门去爬山锻炼刚走出不多远,老头子就喘得厉害,但他死活不听于莺劝,继续往山上走。他在抗日战争年代是指挥后勤汽车运输… 连的连长,带队驾驶着从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缴获来的旧卡车往前线运送弹药给养。他们的车队冒着敌机轰炸的炸弹,穿越重重伏击,勇往直前地狂奔不停。当他老了的时候,每当回忆起那个年代,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一团火,都接受了孤胆英雄的梦想教育,冲锋陷阵出生人死都能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