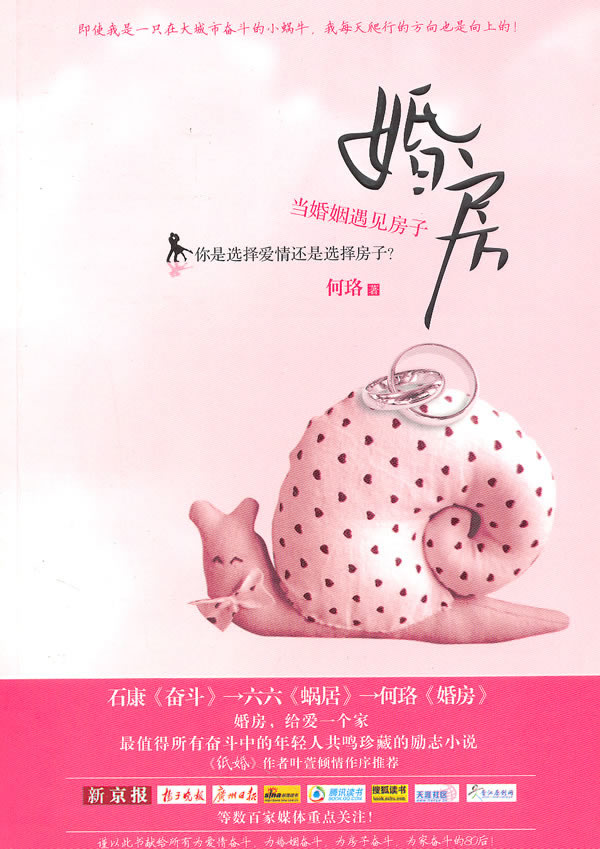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爱情-第9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和以往一样,这回还是从局限在我自己的极其私人的问题开始讲吧。干脆回到故事的开头问问自己:最近我常挂在嘴边的所谓“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者”,这些语词具体有着怎样的含义?再次澄清一下:虽然故事已经讲到了这里,但我仍然没有要赋予它们超出我们通常使用的一般性含义的意图。尽管带着历史性的浓重痕迹,但对我而言,无论何时何地,所谓无政府主义者的话语始终闪耀着新的光芒,可以说它们同时具有向内坍缩的否定和虚无性的含义和往外扩张的肯定而发展性的含义。当然,对无政府主义这一概念而言,因为它是激进性的否定,所以终究能获得肯定的领域。反过来,由于它在本质上是肯定性的,所以会以可疑的否定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这并不是说它具有两面性,而是说其自身既是二,又是一。现在有些相关的言论令人莫名其妙,应该从刚才所说的那种视角去看待它。
不过,理所当然的,我小说中的“无政府主义”并没有留在那种单纯的含义中。不,说得更严谨一点,应该是我急切地希望并不是如此。在我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一直致力赋予这个词以好几个方向的多义性,其中之一是要明确地意识“我是、无政府主义是、对某种东西的无政府主义”。因此,我并不是以小看我们人生的价值形态或意识形态为前提,耻笑他们而谈论无政府主义的。说得冒失点,我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对付成为人类自由之绊脚石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制度性力量——如果有必要,就与之展开斗争——作为我自身意
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来实施我的文学行为而已。
在我所确定的方向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现在做的是文学。因此,我的“无政府主义”首先是文学性的无政府主义。文学性无政府主义成为我的无政府主义的脚踏板和出发点,二者差多是一回事。对于写小说的我而言,文学包含了个人、社会等所有的现象。因此,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会被并非文学本身的背景和各种价值、现象所迷惑,而无法靠近真正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或许这确保了我可以逆向性地怀疑无政府主义的所有基准,令其不致于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堡垒。
这两种方向性,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是相互冲突的。但我并不惧怕矛盾。矛盾其实是我们人生的条件。因此,不能为了躲避矛盾而犯下使自身或历史成为矛盾的决定性错误,更不能怠慢那些相互矛盾的事物有着怎样的关联,以及那种关联将会如何变化和发展等等问题。
不过,在此处这样说话的我,其实并不知道我的无政府主义具体会在怎样的脉络中,以怎样的姿态落定尘埃。那个事实让我感到不安,同时也让我心中踏实。回头去看,这一期间其很多小说家都回避正面探讨、简直可以说是擦肩而过的若干问题,包括完全无历史性且虚无主义,甚至会蒙受败北主义嫌疑的问题,即无政府主义问题,我都企图以自己的方式接近它。我认为,在这个公然形成制度性压迫的社会里,无政府主义者清净的声音不管以何种方式,都要马上流露出来,溶入志向自由的流动之中。不过,实际上我也非常清楚,不清净、也不鲜明的自己的声音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我无非是怀着能实现最终自由的纯粹而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开始而已。
身处各种混乱之中,还要说出如此肯定的话,我知道自己会让许多感到非常可笑。他们会想:看你最后怎么收拾!我承认不太清楚以后怎么收拾;但是,对我而言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我现在只不过是以回头看的方式,来看所谓无政府主义的概念而已。作为小说家的我,希望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也希望以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来写作。为了肯定地表示我的想法,我想在这里再加上一句,“反过来怀疑怀疑的视线,或原封不动地接受怀疑的视线”。
那么,这样的无政府主义与叫做《赤身与肉声》的小说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我非常认真地问自己这个问题,然而,我眼下只能以关于写作的写作、根源的瞬间、会聚在一起的小说之间的关节或纠结,以及用裸体感知的新的感受、用“肉声”搭话的新的经验等等来回答。就是说,我想在这部小说里以我的方式全力以赴地去实现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写作。不妨再极端地引出异说意义上一个观点,那就是:我想通过这部小说阐明的并不是这样,而是正说着的这些。
我还怀有这样的想法:对于写作的人而言,向写作本身的问题接近,冷不防一想,好像不是与世界的沟通,反而是掉进了自身封闭性的内心世界里。可是在我看来却并不是如此。相反,现在的种种写作不顾所使用的语言的差异,形成了形式上的共感性,所以最切实地钻进写作的问题里,暴露出自己所处时代与空间问题的,恰恰在本质上具有能克服文明之间界限的可能性。这或许是多余的话,但必须要说明的是,谈论文学的普遍性并非像有些人误会的那样,是指我们向着西方文学前进,而是指超越已经展露出全面目的西方的想象力,向着这个时代普遍的中心、普遍的共感性前进。那是我们立足我们的视角和方向,以指向普遍性的一种方法。普遍性终究也是从每个个体开始,经每个个体的视角所合成、修整、补充后,形成一体而获得某种展望的。此时,那种理想化的普遍性与调节和控制个人的集团意识形态是截然相反的。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区分集团意识形态和普遍性的。
这里再让这个故事的脉络转个弯。我打算让《赤身与肉声》就这样以相对独立于前面三卷小说的状态存在。这是属于注重小说与小说间的关节与个别独立性的我的想象力小说;而且我自己也希望,能从已经被大概做成的那些很大的团块,那些经过认真的揉搓后,再相互粘贴在一起的繁琐而漫长的事务中得到自由。这是因为,虽然是暂时性的,但我还是负责这部小说的人。
我的这种关于自己小说的界定性发言,从批评的角度看,无疑是一种使自己的写作失去意义而变得落魄的行为。但我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当然,我的观点无可无不可;不过,极其矛盾而又非常有趣的事实是:无论那些批评的观点是为了支持、突出我的立场,还是为了对我进行攻击,总之,都是我的小说所乐于引用的。
不管怎样,谈到这个程度,或许多少能表明我对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了吧?进一步说,从个人的角度谈自己的文学,多少是在为保持对韩国文化的宏观视角而努力吧?思考片刻后,不,用不着思考,我马上得出了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的结论。但是,我不能从头至尾都乘着一条叫做文学的又小又破旧的船,更不能鲁莽地出海,否则,说不定会因为不必要的贪心而迷失归程呢。
就这样结束这一段落时,我想明确表明,至今我在《赤与肉声》中一直小心翼翼地区别使用“这些文字”与“这部小说”。用不着长篇大论,前者是指组成小说的每一个当下的部分,后者则是在整体范围内唤起这部小说。我敢说,这表明我始终深切地关注着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联,并表明我处处留意着写这部小说。不过,想到这部小说的整体究竟刻画出了怎样的轮廓时,我的心情又变得错综复杂。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现在真的该结束这部小说了。我忽然感到了不想用“结束”,而是想用“完蛋”一词的冲动。不过,这种冲动只是在说话的瞬间多次重复的经验,反复的行为以其自身唤起我的怀疑和反省。那么,现在应该首先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与结束尚未有任何关系似的,继续紧张地讲这个故事。应该说读者们比我本人更能清楚地意识到结束已经不远这一事实。我希望读者们不时地翻翻此书,以确认到结束为止还剩下几页,并以此来慰籍这个漫长而无聊的故事。
我曾经说过,在这部小说里,我一再与想坐上飞毯的欲望展开斗争。最终我也没有那么做。乘坐飞毯意味着出去旅行,而旅行可能有生命力与性的意味。因此,说不定这期间一直坐在小说里和书桌前的我,是在浪费我身上尚存的年轻的可能性。这部小说一旦这样结束之后,就不会再对往日的我做出任何具体的证言。因此,或许往后忽然转过身看的时候,这部小说会像一个皮厚又光滑的鸡蛋一样,轻巧地坐在我的手掌上。想到这一点,我的心中不禁涌出一股惋惜之情。
回头去看,在写这部小说的大约两年内,作为普通人和小说家,我身上都发生了许多具体变化。我首先想到,并且要向读者报告的是,大概从六个月前开始,我不再用电动打字机,而是改用了个人电脑。但我不想再罗嗦什么写这部小说所需的用具。打字机与电脑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技术性差异;不过,我跟电动打字机打交道的过程中所获得过的认识上的东西,电脑是给不了的。它俩与写作间的关系,从结构上看有不少相似之处。当然,电脑能大幅度缩短工作时间,增加工作量,这一点虽然并非是无关紧要的琐碎小事,但是,我并没有因为用电脑而受到任何自我意识的刺激。我甚至感到,从我的内心里向各个方向伸展着的某种东西正在萎缩。例如,有一天,不知是谁告诉我说,烟雾对电脑有害。从那以后,我不得不抑制自己写作时想抽烟的欲望。比这更成问题的是,使用电脑的时候,总是甩不掉我不仅是作家,而且是机器的某种不快感。人们忠告我说,一旦熟练到运用自如的时候,就能摆脱那种感觉;可是,按现在的状况来看,我更多地被自己身体的某些部分已经成了机器装置的零件,或是我光溜溜的身体上装载着电子零件这种非常夸张的感觉所纠缠。不过在现今时代,不也有人真的把人工器械装入自己的体内了吗?而后过一段时间便忘却了这一事实,似乎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泰然自若地活着。
到现在为止我只是在说我个人对电脑的见解,但是,我觉得电脑不仅对我,暗中对我们的写作所带来的影响也很深刻。因为现在还没得出什么结论,所以无法很有条理地予以说明;但是,最近我一再想到,电脑所具有的便捷性,其组合与解体的几乎是自发性的瞬间发力与自由感,是否与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写作方式在形式和构造上有更多的关联呢?不过,关于这一点,就我的立场我还不能予以更准确的表达。
作为补偿,我打算说一说曾经作为这部小说主人公的非人格存在,即我的打字机,与我之间最后一次发生的关系。事实上,至少是在写小说的时候,打字机现在已被电脑所替代,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废物。不过,前几天为了结束这部小说,我终于在某一摄影师面前,以裸体摆出一个姿势照了相,那次打字机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不管赋予怎样的意义,几乎脱掉所有衣服照相,真的算得上是一件苦差事。而且,因为发生了意外事件,我不得不一再经历在摄影机前脱光的那种侮辱或是困扰。每当那时候,那沉甸甸的打字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