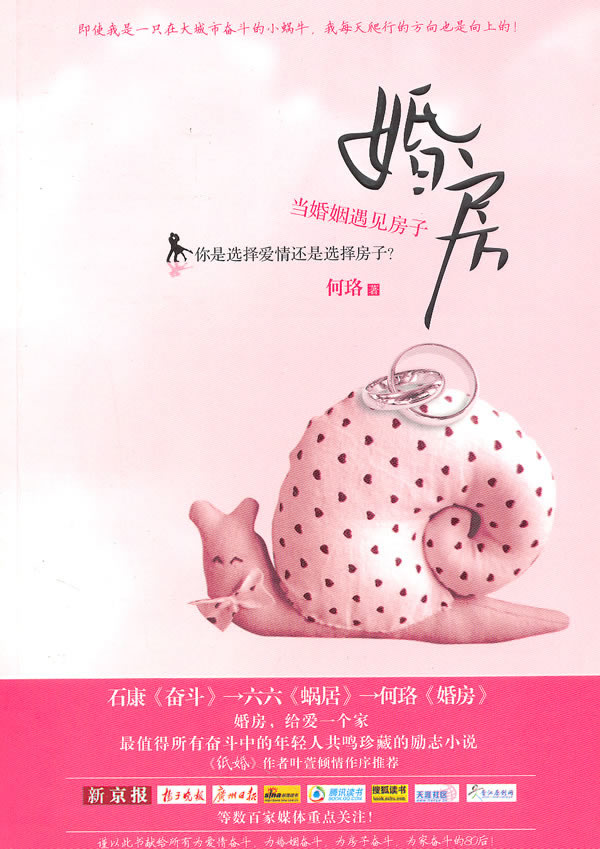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爱情-第6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赠送一件青年学生在国土纵断巡礼大行进中要穿的T恤衫。
引起整个民族、所有同胞关注的南北学生会谈时刻将近。由以南的青年学生发起,以北的青年学生积极呼应的此次板门店会谈,是为了解除民族分裂之痛苦的祖国青年学生的充满爱国赤诚之心的民族大事,同时又是必须要成就的绝对正当的一件事情。
生活在日本的侨胞学生,作为同一民族的青年学生当然也不能懈怠。我们始终为了实现这光荣的伟业而努力着,成立了包括113所大学的侨胞学生和朝鲜大学学生在内的“为了实现南北学生会谈的在日侨胞学生联合促进委员会”。我们决议汇集我们的力量与智慧,制作南北学友在国土纵断巡礼大行进中要穿的T恤衫送给他们。
这件衣服里浸润的,是尽管身在异国他乡、但要与祖国的学友一起站在统一战线上的在
日侨胞学生们的热忱志向。
一分为二的祖国土地被一条行进路线所连接。南北学友在板门店相互拥抱的那一天,作为渴望统一的热忱之象征,希望一定要穿上这件衣服。
为了实现南北学生会谈的在日侨胞学生联合推进委员会
1998年7月,日本,东京
是既简略又铿锵有力的文字,但是为了急于表现意志的鲜明性而显出些许粗糙感。况且尽管他每次都试图理顺,但意思不通的地方还是有几处,词语之间的空格也被忽略。不仅如此,把“T偕茨”写成日本式的“T夏茨”,也不免让他心里感到一阵凉意。当然这些和他们实际上已做到的相比较,都不过是极其琐碎的点点滴滴;不过既然用文字来表明所思所想,却疏忽了韩语的文法,终不免让人感到他们对于即将要成就的事情,相比严正的认识,更多的是抽象的热忱。对细微事项的疏忽——或许是杞人忧天——说不定会成为他们的陷阱。
他不知该如何接受在他们眼里已经是老一辈的自己也收到了这件物品的事实。不过他暗自下决心,不再想那些相关的问题。他再次抖开T恤衫,白色的布料和蓝色的图案与字都很和谐。但是他仍然嘟囔着抱怨道:“为什么非得是白色?有时候也可以用更强烈的色彩嘛,哪怕是像那些无聊透顶的香港影片的血色呢。”
他把T恤衫放在膝盖上,脑海里不知不觉中浮现出给他送来邮件的那个男人的脸。他之所以想起他,可能是因为那件T恤衫的白色谙柿痢D歉瞿腥丝隙ㄒ泊蚩⒖垂羌⺄恤衫,十有八九不会有什么想法,只会随心所欲地破口大骂。朴性稿随即闭上眼睛,他怕再想下去就会永远忘不掉那个男子的面孔。不过他又马上睁开了双眼,然后一边想说不定已经来不及了,一边从椅子上起身。T恤衫在他的腿上停留了片刻,随后顺着大腿像树挂或昆虫的残留物一样哧溜滑下来了。
走出酒馆时姜圭真明显神情疲倦。朴性稿半开玩笑地说,不能驯服于政府的这种处置,所以应该像个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找一个隐秘的地方再喝一杯。但是姜圭真只是笑笑,朴性稿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一会儿,他们的车开到了市内一家旅馆门前,姜圭真似乎已经预定好了,先爬上楼梯从服务台取了房间的钥匙递给他。朴性稿从他手中接过后说要送他离开,姜圭真稍一犹豫后便也点头同意,二人一起下了楼。姜圭真一直在酒后驾驶,多亏道上汽车并不很多,因此朴性稿倒还能放下心来。
送完姜圭真回到客房,朴性稿随便冲了个澡,脖子上挂着毛巾在房里踱来踱去。精神和肠胃、嗓子都感到极度疲劳,但身体却不觉得很疲惫,所以为了早点入睡似乎应该再活动活动身体,多少放松一下;否则以这种状态躺在陌生的床上,恐怕会被失眠折腾一个晚上。说不定连失眠也会变得陌生,令他束手无策。
他在房间里一直踱到腿发麻才上床,但仍然无法轻易入睡;好不容易入睡了,却又很快再次醒来,一看表才过了二三十分钟而已。他原来就有在陌生地方睡不着的毛病,但是像今天这么严重还是最近以来的第一次。到凌晨四点左右时他终于还是起来坐到被子上。在他看来,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极其不自然,在那里翻来覆去的自己也同样不自然。虽然也想过试试再喝一点,但是照他目前脑袋发晕、肚子发空的状态来看,几杯啤酒之类根本不能解决问题,除非干脆喝一杯加了毒品的酒把自己放倒。可是这么晚了,到哪里找毒品呢?于是他几乎是下意识地拿起电话,迷迷糊糊地问能不能叫小姐?电话中女人的声音丝毫没有要掩饰睡意的意思,似乎嘴歪了一样反问道:“都这个时间了,哪有人愿意来啊!”他只好默默地放下电话站起身来,然后脸也没洗,穿上衣服走到外面。外面还真像个典型大陆性气候的地方,清晨的空气中涌动着凛冽的寒风。
一会儿工夫,他就走到两个中年女子跺着脚站着的地方。抬头一看是市区巴士终点站。即使坐上出租车也没什么好去处,于是他就随着她们跳上了刚好到站的巴士。似乎是辆刚从车库开出来的车,里面也是一样地冷。意想不到的是座位上几乎已经坐满了人,有些两三个一丛聚在一起站着,还有几个可能身体还僵着,站在空座旁边凝视着窗外。车窗上还没起雾,迎着晨光那一面的玻璃,在冰冻的大气中发出耀眼的光芒。他纹丝不动地望着乘客们的样子,突然联想到莫名其妙的画面,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一瞬间一阵寒意透过脊梁传遍全身,他不由自主地颤栗着。
他的两只眼睛因恶寒而缩成一团,透过眼睛能看到寒冬的窗外正下着夏天的梅雨。巴士正在雨中疾驰着。不知是不是天花板漏了,有雨水渗进了车厢里面。可是怎么看上面也没有雨水可以渗进来的地方。终于到处都开始滴答滴答,人们每回被雨滴打中都会尖叫一声,一边拍打着头发和肩膀一边的四处。一滴雨钻进了他的脖颈里,然后马上渗进他的衣服里,像冰一样凉的感觉无情地躲避着他的皮肤。他全身的皮肤整个起了鸡皮疙瘩,好像马上将要绷开或被撕裂一样。咧着嘴巴,紧闭双眼嘴巴,鼻尖扭曲着,想开口,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比到达高速巴士始发站时距头班车还早,从出租车下来时,外面正轻飘着雪花。他走进候车厅买了一张去汉城的巴士票,然后缩在塑胶椅子上,像冻僵了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直到耳边广播说汽车已到,他仍然没有摆脱被雨水淋湿的感觉。然而像零下十七度的河水一样冰冻着的时间,只是一点一滴地、非常缓慢地在融化着。
写给姜兄。也许姜兄挂怀把我一个人留在旅店,所以自己也没睡好觉,一大早就回到我
的住地了吧?而后得知我清晨连包也没顾得上拿就出去了的事情,想着或许我留了纸条,于是再次环顾了房间。然后终于知道我没留下任何痕迹,于是心的一隅里感到一阵空虚。但是尽可能快一点把那份空虚之感清除掉吧。尽管我使姜兄感到了空虚,但这并不说明我自己疏忽了姜兄昨天一整天给予我的关怀。现在我想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事实上今天凌晨我本打算写一封书信之类的东西,但我根本没有办法写出来。我即将要写的是为我们所谈的话题做一个结论,哪怕是暂定性的。但是以我当时落魄的心情根本做不到这一点。这么看来,在某种意义上现在我所写的这封信说不定会成为一个句号。不过,现在我无法确认自己有没有勇气把这封信寄给姜兄。就算因为这封信到不了姜兄手中,于是姜兄始终无法清除与我相关的空虚感,使得我们之间留下什么误会之类,我也想以那样的方式掀开我们对话的一角。不过至少在这一瞬间我想郑重地与姜兄道个别。
再见。
三、正是引刻,以及此处
为了在一侧墙的正中钉一个钉子,张号角耳朵上别着一支半长的铅笔,长时间地用卷尺量长度、算距离,上下椅子,终于得以在白墙上点下一个黑点。他把椅子推向旁边,后退几步,盯了一会儿那个点。它有着仿佛小蚂蚁一样的身形,在他继续凝望着的当儿挤出视线的缝隙,开始细微地蠕动。眼看它要消失在墙里面,他拿着台子上的锤子与钉子走到墙前,把钉子准确地放在那小小的蚂蚁身上开始用锤子砸。片刻之后,他就把大大的水泥钉几乎全部钉进墙里了。他从椅子上下来,后退到比刚刚稍微再远一点的位置,以稍微颤动的目光望着
这次与刚才不一样顽强地与墙粘着在一起的,那泛着金属光泽的圆而光滑的表面。
正要拿起椅子转身的一瞬间,他停止了胳膊与腰部的动作,然后一本正经地趋近死死盯着那个钉着钉子的地方。刚才他用铅笔在墙上表示的那小点现在去了哪儿呢?他在那个点上用锤子钉入了钉子,弄出被铁灌满的一个窟窿,但是他没办法认为那个点已完全消失。那么那个点究竟跑到哪儿去了呢?还有,刚才从他手掌上的汗意,在钢与钢的碰撞中结结实实感受到的那种肌肉组织的紧张,包括些许的兴奋等等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难道它们也溶进那个点里一起消失了吗?还是成了为锐利的钉子尖的一部分呢?进一步想,他自己在那一瞬间,充其量也不过是宽大的水泥墙上似有似无的、用铅笔标出的一个小点而已,那么他的现在与这里又会去往哪里呢?不用想什么未来,每一瞬间的他去往哪里了呢?在如此空然地像密密麻麻的齿轮一样转动的世界上,他应该立足何处,在哪一块土地上垂下他的影子呢?能否哪怕是极其短暂地因自己的影子而感到某种清凉呢?
在毫无商量余地地萦绕于脑海的恐怖思绪的旋涡之中,他无力地垂下了手。锤子在击中他左膝盖的同时,脱离了手心的把握,划着半圆,沉甸甸地掉在了地上。他被那瞬间而集中的疼痛所纠缠所唤醒,毫不容易才从茫然中摆脱出来,多少真实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他以疼痛的膝盖活在当下,全身的支点偏向左膝凝固在那里。
凝固的瞬间也停止了它的步伐。他忘记了是什么原因让他以不甚乐意的心情坐上了朋友的车,打量着被灰尘弄得脏兮兮的车窗玻璃一角粘着的辣椒沫。锤子敲在膝盖上的疼痛就像钉子或锤子在薄而宽的铁板上留下的尖细回音和颤动一样,仍然控制着他浑身的神经系统。他坐在窗边,在驶向目的地的过程中,一直努力不再把头转向起初偶然发现的那块血红的辣椒面上。但是与他有意识的努力相反,无论何时只要他一转头,那块辣椒沫就在几乎要贴着他下巴的位置上。他拼命努力不去注意那块辣椒沫,但随着车身的颠簸身体的摇晃,连注意力也摇晃起来,以至他忍不住不断地转头去注视它。
来回转头的过程重复了一段时间,那个点的引力也随之越来越强大,在那单纯的动作中,他感到自己整个的存在一点一点地被吸进了那块红点中。他终于忍无可忍,用力转过身,开始用指甲刮玻璃上的红点。但是他的手指甲在玻璃上突然滑落,那个点纹丝不动,他没想到那个点其实粘在车窗玻璃的外面。确认这一事实的刹那间,他因感到无地自容而涨红了脸,别过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