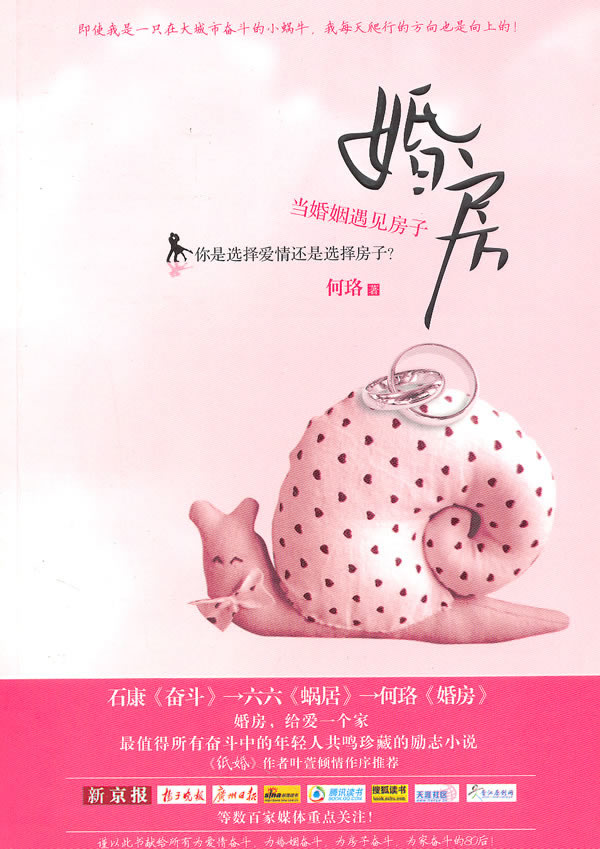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爱情-第5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太难了。非要把简单的事情解释得那么复杂,似乎只有这样才感觉更加正确和清楚,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因为自己是俗物吧?制造又密集又细微的无数皱纹,然后想把自己夹进它们中的某一个缝隙里,那些话语中就有着这种意图。当然,立体的空间里可隐藏的地方更多。对你来说,这个世界过于复杂而美妙,但是你周围的人们又过于单纯而明了,你在内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吧?”
“你的这些话中还掺杂着某种即使被我否定也无所谓的傲慢。看来你对我已形成了固定的判断,既然如此,还有什么理由继续这个话题呢?”
“你需要明白这个事实:你到处说自己是俗物,你在以这样的方式辩解自己的俗物性。我知道自己是俗物,但是这个世上哪有不是俗物的人呢?既然如此,诚实的告白我是不是就少一点俗物性呢?但是以那么单薄的辩解,俗物又怎能摆脱掉那俗物的壳呢?公然告白自己为俗物的人终究也是出于另一个层面的俗物根性。说不定那种做法会留下更严重的俗物的烙印,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半夜下得不是时候的残雪一块一块地留在田垄两侧的草丛中,明明被太阳照射着,却依然没被融化掉。看来草丛间那凹进去的小小空间能玄妙地保持着原来的温度。若那里面放进温的,那会一直保持是温的;若那里面放进凉的,则会一直保持是凉的。朴性稿从窗外收回视线,转向临座的张号角说道,
“那么,难道你以为暂时把自己诱避到这种地方来,就能从俗物根性中脱离出来吗?我们来这个地方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是对‘我在这样的地方,所以这一段时间别来找我’这种意思的逆向性的表现吗?”
但是张号角不理睬他的那些话,只顾凝视着前方。那种沉默持续了很久。静寂中朴性稿开始后悔随便跟他一起出来。静寂开始拷问朴性稿。首先他被张号角扒光了衣服,这种静寂很快紧接着又往他的身上轮流倒着冷水和热水。他的身体因烫伤而变成火红色,随即又冻得发青。皮肤因冻伤而发痒,因烫伤而不可言喻地刺痛。张号角从下面伸出手抓住他的阳具,像抻皮筋一样抻着。他尽管没被捆绑,却不能做任何抵抗。从两腿间伸出来的角木使下身发麻,让他感到似乎就要凝固成一座石膏像,肚子和脑子都变得空荡荡。除此之外,还有种种
他根本就不知晓的拷问,在他眼前仿佛用碧光闪闪的刀刃割肌肤一样,按部就班地依次进行着。在这一过程中,终于忍耐到极点的他,不得不开口道:
“是的,我承认因为我这类人的存在,最先是像你这样的人们、随即是这个世界将会毁灭掉这一事实。与其说是承认,不如说是我自己有着那样的预感。因此,可以说是我是人魔的杀伤性武器,而你是我的安全阀。你是我的安全阀”。
张号角回头看着他,彼此对视了良久,然后彼此一点一点地在对方眼前都变成了连在梦里都没见过的怪物。他们一边晒着从车窗洒进来的温暖的阳光,一边重复着不知何时会终结的蜕变。
二、向着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朴性稿在车站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才坐上从汉城开往外地的高速巴士。这是一次期待了很久的旅程,但奇怪的是他没有丝毫的感情波动,哪怕是情绪上的细微变化都感觉不到。他按照车票上的座号坐到窗边的座位,把椅背往后放到最大。自从巴士开动后一直淡漠地望着窗外的风景,一会儿,他就像陷入莫名的沉思一样暂时进入了梦乡,等到他醒来的时候,高速路周边已是夜幕沉沉,随着车快速移动而犹如被风荡漾的波纹一样缓缓摇曳着。
他不觉又重新进入了梦乡。过一会儿睁开眼睛往外望去,车窗不知不觉间已变成了一面漆黑的镜子。车窗玻璃白天的时候只能透视外面的风景,到天黑再也不能展现外面风光时,便摇身一变,成为折射车内景观的镜子。但它自己对此似乎心甘情愿,至多是无可奈何,只要窗外一出现灯光,便一无例外地敞开自己,再次回到似有似无而虚弱无比的本来面目。它就这样随时在玻璃窗和镜子间来回跳蹿,偶尔会同时兼具有这两者。
朴性稿凝望着那既不是玻璃又不是镜子,却完美地分隔着外面的黑暗与他的车窗,突然有了一种怪异的想法:白天干净而透明的玻璃,每到夜晚就变成了不透明以至漆黑的怪物。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但仍然挪动上半身,让两只眼睛更加贴近车窗玻璃。这么一来,他眼前不知是车窗里还是车窗外的漠漠视野里,有什么东西一堆一堆地蹲在一起,或不时缓缓挪动着身子,到处走来走去。这些东西无以为名,只能称之为怪物。但是,仔细观看着这副情景的他并没有受到惊吓或感到突然。
说来这世界上的怪物何止于此呢。连星星都被遮住的漆黑的夜空下,海面翻腾着沥青色的光。一阵风控制不住自己的速度,急匆匆地划着螺旋吹过。在有些怪异的气氛中,终于从海的深处开始有一只不知其真面目的怪兽,流着掺有海水的口涎,缓缓浮出水面。在那样的场景中,那个怪兽的登场能不能说是一个自然而和谐的景观?不仅如此,人们一天要好几次在浴室的镜子里照自己的脸,每回都看到自己蹲在里面的样子方才安心。某一天,那镜子也会像这车窗一样改变自己吗?在大家都沉睡着的时间,从镜子中渗出与人们长得一模一样的透明幻影,布满漆黑的屋子和走廊的角角落落。细细琢磨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人类对这个世界,所知的仍然是屈指可数,那又何必对擦过各自想象边缘的怪物们的存在大惊小怪呢?
朴性稿预感到目的地将近,于是提起上半身坐直了。外面仍然是漆黑的夜晚,他看着那些从黑暗中透出来的无数大大小小的怪物顺着车体爬上来掩盖车窗的样子,重新闭上了眼睛。刻薄一点说,白天过于世俗化;一到白天就看不到的不知原形的怪物们,非要说出来不可的话,其实就是习惯团、意识形态团等等,它们隐藏在人们晕眩的眼睛中,凶神恶煞地到处乱蹦。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认为白天才是最适合于我们的时间呢?就因为些许的舒适吗?但那仅仅是从不过数世纪前再也不惧怕其他禽兽时才开始滋长的我们的傲慢而已。实际上,一到白天我们就成了为其他怪物们的奴隶,充其量也就是模仿着那些怪物们打发时间而已。在事先就已铺好的草盖上,我们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自由。
那么就让我们关注深夜发生的个人之间的事情吧。当然,夜里也会有所谓的习惯啊、理念啊之类的东西,像野狗一样横行霸道着,不过我们还是宁可在夜里,不是吗?在那种黑暗中,首先占据我们的应该是对生命的恐惧感,因此使人变得无限谦恭;而那个时候,我们内面的人性本源,即自然本性也会占据我们。与其相信通过光就能用眼睛看得到,不如因为什么都确认不了,所以始终有必要重新展开斗争,这才不愧为朴素的人吧?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就让我们用全然不一样的方式进行提问吧。对于真正想获得自由的我们而言,白昼中黑夜的位置在哪里?另一方面,黑夜中白昼的位置究竟又在哪里呢?普照我们的生命,又给我们的生命垂降夜幕的白天和黑夜各自又是什么呢?或许黑夜是白昼的影子,白昼是黑夜的镜子?还有,光是否有把人定义为黑夜的影子的属性呢?
巴士还没到达终点站,朴性稿便在市郊下了车。那个地方对他而言并非是很生疏的地方,但他还是辨不清方向。他因不能准点到达而使劲安抚了一阵焦虑的心情,然后顺着路走了一会儿,随即下到车道上,站在那儿环顾四周,确认某一条街通向市中心后,向着仿佛为了团体获胜而赛跑似的出租车挥了挥手。与汉城一样,这个地方大都市也是很难拦到出租车的。他向着那些在自己面前随停随走的出租车大声喊着目的地。突然,他对自己正做着的行为感到无法理解,刹那间不知不觉停住了动作,垂下两只手迎面吹着凉风呆立在那里。往哪个方向走,都无法轻易摆脱陌生的感觉。街头的黑暗变得越来越浓,杀气腾腾的灯光到处闪耀,仿佛在尖叫。在这样的混乱中,他为了拦车而左蹦右跳地瞎喊着。单单这一点,能不说是疯疯癫癫的行为吗?
在那一瞬间,在手指尖发麻、头脑一片空白的茫然状态中,他被一小片思绪——不知是记忆还是联想、或许只是单纯的想象而已——抓住了脖颈。他又清楚地听到了从自己内心深处抛出来的某个声音,而每回他都能对此做出正确的回答:
“是,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还是记忆犹新,越想忘掉就越难以忘掉。那次,训练所的门一在身后关上,所有的人都在察言观色,把‘如何才能少吃苦,能更舒服地结束那里的生活’这样的想法,用表情、身体语言和行动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但我不想跟他们一样,也只能不一样,因此我决心不管想出什么办法,也要在转业之前,在那个训练所结束我的军队生活。只有那样才和其他家伙不一样。为了达到那个目的,体魄强壮的我从一开始能做的事情就是装疯卖傻。古往今来,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选择装疯手段的朋友为数不少,而我
也在这样的情形下,以好端端的精神状态加入了那个行列。不管别人有没有看破我的意图,只要有好的结果,他们会不会耻笑对我而言当然是无所谓的事情。”
“不,也不完全是那样。从迄今你给身边人的印象,或者是从你在那个别人都忙于察言观色的荒漠无比的地方,居然自发地装疯卖傻这一事实来推测,你的内在中分明还存在着与别人截然不同的非正常的一面。从高中时代起就是如此:你根本无法忍受学校的规章制度。你到底过得有多艰难,在旁边关注着你的我比谁都清楚,或许比作为当事人的你自己还要清楚。动不动就和朋友打架,因此鼻青脸肿是经常有的事。你应该没有忘记老师和同学都把你当成废物的往事吧?再回顾一下,当时困厄着你的无穷无尽的穷困。你不但没有一早上学去看轮流传递的报纸,反而为了偷炼炭而常常迟到。当然,我并非因此而断定你一开始就是疯子;我的意思是,与其主张自己疯还是没疯,还不如往‘疯还是没疯的区别实际上是多么可笑的事情’这个方向推进你的话和想法。”
“那是什么无聊的废话?连你也在让我分不清我自己到底疯了还是没疯,听明白了吗?本来我最近脑子里就一片混乱。不过,不管实际上如何,也不管你听不听得进去,我也要讲完我起头的话。我在那里开始了装疯卖傻的生活,但是,如果行事稍一卤莽,就会被别人看破我的谋算,从而使我偏离我的目标。所以要特别地处心积虑。我冥思苦想了半天,最终打算这样作战,就是尽可能做出与其他人截然相反的行为。同伴们嫌弃或想躲避的事情,我就积极地去做;而对他们争先恐后要去做的事情,则表现出不冷不热的反应。当然,我的战略获得了短期效果,不仅是训练所的同伴们,就连教官和助教们都开始关注我。他们开始不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