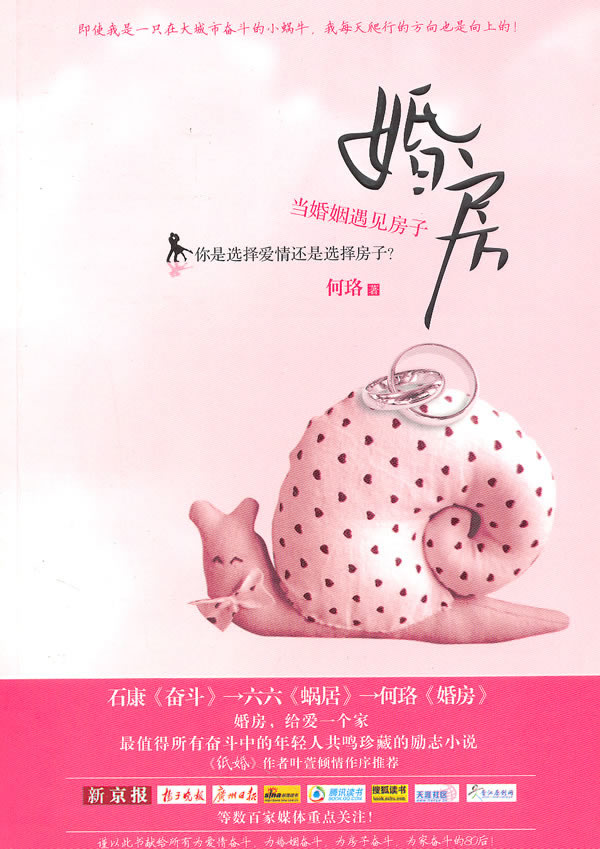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爱情-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我眼里,那边我的一位朋友对我无力的微笑,像一件遥远的往事依稀可见。必须摆脱时光的理论。我不能再上他们——用时光伪装的家伙们的圈套了,尽管最后只留下空洞的仇恨。我的手蓦地从那渺远的过去伸将过来,向现今的我举起了酒杯。经过多次徒劳的手势,我才接过了那来自过去的酒杯。杯中的肉桂色液体将流向何处?大地坚硬如铁,滴水不漏;水在地上积存一时之后,被蒸发到弥漫潮气的天空中,何况是自有挥发力的酒精呢?来自过去迷途的亡灵在跳舞。那么,身在现实中的我就确定无疑的吗?我怎能这般自信?若果过去通向现在,那么这儿有没有未来呢?有的话在哪里?烛泪流满了烛台。如果我用将来式记叙这烛台的话,未来是否就在其中?如果未来不在此,或者我不曾见到,那么我必须记忆出一个未来来。这是势所难免的事。而势所难免跟未来的概念颇为谐合,我无可奈何地记忆未来。熄灭的蜡烛上,飘起一缕烟,散发出一股浓浓的刺鼻味。
我们筋疲力尽地躺在结束战斗的战场上。酒液从一个伏在桌面上的朋友身上的毛孔中流出,弄湿了一地。它渐渐流满桌面,跑到边角,望着下面估量高度,等到更多援军到来之后,就猛地纵身跳下。屋内只听到有规则的滴水声,静如一潭死水。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伪装、欺瞒和记忆了。在此,我该当何人何物呢?是当那挂在墙上的画中裸孩,还是泡在桌面酒水中挣扎的烧剩的半根火柴?抑或是化作杀气腾腾的目光,扫向对面醉意正浓的友人?若变成一只室内拖鞋又如何?当然,变成那女人高耸在低领之上的白嫩的肩膀也未尝不可,又有
谁会反对我成为脑中像蜂群嗡嗡作响的醉意。如果我变成我那友人——他正反抄邻人的手按倒桌面上——额前的一绺头发,又会怎么样呢?然而,我已无可记忆,也成不了任何东西。何况我该离席了。当我起身的一刹那,突如其来的眩晕,以其利齿猛咬我的颈背。对了,我怎么没想到变成躲在身后的眩晕,带着被眩晕焚毁的肉体,像酒精气化飘然而逝呢?哪怕重新撞回人造大理石地面上,哪怕成为烧得滚烫的煎盘上的鸡蛋,而且被人永远遗忘,我也将在所不辞。
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意识到被盯了梢,但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生活并没因此发生什么变化。当然,跟我们原先的相互默契相比,我们的行动多少有些不协调、散漫和山高水低。我们非常清楚:这是盯梢者所致。为了不留尾巴,我们的行为自然变得有些慌乱、古怪。不过,也没到丢人现眼的地步。我们依旧谈论着方便面的滋味,调门忽高忽低。我们之中的两个朋友一如既往,每天一大早便起床面壁打坐。按他们的话来说,他们正在用脑顶的百回血把气送至全身。然而,这些努力安抚自己、不让自己无端恐慌或浮躁的氛围,逐渐冷却了下来,因为我们之中有人相信:跟踪者已经抓住了我们的把柄,要揪我们,令我们感到沮丧不已。
当我们各自打发白天的时光,晚上与世隔离、聚集一堂时,我们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快活。我们无端闻到各自身上发出的甲酚或阿摩尼亚的气味,直捂鼻子,似乎盯梢者从冥冥中渐渐显出了自己的身影。但如同廉价推理小说,我们谁也没感知到他的存在,这自然引发了集体的神经过敏,有几个人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跟踪者幽灵般尾随我们、监视我们,叫我们感到毛骨悚然。有几个人坦言道:跟踪者像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机。他们也明白:他们得的正是遭人侦察的典型的被害意识症。但问题是他们对此束手无策,而且他们就是我们全体。我们对典型都神经过敏。所以,我们经常恍恍惚惚地听到铁蝈蝈、铁知了或铁蟋蟀的鸣叫声。当然,这是我们想象的监视器镜头移动时发出的声音。明知这是幻听也于事无补。不顾再三的失败,我们仍翻箱倒柜,寻找铁蝈蝈、铁知了和铁蟋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再唾沫四溅,拿不痛不痒的凡人世事打发夜晚的时光;那两个气贯百回血的朋友,也中止了每天清晨的修练;我们回家的时间也时早时晚,不再一致了。一句话,我们的与世隔绝的状况,陷入了决定性的危机之中。
尽管如此,跟踪者仍在暗中有效地监视着我们。晚上我们聚在一起,他也在门外通宵徘徊不去。盯梢的可能不止一个,很可能跟我们一样人数众多,而这又无法确定,所以大家不必是耶非耶地浪费睡觉的时间。有一天晚上,大家正在默默地吃晚饭,突然几乎同时意识到,我们都是一台台监视器,正在相互监视偷拍,所以先是相互睁大眼睛张望,而后放下碗筷离开了。虽说大家避免相互对视,却离不开那块小地方。临睡,我们不知道把脸搁在哪儿才是,真是羞死人了。后来,我们的神经过敏益发严重,会随时随地条件反射式地回头张望,以便确认有无盯梢或监视器,明知纯属子虚乌有,却仍然眯着双眼寻视着。我们虽然常备不懈,但监视器的镜头和跟踪者的眼睛仍随处可见,哪怕是在洗手间,它们也会透过光滑的白砖,用特写和变焦镜拍下我们的生殖器,使我们战栗不已。我们不仅被隔离,而且被监视着。怪不得有人自弃道:盯梢和我们相互的监督,把这儿变成了一座大监狱。其中,老人是无期囚犯,而早死的成人或夭折的少年则是有期徒刑者。大家听罢,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了。何况当时年龄各异的我们,正想着各自的存在理由及其对方的存在价值而变得心绪低劣。照那位朋友的说法,我们是自我调整刑量的囚犯,只要想溜,即可走人。我们拥有对自身的裁定权。然而长寿属于多欲,活得越久,他的罪恶就越深重。那老头犯了什么大罪迄今还关在此地呢?我们不分老幼青壮,不得不长时间对照自己,细细咀嚼个中三昧。
终于,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大家下班聚在一起,正忙着准备晚饭,突然从四面的门窗涌进一股股白色气体。大家惊慌地关紧门窗,拉上窗帘;但我们租赁的房屋过于陈旧,孔隙不少,屋里很快烟雾弥漫。富有刺激性的气体直冲我们的鼻子。我们都吓呆了。听说,在世界某地,不也发生过把人关起来,排放汽车废气,把人折磨死的事吗?念及此,我们全体狂乱起来,大叫着跳下楼梯,向外冲去。所有通道都被烟雾紧裹着,我们用手巾堵着嘴,边咳边摸索着楼梯。终于,监视器启动了攻击程序,或者说跟踪者蓦地原形毕露。我们心里很清楚这一天终将到来,那么为什么袖手旁观而终遭此劫呢?如今回想起来这想法很自然,可当时却是我们的错觉。因建筑物周围有些草地,管理员就撒了大量消毒剂。终于在一个无风的日子,消毒剂越过墙头,把屋子和通道灌得满满的。待到真相大白,我们感到虚脱,啼笑皆非,不禁对自己感到恼火:难道我们的被害意识竟到了这般地步了吗?我们禁不住摇头,有的还捶胸嗟叹。大家都真切地意识到,一种悲观之兆像那消毒剂,侵入了我们的肌体和五脏六腑之中。很快,这种可悲的预感变成了现实。从此,我们身上的甲酚气味更浓,心情更黯淡了。同时,监视器和跟踪者的眼睛也不懈怠,继续紧紧地掐住我们的脖子。总有一天,我们会再次在他们假像或真实的攻击面前落荒而逃,暴露出我们极其虚弱的面目。我们最怕的,正是我们不堪一击这一点。总之,我们将越发变得恐慌,最终在莫须有的监视器或隐蔽的眼睛面前低头认输,或者再次陷入集体歇斯底里之中。
于是,我们终于决定解散,不再聚在一起。一旦作出决定,大家的心情也轻松多了。但老实说,这等于宣告投降,我们心中自然不是滋味。因此,对我们的最终抉择,有人作了这样的自嘲:有人曾说,我们是自觉服刑的囚徒。那么,我们现在决定解散,就等于砸牢越狱。这话虽说得有些幼稚,但大家一时肃然,低下头或遥望天际。然而,先有我们相聚一处,而后才不觉间有了监视器,才有了四处张望的跟踪之眼。这多少是真实的。正由于我们聚在一起,才会有监狱;正由于我们想守护什么,才会陷入它的陷阱;正由于我们想主张什么,才会撞上暗礁。我们指望什么,什么就成了陷阱。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现今自毁牢狱,就是另一个自掘的陷阱。我们将全力解散,为了我们自己,为了保护自己,为了最终相聚一起守卫自己,也为了伸张我们自己。
他开始盯梢纯属偶然。他没想到盯梢是件快事。黄昏时分,他干完一天的活儿,便留意一切映入他眼帘的东西,定下当天跟踪的对象。但严格地说,他也不随意选定。首先,他坚决反对自己这么想。按他的想法,不是他任意找人暗中尾随,而是有人需要他去悄悄跟踪。换言之,一到晚上,他便化成一滩水,流到洞穴或凹地里,在那儿静静地呆一阵子,随后重又悄悄回到原处。在一般情况下,他主要跟踪眼望脚尖走路的人、走路双肩晃得厉害的人和甩开双臂、不时撞行人的人。他们明明知道他在跟踪,却装作若无其事,甚至为了引起他的好奇心,故意露出他们的缺点或破绽。于是,他更频繁地跟踪他们。他穿过阴影,拨开人群,通过橱窗的反光观察路对面,忙于拦车追赶,或躲在暗中屏息凝神,无端地看表、抽烟,无缘无故地向行人讨话说。
有一次,他跟踪过一个中年清道夫。在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这位清道夫把地扫得尘土飞扬。这是他第一次盯梢。他隔着一定距离,默默跟随其后,待到清道夫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坐一个多小时市内巴士回到又矮又暗的家,躺在满是灰尘的床上,沉入尘土弥漫的梦乡后,他才浑身疲软地在凌晨时分回到家。从此,他便有了跟踪别人的习惯。
他跟踪过许多各式男女。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长着马脸的青年。他什么也没想,便跟随其后。那青年的脸看来与马无异,而且他的步伐也使他联想起马的动作来。马脸青年住在郊区二层住宅的楼上,想必是他的工作室兼卧室。他跟着青年进了楼内,站在门外昏暗的楼道上,把耳朵贴在人造板上倾听。屋里传来青年不断走动的声音,想来他正面带复杂而焦虑的表情,在屋内来回走着。他一直反复嘟哝一句话:把时间绷紧,像橡皮筋,这才是惟一活下去的办法。对,对。年轻人干枯的声音相当凄惨。他听了许久,才离开了那儿。他回到家累极了,却睡不着,走到居室,模仿那青年的嘟哝,徘徊在合塑地板上。值此,他对自己的盯梢行为产生了疑惑和畏惧心理,但已难以解脱,况且尚无打消它的念头。
他还曾跟踪过一个面带病色的年轻女子。跟踪多时之后,她进了一家综合医院。过了许久,她出来了,脖子上绕了厚厚一层绷带,坐上一辆等她的轿车。他赶紧跑上前,隔着车窗问她得了什么病?或许她喉痛回不了话,或者对这无端提问摸不着头脑,光睁大眼睛瞧着他。司机朝后张望,她用手势告诉他开车,于是,车子抛开他的手开走了。她大概做了扁桃腺切除手术。他的跟踪也就告一个段落。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所以等她走了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