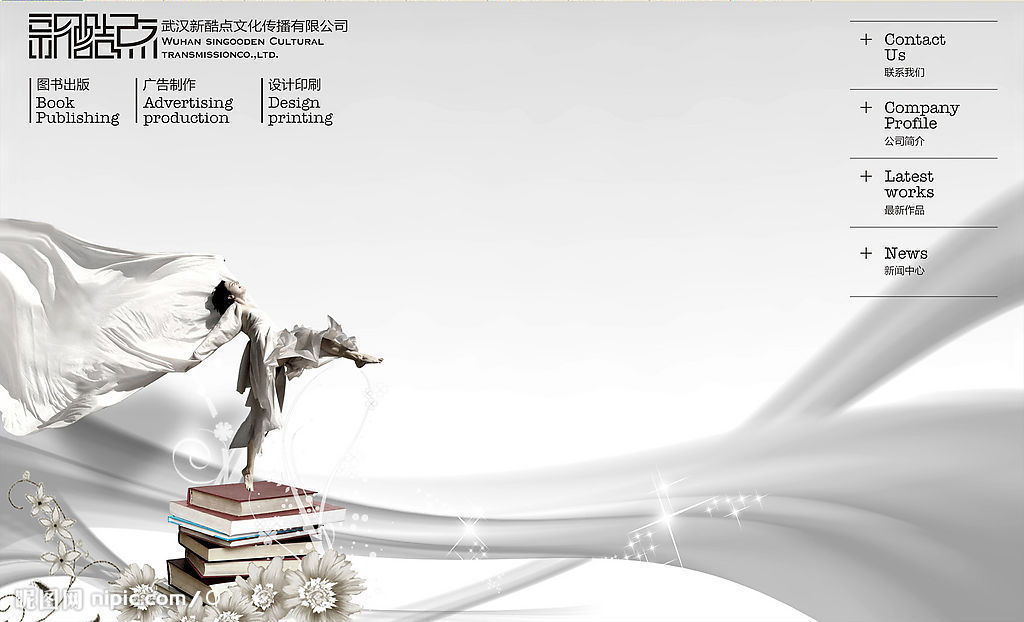基,督山伯,爵 作者:大仲马-第2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说下去!”审判长说。
“当然罗,”贝尼代托继续说,“抚养我的那些人都很爱我,我本来可以和那些人过很快乐的生活,但我那邪恶的本性超过了我继母灌输在我心里的美德。我愈变愈坏,直到犯罪。有一天,当我在诅咒上帝把我造得这样恶劣,给我注定这样一个不幸命运的时候,我的继父对我说:‘不要亵渎神灵,倒霉的孩子!因为上帝在赐你生命的时候并无恶意。罪孽是你父亲造成的,他连累你生遭孽报,死入地狱。’从那以后,我不再诅咒上帝,而是诅咒我的父亲。因为这个我才说了那些让你们遣责的话,为了这,我才使法庭上充满了恐怖。如果这一番话加重了我的罪名,那么请惩罚我;如果你们相信,自从我落地的那天起,我的命运就悲惨、痛苦和伤心,那么请宽恕我。”
“但你的母亲呢?”审判长问道。
“我的母亲以为我死了,她是无罪的。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也不想知道。”
正当那时曾经昏厥过一次的那个贵妇人发出一声尖锐的喊叫,接着是一阵啜泣,那个贵妇人现在陷入一种剧烈的歇斯底里状态了。当他被扶出法庭的时候,遮住她的面孔的那张厚面纱掉了下来,腾格拉尔夫人的真面目露出来了。维尔福虽然精神恍惚,耳聋脑胀,却还是认出了她,他站了起来。
“证据!证据呢!”审判长说,“要记得:这种话是必须要有最清楚的证据来证实的。”
“证据?”贝尼代托大笑着说,“您要证据吗?”
“是的。”
“嗯,那么,先请先看看维尔福先生,然后再来向我要证据。”
每一个人都转过去看检察官,检察官无法忍受那么多人的目光只盯在他一个人身上。他踉踉跄跄地走到法庭中心,头发散乱,脸上布满被指甲抓出的血痕。全场响起一阵持续颇久的低语声。
“父亲,”贝尼代托说,“他们问我要证据。你希望我给他们吗。”
“不,不,”维尔福先生用一种嘶哑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不,不必了!”
“怎么不必呢?”审判长喊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我无法和这种落到我身上来的致命的重压抗争,诸位。——我是落到一个复仇之神的手里了!无须证据,这个年轻人说的话都是真的。”
全场被一种象预示某种恶劣的自然现象那样阴森凄惨的沉寂弥漫着,大家都惊慌地寒颤着。
“什么!维尔福先生,”审判长喊道,“你难道昏了头吗?什么!你的理智还在吗?你的头脑显然是被一个奇特、可怕、意想不到的污蔑弄糊涂了。来,恢复你的理智吧。”
检察官低下头,他的牙齿象一个大发寒热的人那样格格地打抖,可是他的脸色却象死人一般毫无血色。
“我没有丧失理智,阁下,”他说,“你可以看得出:失常的只是我的肉体。那个年轻人所指控我的罪,我全部承认,从现在起,我悉听下任检察官对我的处置。”
当他用一种嘶哑窒息的声音说完这几句话后,他踉踉跄跄地向门口走去,一个法警机械地打开了那扇门。全场的人都因吃惊而哑口无言,这次开庭审判使半月来轰动巴黎社会的那一连串可怕的事情达到了最高峰。
“噢,”波尚说,“现在谁会说这幕戏演得不自然?”
“噢!”夏多·勒诺说,“我情愿象马尔塞夫先生那样用手枪结束他的生命,那总比这场灾祸来得舒服点。”
“那么他犯了杀人罪了。”波尚说。
“以前我还想娶他的女儿呢!”德布雷说,“幸亏她死了,可怜的姑娘!”
“诸位,审问暂停,”审判长说,“本案延期到下次开庭办理。案情当另委法官重新审查。”
至于安德烈,他仍然很平静,而且比以前更让人感兴趣了,他在法警的护送下离开法庭,法警们也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了一些敬意。
“嗯,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样,我的好汉?”德布雷问那副警长,并把一块金路易塞到他的手里。
“可能酌情减刑。”他回答。
(第一一○章完)
第一一一章 抵罪
维尔福先生看见稠密的人群在他的前面闪开着一条路。
极度的惨痛会使别人产生一种敬畏,即使在历史中最不幸的时期,群众第一个反应总是对一场大难中的受苦者表示同情。
有许多人会在一场动乱中被杀死,但罪犯在接受审判时,却极少受到侮辱。所以维尔福安全地从法院里的旁听者和军警面前走过。他虽然已认罪,有他的悲哀作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是用理智来判断,而是凭本能行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最伟大的人就是那种最富有感情和最自然的人。大家把他们的表情当作一种完美的语言,而且有理由以此为满足,尤其是当那种语言符合实际情况的时候。维尔福离开法院时的那种恍惚迷离的状态是难于形容的。一种极度的亢奋,每一条神经都紧张,每一条血管都鼓起来,他身体的每一部分似乎都受着痛苦的宰割,这使他的痛苦增加了一千倍。他凭着习惯走出法庭,他抛开他法官的长袍,——并不是因为理应如此,而是因为他的肩膀不胜重压,象是披着一件饱含痛苦的尼苏斯的衬衫一样[尼苏斯是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因诱拐大力士赫克里斯之妻被赫克里斯以毒箭射死。赫之妻遵尼苏斯的遗言,把丈夫的衬衣用这怪物的血浸过,赫克里斯穿上后因此中毒,苦恼不堪,卒致自杀。——译注]。他踉踉跄跄地走到道宾路,看见他的马车,停在那里,亲自打开车门,摇醒那瞌睡的车夫,然后摔倒在车座上,停在那里,他向圣·奥诺路指了一指,马车便开始行驶了。他这场灾祸好象全部重量似乎都压在他的头上。那种重量把他压垮了。他并没有看到后果,也没有考虑,他只能直觉地感到它们的重压。他不能象一个惯于杀人的冷酷的凶手那样理智地分析他的处境。他灵魂的深处想到了上帝,——“上帝呀!”他呆呆地说,其实他并不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上帝呀!上帝呀!”在这将临的灾祸后面,他看见上帝。马车急速地行驶着。在车垫上不停地晃动着的维尔福觉察背后有一样东西顶住他。他伸手去拿开那样东西,那原来是维尔福夫人在车子里的一把扇子。这把扇子象黑暗中的闪电那样唤起他的回忆,——他想起了他的妻子。
“噢!”他喊道,象是一块烧红的铁在烙他的心一样。在过去这一小时内,他只想到他自己的罪恶。现在,另一个可怕的东西突然呈现在头脑里。他的妻子!他曾以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的身份对待她,他曾宣判她死刑有自己的“明心”方法才是简易可行的。,而她,受着悔恨恐怖的煎熬,受着他义正词严的雄辩所激起的羞耻心的煎熬。
她,一个无力抵抗法律的可怜的弱女子,——她这时也许正在那儿准备死!自从她被宣判有罪以来,已过去一个钟头了。
在这个时候,她无疑地正在回忆她所犯的种种罪行,她也许正在要求饶恕她的罪行,或许她在写信给他丈夫,求她那道德高尚的丈夫饶恕她,维尔福又惨痛和绝望地呻吟了一声。
“啊!”他叹道,“那个女人只是因为跟我结合才会变成罪犯!我身上带着犯罪的细菌,她只是受了传染,象传染到伤寒、霍乱和瘟疫一样!可是,我却惩罚她!我竟敢对她说:‘忏悔吧在自己的发展中不断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起来。,死吧!’噢,不!不!她可以活下去。她可以跟我。我们可以逃走,离开法国,逃到世界的尽头。我对她提到断头台!万能的上帝!我怎么竟敢对她说那句话!噢,断头台也在等着我呢!是的,我们将远走高飞,我将向她承认一切,我将天天告诉她,我也犯罪!噢,真是老虎和赤练蛇的结合!噢,真配做我的妻子!她一定不能死,我的耻辱也许会减轻她的内疚。”于是维尔福猛力打开车厢前面的窗口。“快点!快点!”
他喊道,他喊叫时的口吻使那车夫感到象触了电一样。马被赶得惊恐万分,飞一般地跑回家去。
“是的,是的,”在途中,维尔福反复念叨,“是的,那个女人不能死,应该让她忏悔,抚养我的儿子,我那可怜的孩子,在我不幸的家里,除了那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老人以外,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她爱这孩子,她是为他才变成一个罪人的。一个母亲只要还爱她的孩子,她的心就不会坏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她会忏悔的。谁都不会知道她犯过罪,那些罪恶是在我的家里发生的,虽然现在大家已经怀疑,但过些时候就会忘记,如果还有仇人记得,唉,上帝来惩罚我吧!我再多加两三重罪也没什么关系?我的妻子可以带着孩子和珠宝逃走。她可以活下去,也许还可以活得很幸福,因为她把爱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我的心就可以好受一些了。”于是检察官觉得他的呼吸也比较畅通了。
马车在宅邸院子里停住。维尔福从车子里出来,他看出仆人们都很惊奇他回来得这样早。除此之外他在他们的脸上再看不出别的表情。没有人跟他说话,象往常一样他们站在一边让他过去。当他经过诺瓦蒂埃先生房间时,他从那半开着的门里看见了两个人影,但他不想知道是谁在拜访他的父亲行。由于他的另一创始人、德国哲学家阿芬那留斯把对经验,他匆匆地继续向前走。
“啊,没事”,当他走上通向妻子房间去的楼梯时,他说,“没事一切都是老样子。”他随手关拢楼梯口的门。“不能让人来打扰我们,”他想,“我必须毫不顾忌地告诉她,在她面前认罪,把一切都告诉她”。他走到门口,握住那水晶门柄,门却自行打开了。“门没关!”他自言自语地说,“很好。”他走进爱德华睡觉的那个小房间,孩子白天到学校去上学,晚上和母亲住在一起。他忙向房间里看了看。“不在这儿,”他说,“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他冲到门口,门关着。他站在那儿浑身打哆嗦。“爱萝绮丝!”他喊道。他好象听到家具移动的声音。“爱萝绮丝!”他再喊。
“是谁?”他要找的女人问道。他觉得那个声音比往常微弱得多。
“开门!”维尔福喊道,“开门,是我。”
不管他的怎样请求,不管他的口气让人听上去多么痛苦,门却依旧关着。维尔福一脚把门踹开。在门口里面,维尔福夫人直挺挺地站着,她的脸色苍白,五官收缩。恐怖地望着他。“爱萝绮丝!爱萝绮丝!”他说,“你怎么啦?说呀!”
那年轻女子向他伸出一只僵硬而苍白的手。我按你的要求做了,阁下!”她声音嘶哑,喉咙好象随时都可能被撕裂。
“你还要怎样呢?”说着她摔倒在地板上。
维尔福奔过去抓住她的手,痉挛的那只手里握着一只金盖子的水晶瓶。维尔福夫人自杀了。维尔福吓疯了,他退回到门口,两眼盯住那尸体。“我的儿子呢!”他突然喊道,“我的儿子在哪儿?爱德华!爱德华!”他冲出房间,疯狂地喊着,“爱德华!爱德华!”他的声音不胜悲恸,仆人们听到喊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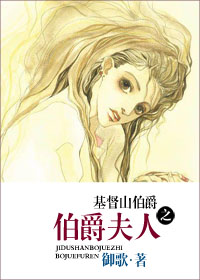

![[基督山伯爵]监禁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66/6689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