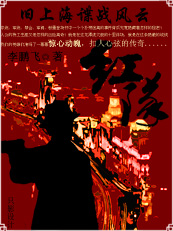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第18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汤阿英想起上海刚解放那一年,奶奶整天唠唠叨叨个不完,怨天尤人脾气不好,看啥都不顺眼,她便说:
“现在日子好不好?”
“这个日子还不好?”巧珠奶奶认为汤阿英常常往外边跑,看的好物事多了,眼光越来越大了,住进这样房子还问好不好,用着责备的口吻对她说,“你还想过啥好日子?人心不足蛇吞象,我们能在这里住上一辈子,就不错啦。”
汤阿英听出她话里的意思,没有正面回答她的话,却说:
“你从前不是说,谁来了,还不是一样做工,工钿还是那些,日子哪能会好呢?”
“你的记性倒真好!”巧珠奶奶望了汤阿英一眼。
“奶奶忘记了吗?”
“过去的事,提他做啥?”
“怕你忘哪!”
“哼,看你嘴利的!”巧珠奶奶不服输,但也不好赖账,想了想,说,“那辰光,我不了解共产党的事,你们为啥不给我说。你们呐,只晓得回家睡觉,起来上班,外边世道变了也不告诉我。幸亏我有我的老伴,余大妈常到我家里来谈谈,我到余大妈家去,碰上余静,她也常给我讲这讲那。我晓得共产党是穷人党,是给我们穷人办事体的。共产党一来,世道就变啦,穷人有面子了,做工也光荣啦,钞票值钱哪,日子好过啦。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们还不是住一辈子草棚棚,谁会给我们盖这样的好房子?连电灯都装好了,想的真周到。”
她指着吊在屋子当中的电灯,满意地笑了。张学海听了她这一番话,也笑了,对汤阿英说:
“娘晓得的事体可不少哩,过去,我们和娘谈的也实在太少了。”
没等汤阿英答话,余静和秦妈妈走了进来。余静朝新房上下左右看了一下,对巧珠奶奶说:
“都安顿好了吗?”
“大致安顿好了。住在这样好的房子里,今后刮风下雨再也不用愁了。”巧珠奶奶眯起眼睛满意地望了一下崭新的房子,新粉的白墙,新油的绿窗,新装的电灯,照得满屋亮堂堂的喜洋洋的。她闻着油漆和石灰的气味,心里十心喜悦,感激地说,“谢谢你,余静同志,分配给我们这样的好房子。”
“不用谢我,这是组织上分配的。”余静说。
“也是经过你的手分配的。”
“也不是,是大家讨论评选的。”
“你总是这样客气。”
“不是我客气,事实是这样的。”余静望着新房子,想起过去的穷苦生活和革命斗争,回忆地说,“讲起来,全靠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斗争,才有今天幸福的生活。”
“我们有今天这样好的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的血汗换来的。”秦妈妈补充说。
“革命先烈?”巧珠奶奶愣着两只眼睛,困惑不解,工人新村和革命先烈有啥关系呢?
余静点点头,从她深蓝布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打开看了一看那些熟悉的尊敬的名字,激动地说:
“秦妈妈说的对!不说旁人,就说我们工人吧,邓中夏,刘华,顾正红他们领导工人斗争,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不知多少人,才换来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了,工人当家做主了,才盖这些工人新邨来。要不解放,我们工人还不是住一辈子的草棚棚吗?”
汤阿英以崇敬的心情听余静提到那些革命先烈的名字,顾正红的英勇事迹她曾经听秦妈妈讲过,邓中夏和刘华的斗争历史就不大清楚了。她赞成余静和秦妈妈的意见:
“没有过去革命斗争,就没有现在的幸福生活。”“阿英这两句话说的好!”余静对巧珠奶奶说,“我们要常常想想过去的生活。”
汤阿英把刚才同巧珠奶奶谈的话告诉了余静和秦妈妈。
秦妈妈指着余静手里的笔记本说:
“你们晓得她这个本本里记的是啥?”
“首长报告记录,”张学海说,“厂里工会的大事……”“这些都有。”秦妈妈说,“头一两页特别重要,那上面抄了许许多多的革命烈士的名字,刚才讲的邓中夏,刘华,顾正红都有,这里面还有袁国强烈士的名字哩。她经常看这些名字。有辰光,她也拿给我看。一看到这些烈士的名字,我们心里痛得像刀剜的一样。余静说,要让这些烈士的名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他们流血牺牲,为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实现革命的理想,为了共产主义,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他们死了,我们活着的人,就应该实现他们的遗志。我一想到余静同志说的这些,浑身都有劲道了!”
“你把我的秘密暴露了。”余静看了秦妈妈一眼。她抄下这些革命先烈的名字,特别是袁国强的名字,从来没有和旁人提起,只是有一次告诉了秦妈妈。
“要阿英他们给你保密好了。”
“我们一定保密!”汤阿英说。
“这也不是秘密。”余静的脸上露出两个笑涡,又打开笔记本,念道,“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她接着说,“我对这一段话体会特别深。革命每一次的胜利都不是轻易得来的,经过无数次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失败;又继续斗争,最后取得胜利。牺牲了无数先烈的鲜血才换来今天的胜利。革命先烈为了革命,不惜流血牺牲,我们活着的人,应该把自己的力量献给革命事业。”
汤阿英听了余静这一番富有革命热情的激动人心的话,十分感动,使她想起了过去阴暗的生活,过去阴暗的农村,过去阴暗的中国,现在住进这么好的漕阳新村,越发觉得可贵了,胜利的果实得来不易啊!她感动得眼睛有点红润了,忍住盈眶的热泪说:
“我们现在生活比过去好了,不能忘记过去,也不能忘记还有很多人住在草棚棚里啊!”
“对!中国工人阶级胜利了,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人、农民和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哩!”汤阿英的话触动了余静内心深处的丰富感情,忍不住从深蓝布上衣口袋里,又掏出一个本本,但不是笔记本,而是一本世界地图。她严肃而又激动地说,“这是国强的遗物。全国解放以前,他特别关心报上的消息,哪个城市解放了,他就在中国地图上做一个记号,大片大片城市解放了,地图上的记号越来越多了。他说,等到上海解放,他要把上海和整个中国地图涂红。上海解放前夕,他给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家里留下了这本地图。上海解放了,全国解放了,我根据他的意思,把整个中国的地图都用红墨水涂红了。中国解放了,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没有解放哩;我们解放了,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没有解放哩;我们当家做主了,他们还当奴隶哩!帝国主义一天不消灭,世界上劳动人民不能完全解放,我们自己也不能算彻底解放啊!天下工人是一家,我们解放了,就应该支持他们,解放全世界。这是共产党员的理想,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国强牺牲以后,我经常把这本世界地图带在身边,学国强那样,哪一个国家解放了,我就在地图上绘一面红旗,希望有一天,我亲眼看见红旗插遍世界!”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秦妈妈说。
“这要靠我们和各国人民的斗争了。”余静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辰光,只有十几个人,就靠这十几个人不断发展,解放了全国!现在中国解放了,解放全世界更有办法了!我经常把世界地图带在身边,就是要让自己不要忘记世界上的劳苦人民啊!”
“这名单和地图是余静同志身上的两件宝!”秦妈妈说。
“这可是宝贝啊,有多少钱也买不到哟!”汤阿英听余静娓娓谈来,像一股清澈见底的涓涓细流,无孔不入地灌溉她的心田,轻轻拨动她感情的琴弦,发出动人的旋律,永远使人不能忘记这些名言!经余静一说,她更相信自己刚才对巧珠奶奶说的话。她对巧珠奶奶说,“你听见余静同志说的话吗?”
“我也不是聋子!”巧珠奶奶知道汤阿英想用余静的话压她,心中有些不满。
“我是好意……”汤阿英想解释。
“我也不是恶意!”
“有话慢慢讲,”秦妈妈见婆媳两个人讲话不投机,连忙劝解,“余静同志说的道理很重要啊!”
“余静同志讲的话,我句句听的进。”巧珠奶奶对余静讲的那些话,不完全懂,有些人的名字也不大知道,但她看出余静伟大的胸怀和崇高的理想,深深敬佩余静。余静究竟是厂里的支部书记,又是工会主席,办大事的人,比秦妈妈高明的多了。汤阿英和她们比起来差的远了。可是阿英却瞧不起她这个老太婆,想借余静的话训她哩,怎不叫人生气啊!她指着阿英说,“不像你,只晓得家里的事,没想到旁人,也没想到世界大事!”
“我哪能和余静同志比呢?差一大截子哩!”汤阿英的口气缓和一些了。
“站在家门口,要看到天安门;站在天安门,要看到整个世界!”余静说,“革命先辈为我们打下了江山,奠定了基础,我们不能坐享其成,不能认为中国革命成功了,就不努力干了。革命胜利了,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有许多革命事业要我们去做哩。推翻了旧中国,还要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的责任大着哩!别的不讲,就拿我们沪江厂来说吧,五反运动取得了胜利,徐义德消极了,躺下了,对生产不积极不关心,团结他搞好生产,就不是一种容易的事体啊!”
“是呀,多亏余静同志操心,领导他们!”巧珠奶奶指着张学海和汤阿英对余静说。
“不,我靠他们才能做好工作。没有他们,我啥事体也做不成啊!”余静转过来,对汤阿英说,“最近要开劳资协商会议,晓得啵?”
“不晓得。”
“你是细纱间的劳方代表,要收集一些工人的意见,好带到劳资协商会议上去反映。”
“劳资协商会议啥辰光开?”
“这一两天就要开了。”
“我要参加劳资协商会议……”汤阿英想起昨天收到爹的信,说弟弟生病了,希望她和学海回无锡去看看。本想把家安排好了,她就请假和学海一道去,现在要开劳资协商会议,这两天就去不成了。她惦念弟弟的病,可是又不好开口,犹犹豫豫地没有说下去。
余静见她谈到要开劳资协商会议就说不下去了,以为她对参加劳资协商会议有什么意见,便问:
“车间选你当劳方代表,开劳资协商会议,你当然要参加呀!你有意见吗?”
“我没啥意见,劳方代表当然要参加会议。”
“刚才为什么不说下去呢?有啥顾虑吗?”余静以为汤阿英第一次当劳方代表,没有经验,可能有什么想法。
“没啥顾虑,”她没法不谈出内心对弟弟的关怀,讲了收到汤富海来信的情况和自己打算这一两天请假回去,然后说,“等开完劳资协商会议再讲吧。”
“阿贵得了啥病?”秦妈妈关心地说,“阿贵这孩子身体蛮结棍,怎么也生病了,真想不到。”
“身体结棍的人小病就顶过去了,顶不过去的病,看来不轻。”
“爹信上只讲阿贵得了病,没说是啥病……”汤阿英焦虑地想:弟弟身体那么好,为啥忽然生了病,真叫人放心不下。
“恐怕病不轻,怕你们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