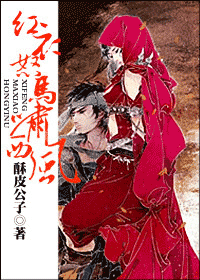怒马香车-第3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许两位事先有过什么协议,在彼此的称呼方面,形成某些程度的差异。
尽管石瑶姑对汤紫云一直称之为姊姊,但汤紫云对石瑶姑却有人前人后之不同,人前,她有如一属下恭恭敬敬地叫车主,但人后却以姊姊的身份叫瑶妹……
石瑶姑幽幽地一叹道:“过去的事,不谈也罢!”
接着,扭头向呆立一旁的石家庆说道:“孩子,咱们走吧……”
★ ★ ★
杜少恒虽然身处“禁宫”之中,但对于外间的情况,却并不隔膜,因为,一切都有俏丫头冬梅会转告他。
他,可能是神经麻木了,也可能是石瑶姑透过冬梅之口,对他有过什么特别指示?或者是他自知对目前的局面无能为力?因而对于目前正邪双方首脑人物的突然明朗化,不但根本无动于衷,反而更以醇酒妇人去麻醉自己。
至于那位天一门主,也就是他的表兄曹适存,也没再去找过他。
经常与他接触的,是这儿的分宫二娘娘公冶十二娘和俏丫头冬梅。
他,似乎是喧宾夺主,俨然成为这儿的主人翁啦!
另一方面,欲望香车也突然失踪。
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由于正邪双方首脑人物突然明朗,而使得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不了了之。
但骨子究竟是怎么回事,恐怕只有他们双方的首脑人物心中明白。
这种表面上一片详和的日子,维持了将近四个月,已是绿肥红瘦的初夏时光。
对洛阳城来说,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并无任何改变,只是由于季侯由隆冬转入初夏,因而街头上的行人,显得多了些而已。
当然,大相国寺前,那百技杂陈的广场上,也特别显得热闹起来。
今宵,广场上新添了一个说书的场子,不!说书的扬子是原先就有的只不过是说书的人儿换了新的而已。
原先那说书的,是一个老头子,打杂的是两个十四五岁的男孩。
新来的这个说书的,是一位年约三旬上下的文士,不但气质上显得文质彬彬的,面孔也长得非常清秀而俊美,算得上是一个美男子。
打杂的也换了,是一老一少。
老的是一位青衣老妪,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看情形,年纪至少在六旬以上。
少的是一位年约十八九岁的美姑娘,一身玫瑰红的袄裤,两条大辫子,配上了她那宜嗔宜喜的俏脸蛋儿,和婀娜多姿的身裁,不论是男人或是女人,都会忍不住地,要多看她几眼。
说书的青衫文士风流倜傥,打杂的红衣妞儿柳媚花娇,这已经是够吸引人的了。
但事实上,却还有更吸引人的哩!
那是棚柱上的一副对联,红纸黑字,龙飞凤舞地写着海碗大的草书:谁识得座前黑尺?
我说段武林秘辛!
横楣是“绝对新鲜”。
华灯初上,说书场中,已经是座无虚席,不但座无虚席,而且,那本来只能够坐三个人的条凳上,居然挤了四个人,却是谁也没有怨言。
两个打杂的刚刚将客人的茶冲好,说书的青衫文士也缓步由幕后出场,从容就坐。
青衫文士刚入座,人群中立即有人扬声问道:“嗨!说书先生,你那‘绝对新鲜’的‘新鲜’二字,作何解释?”
青衫文士笑了笑,说道:“这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在下说书不落俗套,立论新鲜,其二,是……”
他扬了扬手中的黑尺,含笑接道:“如果有人能识得我手中这柄黑尺,在下所说的武林秘辛,也是绝对新鲜,此外……”
他忽然住口不言,端起面前的茶杯,慢条斯理地,喝起茶来。
人群中,那人又扬声说道:“嗨!说下去呀!”
青衫文士道:“我看,此外的这一点,还是不说也罢!”
“为什么话说一半又不说了?”
“因为,最近五年来,在下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可从来不曾遇上一位能识得我这黑尺的人,所以,这附带的一项,也就毋须多说了。”
“这是说,这附带的一项,就是识得你手中黑尺之后的赠品?而且,也是新鲜的?”
“对了,阁下真聪明!”
“既然被我猜中了,何不索性将那赠品说明一下呢?”
“有道理。”青衫文士抬手一指俏立一旁的红衣女郎道:“这是在下劣徒小云,也是我方才所说的赠品,诸位不妨仔细瞧瞧,够不够新鲜……”
人群响起一阵狂呼怪叫:“够新鲜!够新鲜……”
青衫文士向红衣女郎笑了笑道:“乖徒儿,咱们虽然走南闯北,一直没遇上一个识货的人,但这回却有点儿不同啦!”
红衣女郎娇笑道:“徒儿回并未觉得这儿有什么不同之处。”
青衫文士道:“你不知道,洛阳城,是文人荟萃的古都,也是江湖人物的卧虎藏龙之所在,我想,这一枝黑尺,一定会遇上识货的行家的……”
这时,人群中最先问话的人又扬声问道:“嗨!说书先生,既然已备有如此美好而又珍贵的赠品,为何不事先用文字说明呢?”
青衫文士不答反问道:“阁下此问,想必还另有解释?”
“不错,据先生方才所说,业已走遍大江南北,历时五载没遇上一个能识得这枝黑尺的行家,是吗?”
“不错。”
“在下愚见,先生这枝黑尺的质料和来历,必然都是很奇特?”
“那是当然。”
“同时,也是由于先生那珍贵无比的赠品,事先未用文字说明,因而不能引起广泛的注意……”
青衫文士截口笑道:“不!这点,在下要特别加以补充。”
人群中语声道:“唔!小可正恭聆着。”
青衫文士含笑接道:“有关劣徒这项赠品,虽然不曾以文字写明,但在下每新到一地在第一场白中,必然以口头加以详细说明,但今宵,在下刚刚坐下来,阁下就开始发问……”
人群中语声截口苦笑道:“哦!如何说来,倒是区区我的不是啦!”
“不是倒也说不上,只是阁下的性子,未免太急了一点。”
“有道理,有道理……”
“阁下稍安勿躁,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请等在下说完这一段开场白之后,再行发问。”
“行!行……”
青衫文士把手中黑尺在桌子上轻击三下,目光环扫全场,扬声说道:“在下劫余生,携小徒小云,走南闯北,说书糊口是假,以兵会友,代徒择婿才是真。”
一顿话锋,扬起手中的黑尺,含笑接道:“诸位请仔细,在下所说的黑尺,就是这一枝,能同时说出它的名称,质料,和来历者,才算合格。”
人群中那原先发问的人,又扬声问道:“现在,在下可以发问了吗?”
“可以。”
“在下请教,是否只要如阁下所说的合格了,就可以长侍令徒妆台……”
“不!婚姻大事,自然还得他们双方当事人互相认为满意才行。”
“那岂不是一个骗局?”
“此话怎讲?”
“因为,即使有人合格了,阁下都可以借口令徒不满意而作为罢论。”
“说得有理,但阁下也得为劣徒想想,如果那合格的人是一个七老八十的糟老头儿,或者是一个残废者,岂不贻误她的终身。”
“那你也该事先加以说明才是。”
“在下已经开场中说明了,‘以兵会友,代徒择婿’,这是说,纵然是择婿不成,凭着对这一枝前古奇兵的认识,也可以结为朋友……”
人群中忽然冒出一声冷笑道:“恐怕是冤家吧?”
劫余生淡然一笑道:“朋友与冤家之间,有时候是很难划出一道界限来的,阁下以为然否?”
怪的是,那个突然发出一声冷笑的人,于说过一句之后,竟没了下文。
劫余生精目环扫全场,沉声问道:“谁还有疑问的,请尽管问。”
等了半响,再没人发问之后,他才正式开始说书,说的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
严格说来,他不是说书,而是说故事。
表达的方式不落俗套,立论更见精辟,将这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美化得不能再美了。
在一般人的观念,司马相如是一个潦倒穷途的落拓文士,十足是一个穷小子。
以一个穷小子,去勾引一个年轻,貌美,而又多金的小寡妇卓文君,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尽管这块天鹅肉被他吃到了,但一般人的心目中,对司马相如都是或多或少地,存有某种成见的。
至于卓文君,以一个新寡的富孀,不耐寂寞,竟然降尊纡贵地,接受一个穷小子的勾引而相偕私奔,去当炉卖酒以维生,一般人,尤其是所谓有着冬烘头脑的道学先生们,更是不齿其人。
但目前的劫余生,他却很技巧地将这个一般人所认为有缺陷的爱情故事,美化成完美无瑕。
首先,他由不同的时代背景中,不着痕迹地,替两位男女主角辩解。
他说:我国的男女关系,在汉,唐时代,是很自由,也很开放的,直到宋代理学大兴之后,才有着那么多不合理的礼教……
那些看似冠冕堂皇的教条,是杀人不见血的咒语……
那些制订那些教条的人,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
他们视男女关系为世间最污秽,最丑恶的事……
但事实上,那些人对男女闲事,却是特别喜欢得不得了,他们板着面孔去教训别人,这不行那也不可以,但他们自己,却是三妻四妾还不够,还要广置年轻貌美的婢女,供他们随时消遣,自己玩腻了,又将那些婢女卖给别人……
在汉唐朝代的宫廷,父亲抢自己儿子的妃子,哥哥夺弟弟的老婆的事,屡见不鲜,不但没人说他们不对,反而传为美谈……
那些宋代以后的一般假道学先生们,也不曾见到他们对那些父纳子妇的事,作过什么针贬……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是汉代人,他们是生长在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社会,有权利去爱自己所爱的人,为什么后代的人,要受那些假道学的影响,而以一种异样的眼光去衡量他们……
★ ★ ★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这是非常大胆的论调。
普通人,不但不敢在大庭广众中说出来,甚至于连想想也会被认为是礼教叛徒的。
但目前的劫余生,却是大胆地,在大庭广众之中说出来了。
这,当然够新鲜,也够吸引力。
开宗明义既然说得那么独特而精辟,以后的故事,自然更为动听,也更为吸引人。
也由于故事说得太精彩,太吸引人了,因此,在整个说故事的过程中,扬子里面鸦雀无声,除了终场时的那一阵有如春雷爆发似的掌声之外。根本没人插口说过一句话,当然,也更没人过问那枝黑尺的问题了。
★ ★ ★
一连十天,劫余生这个说书场子,场场都是爆满。
至于那柄黑尺,除了第一天时,人群中有人问过之外,在十天当中,似乎被人遗忘掉了。
当然,听说书的人可以遗忘,当事人的劫余生,他是不会遗忘的。
于是,在第十一天的夜场开始之前,劫余生一扬手中的那枝黑尺,忽然没来由叹了一声。
人群中有人讶问道:“先生,你的生意好得不得了,干嘛反而叹起气来?”
劫余生苦笑道:“在下叹气不为别的,是为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