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山伯爵(三)〔法〕大仲马-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谁施舍钱给穷人,就等于还债给主,’在我们的钱袋装满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宫里,她不告诉我父亲,派人把钱送到修道院,发放给囚犯。”
“您那时候多大?”
“三岁。”海黛说。“那么您在三岁的时候,记住了那么多事情吗?”阿尔贝说。“都记得。”
“伯爵,”阿尔贝轻声对基督山说,“请允许夫人把她的身世告诉我,您不许我向她提起家父的名字,可也许她在追忆往事的过程中,会不偶尔提到他,如果我们的姓能从两片这
234
基督山伯爵(三)521
么迷人的嘴唇里讲出来,您绝对想象不出我会多么的高兴。“
基督山转向海黛,脸上是一种提醒她分外小心的表情,用希腊语说:“把你父亲的遭遇告诉我们,但不要说出那个出卖你们的人的名字,也不要说出他出卖你们的过程。”
“您在告诉她什么?”马尔塞夫小声说。“我再一次提醒了她一次,说您是一位朋友,对您她不必隐讳什么。”
“那么,”阿尔贝说,“为了囚犯的福利而作虔敬的巡礼是您回忆中的第一件事情了,其次又是哪一件事呢?”
“噢,回忆起这些就好象是昨天发生的一样,我记得我坐在一个湖边无花果树的树荫下,颤动的枝叶倒映在水里,象是照在一面镜子上。在那棵最古老和枝叶最茂盛的大树下面,坐着我父亲,他斜靠在枕垫上,我的母亲坐在他的脚边,而淘气的我则摆弄着他那飘垂到胸前的白胡须,或是挂在他腰带上的那把镶着钻石的弯刀和刀柄。 不时有个阿尔巴尼亚人走到他跟前来,对他说些什么,我对那些事情并不关心,而他总用相同的口气回答一个‘杀’字或‘赦’字。”
“这不是在演戏,也不是在小说里,”阿尔贝说,“可我却从一个年轻姑娘的嘴里听到这些事情,真是奇妙极了。 您的眼睛既然习惯了那种神奇的景象,那么您对于法国的印象又如何呢?”
“我觉着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海黛说,“而我所看到的法国是它的真实面目,因为我是用一个成年女子的眼睛来看它的。 而我的祖国,我却只能从我那不成熟的记忆里所产生的印象来判断,好象它总是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氛围中,有时
235
6211基督山伯爵(三)
灿烂辉煌,有时却阴森惨淡,那得看我的眼睛看见的是我那美丽的故乡、还是我受苦遭难的地方了。“
“这么年轻!您对于痛苦,难道除了知道它的概念以外,就已经了解到它的含义了吗?”阿尔贝说,不自责地接受了庸俗的见解。海黛看着基督山,伯爵几乎难以觉察地叹息了一声,轻轻地说:“说下去。”
“幼年时的记忆,在脑海里的印象是最难忘的,除了我刚刚向您说到的那件往事以外,我幼时的回忆就都是令人难过的了。”
“说吧,请说吧,夫人!”阿尔贝说,“我向您担保,倾听您叙述。”
海黛抑郁地微笑了一下,回答了他这句话。“那么您希望我继续讲我其他的那些往事吗?”她说。“我恳求您这样做。”阿尔贝回答。“那好!
我刚四岁时,有一天晚上,我突然被我的母亲惊醒了。 我们那时住在亚尼纳的宫殿里。 她把我从睡床上抱起来,我睁开眼睛,一眼就看见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我见到她哭,就跟着大哭起来。‘别哭,孩子!
‘她说。 在别的时候,不管妈妈怎样疼爱或恐吓,我总是要任着一股孩子气哭个尽兴,把我的悲伤或者怒气发泄完了才肯罢休。但这次,我从母亲的声音里听出强烈的恐惧感,以致我立刻就不哭了。她抱着我急忙地向前走。 我到那时才看到我们正从一座宽大的楼梯往下走。 在我们的前面,是我母亲的所有佣人,他们背着箱子、包裹、首饰、珠宝和成袋子的钱币,都仓皇地从那
236
基督山伯爵(三)721
座楼梯向下奔。 跟在女人的后面来了一队二十个卫兵,都拿着长枪和手枪,穿着希腊建国以来你们在法国早就晓得的那种服装。 您可以猜想得到,一定是发生了某种可怕的、不幸的事情了,“海黛摇摇头,只回想到那幕情景,她的脸色就变得苍白起来。”在这一大队的奴隶和妇女之中,只有一半还是清楚的——至少我应该是这样,因为我自己都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楼梯的墙壁上东一个西一个地映出巨大的影子,在松枝火把跳动的火光里跳跃着,仿佛一直跳到上面那个穹形的屋顶。“‘快!
‘走廊一头儿有一个声音说。 这声音让每一个人都对它低下了头,就好像风吹过一片平原,使田里的麦子都低下头来一样,而我,我听到了这个声音时也发起抖来。 这是我父亲的声音。 他亲自殿后,他身着华丽的长袍,手里握着你们皇帝送给他的那支马枪。 他用手扶着他喜爱宠臣西立姆的肩膀,赶着我们大家在他前面走,象一个牧童赶着他那散乱的羊群一样。我父亲是欧洲著名的人物,“
海黛昂着头说,“大家都知道亚尼纳总督阿里。 铁贝林,土耳其人一看见他就要浑身颤抖。”
这几句话的语气自豪和庄严得无以形容,阿尔贝听了不知为何竟吓了一跳;他好像觉着在海黛那一对亮晶晶的眼睛里,有某种非常阴森可怖的表情;阿里。 铁贝林那次惨死在欧洲曾经轰动一时,而她此时就象是一个招魂的女巫,把那个血淋淋的鬼魂又叫了出来。“没过多久,”海黛说,“我们就不再往前去,我们已经走到一个湖边。我的母亲把我紧紧地抱在她气喘喘的胸怀里。不
237
8211基督山伯爵(三)
远处,我看到了父亲,他正着急地环顾。 湖岸上有四阶大理石的台级通到水边,台级下面有一只小船飘在水面上。 从我们站着的地方望过去,我看见湖的中心有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水寨。 这个水寨在我看来好像相当远,也许是因为晚上天黑,什么东西都看不太清楚。 我们踏上那只小船。 我记得很清楚,桨打在水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在我侧身去寻找原因的时候,我才看到桨上包着我们卫兵的腰带。 除了船夫,船上只有女人、我的父亲、母亲、西立姆和我。 卫兵都仍然留在湖边,准备掩护我们后撤。 他们都跪在大理石台阶最下面的那一级上,以便遇到追击时,可以用另外三级当防御工事。我们的船顺风飞驰。‘船怎么会走得这么快呢?
‘我问母亲。’嘘!别出声,我们在逃命哪。‘我不明白我的父亲为什么要逃呢?——他可是万能的,以前总是别人逃避他,他经常说:’他们恨我,但他们也害怕我!
‘“但这次真的是我的父亲在逃亡了。我听说,亚尼纳城的守军,因为长期作战,劳苦不堪……”
说到这里,海黛向基督山瞥去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 在她叙述过程中,基督山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她的脸。 这位年轻女郎于是又往下讲,但讲得很慢,像是一个讲历史的人特意捏造或讳饰一部分事实似的。“夫人,”阿尔贝说,他对这一段追述非常注意,“您刚才说过,亚尼纳城的守军,因为长期作战,疲惫不堪……”
“已经有意和土耳其皇帝派来捉拿我父亲的那位高乞特将军讲条件。 那个时候,阿里。 铁贝林派了一个他非常信任的法国军官去见苏丹,然后决定撤走到他以前就为自己准备
238
基督山伯爵(三)921
好的那个躲避灾难的寨子里去。“海黛继续说。”这位法国军官,“阿尔贝问道,”您还记得他叫什么吗?“
基督山迅速地和这位年轻女郎交换了一下眼色,这个动作阿尔贝丝毫没有觉察到。“不,”她说,“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但如果能记起来的话,我就会告诉您。”
阿尔贝差点都要把他父亲的名字讲出来了,但基督山缓慢地举起一个手指,做出不满的表示;那位青年想起自己的诺言,就不出声了。“我们当时就朝这个水寨划过去。我们所能看到的,不过是一座二层楼的建筑,墙上刻着阿拉伯式的花纹,露台一半浸在湖水里。 但在地面以下,还有一个又深又大的地窟,我母亲、我还有女仆们都被带到那儿。 这里藏着六万只布袋和两百只木桶,布袋里有二千五百万金洋,木桶里有三万磅火药。”在这些木桶旁边,站着我父亲的宠臣西立姆,也就是我刚才跟您提到的那个人。 他的任务是昼夜看守一支枪,枪尖上系着一支燃烧的火绳,他已接到旨令,只要我父亲发出一个信号,他就把这些都炸掉——水寨、卫兵、女人、金洋和阿里。 铁贝林本人。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些奴隶们因为知道自己的生命朝不保夕,所以整天整夜不住地祈祷、哀号和呻吟。 对于我,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年轻军人的那种苍白的肤色和阴郁的眼光。 不管将来死神何时召唤我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我相信他的神态一定跟西立姆的一样。 我无法告诉您我们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那时,我甚至还不知道时间到底
239
0311基督山伯爵(三)
意味着什么。 有时,当然这种机会很少,我父亲会把我的母亲和我叫到露台上去,每当那时我很高兴,因为在那个气氛阴郁阴气沉沉的洞窟里,除了奴隶们哭丧着的脸和西立姆的火枪以外,我看不到其他东西。我的父亲坐在一个大洞前面,目光凝视遥远的地平线,全神贯注地仔细观察湖面上的每一个黑点,我母亲靠在他身边,头枕着他的肩胛,而我就在他的脚边玩耍,带着天真的好奇心眺望着雄伟地矗立在地平线上的宾特斯山,那白皑皑、棱角分明、从蔚蓝的湖面上高高突起来的亚尼纳堡,以及那一大片黯黑青翠、从远处看象是附着在岩石上的苔藓、其实却是高大的枞树和桃金娘。“有一天早晨,我父亲派人把我们叫过去,我们看到他很平静,但脸色却比往常更加苍白。‘要勇敢,凡瑟丽姬,’他说,‘皇帝的御书今天到了,我的命运就要被裁决了,假如我被完全赦免,我们就可以体面地回亚尼纳去,如果情况不利,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逃走。’‘但如果我们的敌人不让我们逃走呢?
‘我母亲说。’噢!这一点你放心好了,‘阿里。 铁贝林微笑着说,’西立姆和他的火枪会答复他们的。他们非常愿意看见我死,可他们不希望和我一起死。‘“这些安慰的话不是我父亲的心里话,母亲听后只是叹息。 她给他调配他常饮的冰水,因为来到水寨以后,他就总发高烧。 她用香油涂抹他的白胡须,为他点燃长烟筒,他有时会连续几小时拿着烟筒,一直静静地望着烟圈冉冉上升,变成螺旋形的云雾,慢慢溶进周围的空气里。 忽然间,他做出一个非常突然的动作,吓了我一跳。 然后,他一面仍盯住开始让他注意的那个目标,一面叫人把望远镜递给他。 我母亲
240
基督山伯爵(三)131
把望远镜递给他,她这么做的时候,她脸色看上去比她所对的大理石柱更洁白。 我看见父亲的手在颤抖。‘一只船!
……
两只!三只!
‘父亲低声地说,’四只!
‘于是他站起来,抓起武器。 准备好了他的手枪。’凡瑟丽姬,‘他对我的母亲说,’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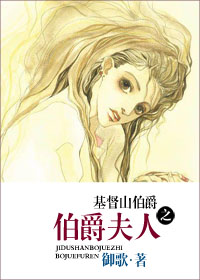

![[基督山伯爵]监禁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66/6689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