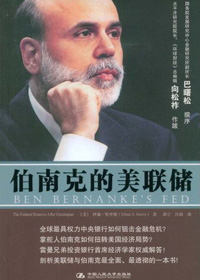̨�������������� ����:������-��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ӷ��µ���¶�������ŵ�һ��Ů����è���ҽл������㡣��ʱ�����鲻֪�Ӻδ�ͻȻɱ�˳�������ס�Ǹ�ɫ������һ�ٺ��ᣬ���������˺�С����Χ�����кá�
�������˸���������ȭ���ű㵹�ڵ��£��������Ѫ������һƬ�������ϡ�
��������������ɫ���࣬�������죬߬��һ˫ȭͷ���Դ���һ�����ֽ���һ�Ѿ�������δ����һ�³������������ѣ����˾Ͷ�Ц�ˡ�������ӲҪ�������Ͼ���ȥ����ʱ���ӵĸ�ĸ�ֳ����˽�������˵��Ȱ���������������ⲻ�ǣ���Ž�����ؼ�ȥ��
�����Ӵ�������������Сѧ����������֪��Ӣ�����������������������ȭ��ģ�����������������䶷ʱ����ѧϰ�ı����ơ������������Ҳ�������˸ҿ������������ˡ�
������ʱ�ڣ��컹���š���ͬ����������Ұ�ݶ������ȷ��˵���ҡ���ô�����Ǵ�һ���ɾ��İ��־С���������²��ÿ���Ū�ࣩ�������DZ߳������Ӽ��������������ɿ��������ߴ�ׯ�ϵ����ݡ��������ź�Թ������Ů�������źͷ��͡�ĩ�ˣ�����̾�������½���˵����Ҫ��������Ů������ô�ѿ��������һ���Ӷ���ҪȢ���š�
������Ҫ������ôС���뵽ҪȢ�����ˡ�
��������˵��ҪȢ������������֪�������㲻ϲ��СŮ�����Ǵ�Ů����ô�������ҽ���������������ׯ�ϵ�����û�У��������Ľ���һ����������������ʲô�����ҹ��ⶺ������������û����ȥ��ׯ������������·��һ��һ�������̣����������ˣ���Ҫ�����㣬��ȥץһ�ѣ�����Ҳ������ô����
�����������ˣ��Ҳ�Ҫ������������ָͷ�Ͻ����������ɾ�������ס�����ͷ���ص�ҡ��
������Ӳ�����������֣������ʵ�������������ô���������㵱���ţ�����һ�����⣡��ȥ��ģ����ҿ�������Ҫ�������Ż���࣡���Ҵ�Ц��վ���������������˳�����Ⱥ�����ɿ���м������Ⱥ�����������Ĵ��Ӵܣ���һ·����ɱ��ȥ��ֱ�������ˣ����к�Щ����û�͵��������Ҳ����ģ����Ӵˣ��������������ŵĻ����ڰ༶�䴫���ˡ�����������ÿ�ο����ң������������Ȼ�һ���������Σ�����ü�����Ȼ����Ҳ���ٸҸ���˵���ˡ���һ�ο���������Ī������غ��������������������̼��ˣ���Ȼ���ǹ������Ǹ����˵����ġ�
����Сѧ��ҵ�Ǹ���٣��ƻ�ʱ�����dz�������һ���������̵�����ȥ�棬�������ܴ�������������һֻ�ư�ë��С������
������ʱ�˼��梺���С��Ҳ�������һ��ɢ��ȥ���Ƕ����������̫�����£���ߴ�Ƭ筺�Ƚ��ϼ�ʣ����ִ���֪�˼���������ʱ�������������ǰǰ�����Ҫ��ɢ���̾�����С�ӵ������������ֻС�����˷ܵ������ǵ������ش�����������Ծ��ǰ���ͷ��̡������ǹ䵽��أ������ѵ��ڳ��ӵĶ������������������С�
�������Ѿ������ˣ��������ᴵ����������硣��Ƭ����δ������ĺɫ��գ��ر����ܵ���ɫ�Բݺͺ�����̫����ȫ����ӳ��һ�ؿ���������ż�������������ij�ˮ�С��Χ�ų����ܣ�������С��Ҳһ��ӳ����ĺɫɽˮ�С��˼��梺�С������ľ̤���ϣ����Գ�������������శ�����������ʱ��̲��ξ���������������������������������
������ͤ�⣬�ŵ��ߣ����ݱ����졣������������У�Ϧ��ɽ��ɽ��
������֮�ģ���֮�ǣ�֪�������䡣һ���Ǿƾ����Ϧ��ɽ��ɽ��
�����˼�С�ú����ܲ���ȫ��ʣ���������ô�Һߺߡ�Ҫ���ɴ೪��̨��裺��ҹ������ҹ�����ܷ��괵��أ����˿�����ÿ��Թൣ���л�������ٻء���
������ѽһ����ѽĶһ����������������ѽ��������������������ˮ������
�����˼���ɤ�����������Ҷ�ϲ������������ͤ�⣬�ŵ��ߣ����ݱ����졭����ǰ������Ƿ���һ��Ƭ�����ӵ�����ȥ�ˡ�
������������Ҫ����û���������ӣ��������������ˮ�ﶪʯͷ����˭����Զ�����������Ρ�
������������������������������������������������������������������
��������ڹ���֮�����������ֻ���룬��Բ�����ۣ���˼������ϣ��Ż�����ʴ��ȥ����Բ����������������������˵�����Ķ����Ծ�������
����������ϴ��������ľ�崲�ϣ����˼�����ôҲ˯���ž���
�����Աߵ�ׯ����˯���ˣ����ż��н�����������¹���������Բ���Ϻ�������һ����������ɵı�����ƽ������������ֱ�����û����ĺ��ӡ�
������ǰׯ���ֻ����У����߸��´�ʱ�����˼ҵĹ�����ȥ��
�������ǵ�ù�������Ѳ���ҽ��˵��Ҫ�ʶ��ӽ�����ȡ�������ɡ���û��������������ȥ��������ӻ������ˡ�Ӥ������ɴ����Ѫ�Ӻ���ɴ�����Ƭ��Ƭ�����������Ǹ���Ӥ�ء�����Ҫ�ҿ�ɴ������������ȴӲ����ʿ���˻�ȥ������ô�붼������Ӥ��Ϊʲô������ô�����Ѫ��������Сҽ���µ�̫�أ���С�Ľ����Ӹ����ˣ����������ʣ�������ȥ�������ۡ�ֻ����ҽԺ��ΰ������һ����ʪ�ġ�������ɫֲ����쾮�����صؿ��������������㷼���ɪ����վ�ڸ��ڵĴ�̨�ߣ�͵�����Ÿ��ף�����ǰȥ�����������䶼���������������ߩ������������������ͨ��ͨ���־����£�ֻ��û������
�������������Ժ�ׯ�Ͼͱ���������ġ��ճչ����������ٺ�����ׯ�ϰ�ҹ��Ҫ�ѣ�����һ����̾����˵����˵��һ��Ҳ��ҲЦ��Ҳ��֪��˵ʲô��Цʲô����Щʲô���������������ˣ��������ӣ�����������Թ��Ե�˵ȥ���������ʱ��Ϊ����ز��ʹ�����ܴ̼�����Щʱ�ձ����ˣ����Ǿͷ������Թ��Ե�˯�ˡ��������Բ����ׯ�ϴ����Ժ�֪���ı������������ͷ�Բ�����������Ϊ�������ļ����ѣ������ͷ�ͽ��ϻ����ܲ��̲˵�С���ظ���߶���ݡ������������ܹܼң����Ͻ��Լ�Ҳ���߶��ˡ�������Ÿе������ͬС�ɣ�����ûǮ����סԺ���������ԴӺ���������Ҳ������ҽ����������˵סԺҲδ���εúã�ֻ�������������ȥ���Լ����ܵ���̫̫�Ƕ�ȥ����������취��
������������ֻ��ɫ�����űߵ���ñ����������Ծɲ����ݣ�վ�ڳ����ſڰ����ͷ��ͬ��̫̫����˹����˵�ţ�����Ҫ�����ֳ�����˵Ҫ���������ĸ�ҵ���Ҵ���ȥ�ϲ�ѧѧ������������û���������������ӣ�����Ҳû�����dz�ס�ĵط���ׯ���ⲡ��֪��Ҫʲôʱ��źá�Ҳ��֪�ò��õ��ˡ�
���������롭��
���������˶٣�ͷѹ�ø����ˣ����ѻ�˵��������������û��ʲô������ġ�������Ҳ������࣬�շѱ��˵�����Ժ֮��ĵط����Ѻ������Ȱ����ˣ��Ҳźð���ȥ������
�����ǰ��ǰ�����̫̫һƬ���ģ���˵�и��¶�Ժ�ǽ�����һ�ְ�ģ��������û�Ǯ���豸��ʦ�ʡ���������һ����һ���ù�����ȥ˵˵��������ô���ܰ����������ͽ�ȥ���ǡ�
������������˵�����ĸ�л������������ϣ����ȥ�ˡ�
������ҹ�����ƬƬ�ζο��źڰ�����Ƭ�Ͻ����˱���������Ժ�����ӣ�¶���߹����е�Ц�ݡ�ͻȻ�������㷼�����ˣ��ܺ��ߵر�������Ӽ���һ�ԣ���Ӱ���Ļ���ʱ��ʱ��ȥ���ǵ�ͷ�����ֽš���Ҫ�°�������������˷��ּ��еؽ��ţ�ȥ�����������֣����漴һ�ɸл����������ἴ�����������
�������Ϲ�̫̫���Ե���̾���������㷼Ҫ�������Ǹ�������Ѭ���³�����������ʶ��һ�����ء���������������ʮ��Ĺ���������̼���ǫ���ޱȣ���������ס��ҾЦ��������ţ�Ŷ��ԭ����ͬ���˼��������ء����������ٶ��˷��������Ѳ�����Ϊ�������㷼����ȥ����ô����������ҹ������˯��ȫ���ε���Щ��ߵ������Լ����ӹ�����ǰ���°��ܵ�շת������
����δ�ϣ����鲻�ɡ�ԭ���ǹ¶�Ժ�����ܸ�ĸ���ڵĺ��ӡ�
���������齫Ů������ʱ�и��������������ţ��Լ�����ȥ���ϲ��������º��������ˣ������㷼�������ݣ������鿴�Ų��̣�������̨�����˿�һ�γ����˵��
����������ɹ���ֺ���׳����ͷ�������ˣ��Ժ�һ�ζ���Ƥ��������˷��ͣ�������أ�����û�д�ǰ���ֳ������������ڣ��Ҳ�֪����Ϊ���˻������ˣ������ݺ��Ŵ��˵����������촽ɹ�ý��ɸɵģ����ﲼ��Ѫ˿��ֻ��Ц�������й����ĺۼ�����ร���ȴ��֪��ʱ���ϻƳγεĽ�����������ʵ�����ľ�����ȫ������ȥ���������ഺ��ç�����������ˡ�
�����ؼҵ��Ǹ���ݣ������������㷼ȥ��ׯ�ϡ�ׯ�Ͼ����ϵ������Ƶġ��㷼�����̲�ס��������������Ҳ���ű��ӣ�ȴ������һ��ȥ�����ô���˵��������
��������˵ׯ���ⲡʱ��ʱ��������ʱ��������ڼ���ţ�һ�����������˳�ȥ���߶�����С���ɲ�֪��Ҫ����ʲô�������
������Ҳ����һ��һ�붼���ڼ����Ҫ��ȥ�����ѽ�ģ���˵�ǰɣ��������ǻ���ѽ�����Dz�֪����ʲôʱ��Ҫ������ѽ����������С������������ׯ�ϵ�ͷ������֮���Dz����ٸ���������ˡ������鵱��л�������������ׯ�ϻؼ�����
���������������ۣ�ׯ���Դӻ�����û�ٷ�������������Щ�٣��ۣ���������û�����Ƶġ������������Ͳ�������Ҳ�����ֱ��ˡ�
���������鷢�����Ŀ���һ�Դ��ϵ�����Ů����˯���������룬Ҫ��������������������ļ�������Dz�ʲô������ô��
����Ҳ��˼ҵĺ���������������ʳ�س�������֦��Ҷ�Ƶģ�����Ҫ�ȹ˼�����λС�㻹���ý��������ء�
����·�ϴ������յĽ������ԡ����ƣ������ԡ����ơ�����һ��Զ��һ��������Զȥ��
����������ź��žɱ�ֽ��Ů���������İ�ǽ�棬�ڴ��������¹�������°�����ţ������ź����Ȼ�Ĺ⡣��Щ������ʣ�µĴ������Σ��������Ǽһ����õ��ϣ��������ž�ֻ�䵱����ա���ֻ�������������������ʣ�µķ������ӣ�һ����������Ͼ�����������Ӱ���϶�����˷�IJ������ﴵ�����������ġ������ڵð��ƴ��������ˡ������˸����硣�����Ƕ�������һ�ţ������־���ׯ�ϴ����α���һ��ë�£����������¹������ͳ���֪ʲô������һ�������Ӹ��ϡ���֪����뻹�Ƿ������һ�����߰����ֽͷŪ�������졣һֻ������ڲ��ø�Ĺ����ϣ���ͷ�����һ��ʪë����������ˮ���Ѿ���̨���ϻ��˲�С��һ̯�������Ź�����������ϣ����ɵ���İ��������ű�ȫ�ҵ���Ь���
��������·������Ħ�˵ĵ�����������������������ƫƫ����������ҹ��û�������������ƣ��������ҹ��ò�������
���������������ᣬһ�ɾ������µ�������˵ĺ�������һ�����������С������Ȳ������ϡ������ֲ𡢾�����֪�����������ƾ��Ű壬��������ᷴ���Ųҵ��IJʹ⣬������߰������ż������ӡ�С�������������ë���������˽ǵ�Բ��һ�������Ķ���ͻȻ����û��������ô������һ���������ˣ�����������һ�������м��ء�����ͻȻ���塢ȴ���������Լ�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