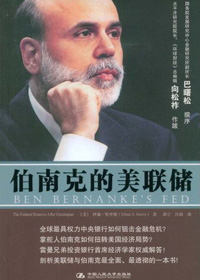̨�������������� ����:������-��37����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û��ã����DZ���ȫ����������̵Ŀ�Ұ���������ѩ�ɡ��Ĺ����ˡ����ô�Ắ�Ķ�ҹ�һ��������һ����ð��ѩ�����ŷ磬��������ǰ�С�
���������ֱ�ֵþ����ˣ�ร�ѩ�����ſ��ֱۣ��������棬�����ܵ��������Ӵ����µ�ѩƬ����ѩ�������еĸ��ֺ룬��Ҫ���棬������˼�������������������㵸������˫�ŲȽ��������ѩ�ѣ�ϸ�����Ƶģ�һ��һ��������������������Ь�ס������������Ĵ�����ԼĪ��ʮ�졪���ȳ����Ļ��Ǹ������Ŀ����������Ьӡ״�����ɰ������ϼ��������������һ��Գƺÿ���ͼ������������ѩ���ϵ�ǩ����
����ѩ������ô���ᣬ��ë�Ƶ��������ϣ������㱻�����ܻ��ˡ��������ģ����̻���ˮ��
�������Ŵ�ڣ�ֱ����ѩ�������ñ�����������Ӵ����IZl���������ȥ��
�����װ�������ƮƮ��������أ��ޱ���������£��ɽ���Զ��
�����������죬ѩ��Ʈ����������Ѹ�٣���б��״�Ķ������������ֱ����¡�ѩƬ�ķ������һ��ʧ�ص�ʧ��У�����Ư���š���ѩ�������ı��䣬�����������ྻ�������Լ�Ϊ���ĵ㣬��ɫ��ѩ�Ĵ��һ·�ӽŵ׳ʷ���״����˷��������ĵ���չ��ȥ����
������������һ����չ�ų��ӣ������Դ���ѩ���ϴ�תת��С������������ɵð�����߰ɡ�������ϳ�˵��Ҫ��ѩһ·���е��ǡ�
����������Ź˲�����ѩ�������������������ǰ������ʵҲ�ò��������ߴ٣���Ϊû���������е����ѩ���Ƶ���в�����ӽ���·�Ļ������п��ܻᶳ�������ѩ�
��������������û��ñ�ӡ�����Χ����ֻ��̫�������ߵĹ�������Ϊ˵������ȥī����;��Լٲ��ˡ���ī����Ķ���ô���ȵû�Ҫ�Ա�����ء�������������֣���ġ�����û�������ȴ��������ÿ������Ժ����Dz�֪������Ǽ��ô���Ŷ����������̫�����ˣ���ǰ���ܡ��������㿴��������ץ�����Ҵ�������͵�ɵĶ�Ѻ��������Dz�͡�����Ц������ȥ����Ҫ��ծ���������Ρ������Ӽ��ô������һ�����㣬�߾���������Щ���ٺ٣������Ƕ��졣��
�����ٺ٣������Ƕ��졪����ʱ��仰���ž���Щ���Ρ����ڣ������������ˡ�
����û������������ô�����š������ڸ�����ʲô���Ƕ��ʹ�ʲô��ī�������֡���ɼ��Ҳ�������Ķ�ȥ������ͷ������ǰ˵��������������������������������Ʋ���һ���Ӿ���ôһ�ء�����������ͥ������ֵĻ�������֣����ô���װ�������
����û��˭��ʲô�������������������ͷҲ����д�����Ϊ����û�и��������Ŀռ䡣������µĺ����У�������С������˼�ʮ���˺�һ��ʬ��֮�⣨��·������һ����ù�ļһ����������й��Ż�»���֮�䣬���߶��ĵط���û���١�����ֻ�ðѱ����õ��������������ͳͳ�������ϣ�ÿ���������ٴ�����������������������ӡ��⣬�������Ǵ˿����������������ˡ�
��������ѥ�ӣ�ñ�ӣ����ס������Ⱳ�ӻ�û�������״���ѥ�ӡ������������ϼҸ������Ͳ������϶������ĸ��
��������ͣ�����ô�ͬ�����˶�����������˫���ּۻ��ۣ�������ߴ�Ӧ���ط��������������������һ�ƾ͵�ʮ���졣�ϳ�����Ϊ���ܲ��˴��հ���Ŀֲ���С�������µò��У��ٴ���ȥ����Ҫһ���غ�����ô�������������Ǹ��ȹ�����������Ĵ��ս��ѳ�������ʵ�ĵ�Ҳͦ�������ô�ġ��Ƕ������´�ѩ�������𣿡�������֪�����Ƿ�ѩ��Х�����Ŀ������Ƶģ����������ţ���ȫһ��������̬�ơ����ǻ�ԭ����ϴ���ô��Ū�����ô��Ū�㡣���������ʵ��ѩƬ�������š������������Ƿ���һ�����Ĺ��ƣ�������ͷ�������������ȫ��ֱ�������Ǽ������Ƶġ����ǰѲ��������ѩ����Ȼ��������һ��ȥ���ɣ�����ѩʹ�ýŵİ���������ѣ���ʱ������˵��Ь�һ���д���˪ѩ����ʱҪ�������������ڿ�ܲ��֣���֪��ʱ�Ѿ����ɱ��ˡ�
�����������ϣ�����ͷ�����磬Ҳ���˼ҵ��ݶ����������������˺��һ��˪ѩ���ն���Щ���ֻ����µġ��ɵĻ�������ȥ���µ��ֶ�������
�������䲻��ֻ���䣬��һ��ʹ�Ѽ����ı��ף�������������̵������¶ȵ���ζ��������˵��û����ѩ�����飬������·��Ҳ���þ��������־�����������Ƕ�����֧���š�
�������������˿����������ֻ����ôһ�����ۣ�һ�����һ������Ҳ����������ۡ�����;������������ʮ��������ѩ�ĿẮ�У��漣�Ƶĸ������������ϣ���������ͽž���
����������������������������������������������������������������
�������࣬ѩ�н�С�����ơ��������㣬ѩ����ͣ�ˡ�
�����ϳ³����ؾ���������������һ�ߣ���Ȼ����������Сʱ��
�������Ż�������¶��ѹ�����ˣ�����������ȿ�������İٷ�֮һ������ֹ���䣿��ѩ��Ȼ�Ƿ����ģ����ž���һ������Ϯ��ֱ�����������λ���Ҹ�С�����Ҫ�����ñ�ѩ�����ˣ��������ⶼ�����ˡ�
��������ǰ����ͷ��֣����һ���һ�;�������飺·�Ͽ����ء���Щ�������������˵ġ��������ҷݹ����Dz��ѣ���Ҳ����һ�����֡�
�����Ҳ��£�����ʱ�������������ظ�˵�ġ����Ǵ˿̣�����ʶ����Щ��;�������˵ļһ�ѵ���Ҳ������һ������ͬ����ǿ����־�����ô�����������Щ����ùͷ�ġ������̾����Լ����������첻��ô������������Ͳ��о����ˣ��Ϳ����������ˣ���ɲ�ʧΪһ���÷��ӡ�������õľ������ڹ����������еغ����衢���壬���߿���Ҳ�С����紵�����꣡���Ͱ�������統���������´�����������ˣ������Ӵ����ô����Ӵ���������������������¯��ʱ��Ҫ���ܵ���ѩ�������������죬�治֪�ж���ء�����Ǹ����𣿡����Ǹ������¾Ϳ���߰�����������ս����Ȼ�����IJ������Եؼӿ��ˡ�
�����������ʱ����ͻȻ����Զ��һ����Ĺ�㡣һ������������Ľ�ѩ�صĶ��������ӽ����Ƿ����̣�һ��գ�����Ѿ�������ʹ������Ƥ���Ա㿴�ø�ȷ��
�����������������˷ܵؽ��������������������ϳº�С��Ҳ����ͬʱ������������վ����������վ�����ķ�������ů�����ء����������ֵ�˾��˵��������ͷ�г��кȣ��ò��˶���Ǯ���������ϲ����мӱ�ô�����������߶�ʮ�����ӵ��¡������������ϡ�����೬������ʮ���ӣ��������������ң�����
��������һ��ȸԾ�������˷ܣ����¶��˼�������������·�ߵÿ죬����������
�������ǹ���Ŀ�ĵؾͲ�Զ�ˡ��п���ʮ�����ӣ�Ҳ���������߰˷��ӡ��ļ������ţ����ϡ����Ͼ͵��ˡ����е�����ģ�����
����������������������������������������������������������������
��������������ʮ���ˡ����Ǹ��������ˡ������Ǽ��磬�����˳����������¸����ձ�ò�����£����ѳ�Ϊ��ͳ��������������������ʱ�ڣ����Ǿ��Ѵ���������̨�塢�������ǣ�����Զ�����������������������ޡ��������ȵء���������Ժ��Ĵ�ͳ��������Ϊ���¶�����ı�Ǩ�����ֻ��������ʲô�˲��������������涨���ı���˵ģ��Ϳ�������������Ĵ�ͳ��������ĸ���ǹ߳�˵�Ķ��ǣ��۳��ֿ�ȭ��ɶ��û�У��е����������еľ�����������������ǿ�����ɲ�Ҫ����ƴ������������������������㣬�������ط��ٷ��¡������ⴳ����Ŀ���ģ��������������˼�С��ȥ�������ٹ�������ϸ��������Ĺ���Ȣ��ȥ���������뵽�˻Ʒҡ�����Ȼ�����곤��ȴ���������Ĺ�����ͷ�����ѵá�Ҳ��ɰ���һ���������뵽�Լ�����Ҳ�����й�ҫ��鹵�һ�죬һ������ͻȻ�ܺ����ۿ������뵽�������ĸ�ĸ������һ���ھƳ���һ���ڳ���������һ���ӵĹ��ˡ�ĸ��ǰ�����¸ڡ���������ʮ�ģ�ֻ�ܿ�����㹤��æ�����Ҽơ�
����Ψһ���梼��㶫�����ӹ��ý���˵�������Ǹ��쵰��ʱ���������ֵģ��梵�����Ҳ���õ��Ķ�ȥ�����ⶼ�����ص㣬�������������ɡ����������ȥ���뿴���磬�������ȸ��Ǵ�ͳ����·����ƾ�Լ�˫�������磡��������Ķ�������Ͳ����������꣬����һ���������ݵĽ��ܣ��������ܵ����ڣ�����һ��̨�̿��ļӹ�����ͬ���Ǵ�һ�������õ�нˮ�������ϵ���Ǻ����Ǹ��ڹ������ϰ������һ���¼������Ķ��ࡣ����˵��������ĩ�������֧˫н���DzŽпɹ��ء�
�����������������ʱ���ǹɵ��⾢����ɷ���е��ˡ�����˭���������ǵ���С�ӣ����ں��ˣ�������Ů����ȫ���յ�����Ժ����������˵�����ϵ��϶��������ˡ�����������ţ�������ڵ������¶���ʲô����OK�����İ��ᣬ�����ô��������������ʽ�ģ��Ƴ����֣���������ů������Ĺ����Ƕ�������ɴ�����棿�����滹����ʲô�������ڻ���һ�����µ����������������ѹ����ɤ�ӣ�Ԯ�����ʡ�
����������δ��ȫ������������˵����ʽ�������У��е��õ绰���е����õ绰����Ҳֻ���㲣���壬���ü��˵ġ���
������ȫ���ǵ�Ӱ�ϵ����ס�������Ӷ�������Ӱ�����ɷ����ǹ�������������
����������Ǯ���Ǻ������ģ������зݣ����˶������̾ơ���Һȵþƺ����ȣ��Զ������Ӱͽ���������ö���ϣ���������Լ�ȥ�����Խ�����̡�
����������������ϡ��������ò���һ��Сʱ�������Сʱ������Ҫ���������ˡ���ֹ�����������Ƿ�ױ������������
����������������ʲô����һ�ݹ���Ҳ�Ƕ���н�ʵĺü����ɡ�
�����뵽�������������ճ�һ�ɻ������Ƶġ�һ���ů�����Լ�ƽ���˲���������
������ʵ�ϣ����ǵ�������֫��������֫ĩ�˵��ֽ��Լ�¶����������沱�������Ѷ��ˡ�ÿ�κ���һ��Ϯ���㷢��һ���̰�Ķ�ʹ������������ʵ����ᵽ����εõ����Ƶġ���ζ�ˡ�
���������е�ѩ�������ڱ�ǻ�����������������β������Ƿ�������ʹ����֮���飬��ľ���о��·��Ҫ��Ϣһ�㡣
�����ߵ��ˡ��峿�ij������Ʋ㣬������Ů��ϼ���������¡�
����������Ӱ���Ծ���ء�ڷ�ѩ��ԭ�ϡ�
����ԭ���Ǹ��Ƶ�ֻ��һ��������������ƣ���������ʲô����վ�������˵�üë�۽��϶��ѽ���˪ѩ����Ƥ�촽Ҳ����������ϣ�˵�������������ѡ��˿̣�����գ����˪ѩ��Ө���۽ޣ������������������û���ˡ���ʵҪ˵�ģ�����������ȫ���ס�
�������������ҵ�һ�����£��±߰��������Ȼ�����ܡ����������������ȡů�����˺ô�ʹ�Ž�ֱ����ʹ�����֣����ڵ������̣�����һ�����о��ö��ˡ�������Щ��֦������ȡů�ģ���ѩ̫������ż�ʹ�ҵ�Ҳ��ʪ�����ң��ڹ��컯�����������ɴ�������˱����ֵļ��ʡ�
����С���������촽˵����ʱ�͡��������ҵģ�����·�����ߣ����С�������
�����������յġ������뱻ץ���ɣ����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