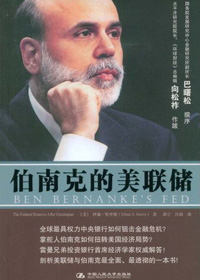̨�������������� ����:������-��30����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һ�����ݵġ������ġ���ʱ���Է���
���������ˡ�
������һͬ�������ѣ����ϴ�֣��߽���Ⱥ���Ȳ��������ľ�Ĭ���أ��ڵ���ľ��������һƳ˽�ܵ�����
����Ȼ��ͷ�һ���Ĵ�ɢ�ˡ�
�����ؼ�ô�����ţ��ؼҡ��ص���һ�����ӣ��������ӣ�һ����ģ�ϴ�ģ��ճ��ģ��̶��ģ����õģ���Ϣ֮�����ص���һ���������ߡ���������˵ʲô�ˡ��������������ϴ���˯����
�������������۳ɰ���һ�㡢�ٻ����Ĵ����ϣ���������һ��ұ������֮�С��н��еĴ�ֻ�������ĺ�ˮ���������۵糸���г���
������ͬ�����ӣ���ͬ����������ͬ�ķ��䡣��ͬ�ij��У��ͱ������Ŵ�֮��ͬ�ȵ�������
�������У�Ҳ��û�С�
�������������������Ӹ��ϣ�����;��ƣ���г���˯ȥ��
������������������������������������������������������������������
�����峿�ꡣ��������һС�ε�����
���������ϰ�ʱ�֣�������һվ���ڳ��У����Բ�����ӵ������˳�������˳�������������һ·ҡ���ţ����������Ħ��ײ�������ʯ��һ���ڰ��ڵ������м�ʻ��
���������ţ��۹ⲻ�������ض��ų���β���Ǹ����ˡ���ʱ���ǿտ����š�
����������̫���ˣ�������������Լ�����һ��֮ϸ�ڶ���ȫ����ӰƬ������������
����̫���ˡ����е��Լ������ƺ��������������建���س�������ij��ֻ������ȴ������ס�վ���ŵ��������Ͽ�ȥ��
������̧��խȹ�µ�С�ȣ������ϥ��ʮ�����ݵ�һ���ӱ���������ӵ�����֮�䣬���ɵ��ع���Ħ������������Ҳ�������ؿ����ˡ����ӵ��ػ���
�����������ۣ����ų������ɵĻζ�����������Ĵ�Ϣ��
�����г��Ծ��ں�¡��ҡ���У����ʯ����ڰ��ڵ������м���ǰ�С�ͻȻ�����ἱ��ɷ��������һ���ۣ���վ�ˣ��ֻ�������������������̤����̨��������ȥ��
����������������������������������������������������������������
��������Ľ�˵��һ�꣬������͡�
�����ո���̸����ɢ�г���һ�������˼����Ҳ�����й������Ĺ��롣
����������ô�����ҿ��ǿ�������Сʱ���ڵ�ͷ���˯������������ʼ���ҽ���Ȼ�����������Ƭ��
�����㲻ס����õꣿ��ס�ģ�������̸������һ������Ľ������ã���һ̸˳�����͵���λҲ���Ŷ��ˡ�����������û�뵽������������ùݣ����ں������л��ɵ�Ʒζ�ˡ�
����������ร���û�뵽�����������ζ����ˮ������ȫȻ���ƵĿ���������������ʵҲ������������ʵģ����ڻع�ͷ�����롭��
���������������������⣺���˵ģ�˽�µġ�����
����������������������������������������������������������������������
���������������ùݷ��š����³��ֵ��Ǿ��������ġ��ռŵġ���Ȼһ�µģ���ͷһ�ش��ź�ͬ��ĮȻ�ķ��䡣
������Ь�����࣬ϴ�裬������
����Ť�����ӡ�
�������Ϻ��а�������
����ร����㣿������ԭ�������ʱ�������ߵ��Ǹ����ӣ������������й�һ������ʱ��ĶԻ��������ƺ����ĵ��൱��졣�����ھ�����������Ҳ�벻�����ˡ�����������д��һ�ݱ��棬����˵��Ҫ�����㿴ô���������е�Ȳ����ˣ��Ҷ��������������Ǹ���ɢ�г����뷨������Ȥ���ҵı�����Ҳ�����Ƶ��뷨����
�������������ˡ����˯�IJ��������𣿣������ɣ��ܲ��ܽ�������̸����̫����һ�㡣
����Ŷ�����Ҿ�ֱ˵�˰ɡ��������ģ��ҡ����Һܺá������������úܺá����ң��������б����ס�
���������䣡���������Ҹո�˵����ô���������ˡ�
������Ҫ������ҪҲû��ϵ����������ģ��Һܺá���������ˣ�ʧȥ��λ���ܿ�ϧ���벻Ҫ��ԥ��
����������ˣ���һ��û����ԥ��
�������������Ϸ��š�
�������¾�������£���֮����ͻȻ��ȷ���������ѵ�������������˵�IJ��ǡ����ҵı�����Ҳ�����Ƶ��뷨�����ܲ��ܽ�������̸���������Ҿ�ֱ˵�˰ɡ����ǿ��Խ��������뷨�ϲ���������������ܺá���������ʹ���һ�ݲݸ塣���������𣿡������㲻ͬ�⣿����Ҫ������ҪҲû��ϵ����������ģ���ܺõġ���������ˣ�ʧȥ��λ���ܿ�ϧ���벻Ҫ��ԥ����
�����ѵ�����������˵���𣿡���Խ��Խ�Ӳ�ȷ���ˡ���������˵���ǡ��������绰����
������Ȼ���ɷ�û���ˡ��绰��Ͳ�ﴫ���ı�����������ͬһ��̨�����š�
��������һ��ûһ����д��ţ��ż���Ū�ŵ�̺�ϵ���Ь��
�����ðɡ��������ˣ������ӵĿ������ˣ��ҵ�ȥ��������
�������ϵ绰�����ϴ����ж��˴���һ�е���Ϣ��������������������������������һ����������Ϣ���뷿�䡣��ռ䣬��ʱ������������
����������������������������������������������������������������
���������������ӵ�С������з���Աһ�㣬�߳����������վ�ڵ��ݿڴ����ȴ���
����˾�����ˣ���������ϳ���������
�������ܹ����ϰ�ļ��ʱ�ʣ������Ծ�����Ƕ���ʱ�ؼ�����
����˾������Ҫ�������̸�ϼ��䣬��˵�Լ��ǼӶ��������ġ�
������������ɯ��Ů������ס���������С�˾��˵��
�����ǡ���֪�����ҿ����й��Ǹ����еĵ�Ӱ��
��������ʵ���������Dz�ӰƬ�������ǼӶ����𣬶����ӱ���
�������ڳ�����ŦԼ�ֵ��Ĵ˿̣��ӱ���Ӷ���������ʲô�ֱ𣿡����������������ӵ����բ�ڰ���һ���ð�������ƺ���������������¡ʻ�������졣
������֪���𣿡��ұ��Ǹ���ʦ����������������ʦ�ʸ�Ŀ��ԡ�˾������˵��
������á�ϣ����˳��ͨ����
�������³����Ľ����ڴ�ͬʱӿ��ӿ��һ�������˳�������һ�������ǿ�������ʶ�����ˡ������ˣ�ӰƬ�������ô�����ģ�������ʱ�պ�����������������������������һͬ�����ڵ��³�վ������Ʊ��֮�ʣ����˺�����ǰһ��������λ����֮�����Ů�Ӿ������߳�Ʊ�ڣ�����һ�����档������ס�ˣ��˴������һĨ�������˱�ҴҴ�����ȥ��
�������ӴӺ����ɷ�����˭��������ʶ�İɣ��������Ҳ���ʶ��
�����ǵģ���û˵�ѡ�����ȷʵ������ʶ��
����������������������������������ij������
���������������Ķ�����ͨ�����ĵ�����ʱ�䡣�����û�Ͳ���ۿ��Ŵ���������������⣬����ҽ���תΪ���ԣ�����ȴ�������������ϵ绰�Ժ��ü�ֱ���
�������о��Լ������鼸��˵������Щ�����ˡ��������ն�籩�µIJ���תΪ����ε���ĺ���ֻ������������ʱ��������տ������С���ȫ�����Ǽ���ǰ�������ش��ַ���������ˡ�
�����������о��Ǽ����ھ�����ʱ���϶����Լ��뿪��Զ���Ѿ���ȥ�����������Ĺ�ȥ�ˡ�
�������������绰���ˣ���ʵ�㲻�������ѣ�������ǿ�㣬Ҳ�dz�ʶ��������ӭ�����ķ����ϼ���һ�棨����ʱ���DZ���ȥ�����ģ���������û���ϼ��䡣����֮������Ȼ��ʮ���ǧ������һ�����еĵ����������ˡ�������Ȼ�����ǵöԷ��������˴˵����֡�
������һ���˰ɣ���һ����ˡ�
���������������˷ɻ�ֱ�ӱ���ȥ���֣������Ͼ�������û���������űʼ��ˡ���˵��
������Ц������Ҳ�ò����Ķ�ȥ�����������ֱ���ࡣ
�������˵Ŀ��������ڽ����췢�����¡�ԭ������ס�����Ѽ�������ס��Ԣ������ͬһ����¥��
���������Ժ�һ�����쬵����磬�������ģ�Ҳ���ڽ��㣬����һͬ�߹������֣�ȥ����һ�����ȡ��س̵�ʱ���������������˶�û��ɡ��������ͷ�����ϣ���ʹ���ǵĽŲ��ӿ졣�°���˳���ʼӿ�֣���Ϊ���꣬��ȫ�������ʩ�����ּ��µ���¥��������ӵ���ļ粲�м����ߣ����߱�˵��ʲô���������ӣ����˶����Ծ��ؽ���������ˡ��ڽŲ������ƶ����˳��Ĵ�ӵ�䣬���ǵ�����Ѱ���ʵ����λ�����϶�У���Ъ��ʧȥ�ֲ���˴˱���ˮ��ʪ����ף�ע�Ӻ���Ϣ��
����������֪���ƵضԴ�ȴ�������һ�����ʺ���Ҫ��̸����
������������¡��ꡢ����Ų���ӵ�����е�һ�磬��������������ɵ��ˣ�ȴ��ô�����ء����ٵء���Ȼ�ضԴ��ţ����ֵ���һ����֪��������ѣ�������һ�����ܵİ��ˡ��ɵ�ʱ��������Щʲô�������ڿ��ȵ꽲�����ݣ�֮������ȴ���Dz������ˡ�
�����绰����˵��������������˵��ʲô������Ҳ�е����⣺��֣���ôһ�㶼�Dz������ˣ�����ʱ����û���Ͷ�����
������˵���DZ���ˮ�ͽŲ������˰ɡ��ҵľ����ǣ�һ����·һ�߽��Ļ���ʮ֮�˾Ŷ�����������
����������ʲôҪ��������Ҫ�����������л�˵�����һ�����û�ꡣ
��������ںȹ����ȵ�����֮��һ���������磬����ά���������ĵ绰��̸��ʲôҲ��Ϊ�����ǽ��������Ž��ţ�ʱ�����ô�����ˡ�����˭Ҳ����Ϊ�Ա˴���������������ʲô�ģ�����Ҳû����������Լ������ʾ����Է�Լ�����˼��
���������ŵ���ң����������ʶ��ת��̨������һ���ӣ���ʮ��̨�Ѿ�ת���������顣����֪���Լ������뿴��ʲô�������������ر��뿴ʲô��������Ҫ�ҵģ����й�����绰��̸����Ķ�����������˵���������ӻ�ʱ����һ���Լ���������Ů�˺ȿ��Ⱥ��ĵ绰����Ϊ������ʲô�����أ��������ɱ�����Ǯ��������Ūһ˫��ʵ����̫�����˶�Ь��һ��ϴ�����������е�һ�ָ�������ҡ��ݳ����ɣ����⽫�Լ�������ֻ�ᱻ����ǣ�ű����ߵ��������������������Ǹ������dz������ģ�һ���������ر����е����ĵ����ˣ�������Щ����Ҳδ�ء������dz�������Ҳ�ý���Ҳ�ã���ȴ�����⼸ͨ�绰�����ܽ������ݸ����Ĵ���������ɣ�������������Ϊ����ɣ��������漣�Ƶ��ɹ�ȥ���յĻ��ƺ;����е��Իָ�����������ʵ˵��ÿ�������������绰֮�����о������������ľ������������һ�����������ţ���������ʵ�Լ����ˡ�
���������żij�ʳ����ͷ����ɫ�Ѿ���ȫ���������������ӣ�����װ�ڲ���ƿ��īˮ��ɫ�����ִ���Ѿ������궼����ʹ�õIJ���īˮƿ�����ڣ�������īˮƿÿ���������ӱ���ֽ���Ū��ij��ơ���������ؼҵľӶࡣ��ҧ��Ѭ��ƹϼ��ڷ��������������Σ�����������Ҫ��Ҫȥ��������Ϸ��
�������Ҫ���ҿ�����Ʊ��������Ʊ��ֻҪ����������һ�췽�㡣
������д���Ǹ���̨���������ţ����������ܲ��������Ǻ켫һʱ������û˵ʲô�����²��ߣ���������ô��ȥ��Ϸ�����������ҵ��ˣ�Ϸ��ô˵Ҳû������������̨��Ȱɡ����������������һ����ȥ�������������������ԭ��������û˵Ҫ����ȥ�Բ��ԣ������Լ���д�Ķ������²����Ѿ����������ˣ������������ˣ��Ͻ�������������ӣ��÷Ž�����Ļ��������ء���������æ�Ž���һ��Ů��Ա���ȻҲ�����������ġ���֪���Ǹ�Ů���ǣ��������ݵ�һ����Ӱ���Ǹ����ˣ����ᡢ���������ġ��������˻�ġ���ȥ���������ֱ�Ť�������������ɷ��ֵľ�����ֱ������Ϸ�������£�����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