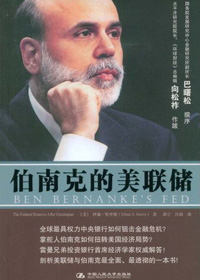̨�������������� ����:������-��2����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ط����ݶ�������ȥ��
�������ɿ�ر����˺��ţ���ԽһƬ�ϵء�һ���ķء����žɹ����Ľ�����Ժ���ܱ������﹡��Ծ��С�š��ܽ�����Сʱ����Բء�ľ�ij�����Ƭ�ѻ�����ľ�ĵĿյء����ܵ���Զ�ֿ죬�ҴӲ�֪���������һ�����ܽ���������ƴ�������������ˡ�
�����������ܽ���Ұ�������Ϸ����š������ˡ��ĸ�Բ���ơ�����ѧ��ʦ������ļ��ԶԶ�ģ���������Ӫ�������Ļƹ���������س����DZ�������ҡ��β�������ͽУ��߲�ס����Ҿ���ݰݡ���
��������ҹ���շת���ߣ���ôҲ�㲻�����յ˵ĵ���������ʲô���Ҳ�ס����˼������ͼ�ѵ����ĽǶȰ���������һ���ػ��룬�Ծɲ���Ҫ�졣������Σ����������Ǹ����ɣ����ͬ˭Ҳ�������𣬰����������ڡ�
����ȴ�dz��ڲ�����ԭ���Ҿ������ܾ������ޣ����ϰ�ҹ������߳���˯���л�Ϊһ̸�ˡ������У��·���������ҹ�ﲻѰ����������졣һ�ȼ������ѹ�����һ����������������������������а�������������һ��ϸ�������Ŀڼ��ҵؿ����š�
����Ҳ��������ֻ�Ǹ������ֻ��ҵ��ξ�����ij�ּ�Ϊ��Ϥ�Ŀ־����ʹȴ������ʵ����ʹ����һ�������Ҳ�ر��������
�������룬�dz���������ֹ���ķ����������Լ��ǵ����ˡ������ߣ���ʹ�Ϳ־����Թ��ߵĽǶȣ�����ʵ�ػû����̶��γ�һ�ֳ����ġ������ġ����ѹ�ȡ���������������ӡ����á����������Ȼ���ս���Ļ��棻�Ҳ�����Ԥı�����ǹ����������������������õص������·��ķ��ա��������亹��ս�������ſ־����Ű���о�������һ��������繽�������
�����������ξ���ֵس����ţ�ʱ��ʱɧ�����ҡ�ֱ�����������ûͷû�ԡ����ص��Ȼ��ֹ��
��������������������������������������������������������������
����������÷�꼾���������꣬���ڸ�һ���䡣ÿ��̫�����Ű��Ȼ���ǿ�����մ�ء�����һ���峺��һ���������μ���ʬ����ˮ��Ⱦ��С�ӣ��ڴ��귺��֮���ֹԹԻص�ԭ�еĺӴ�����һ�����������˵Ķ������һͣ���˽���Ԣ���õĹ���������ð��ͷ�����Ҽ�Ҳβ������ɺ�������ʼ���ô���ˡ�
���������һ����������ʱ����������ҧ���������˹�����������С������Ľ���������Щ��沢ռ�õ�Ŭ�����������һ����ʵʵԼ�߰�ʮƺ��С���õء�
����һ�����ȵ���������ܲ�ס������ʪ�ƿ������ϱգ������������Զ���ѧ��ֵ��˳��һ����ǣ����ڹ�С������������֮�����ڱ�ҵ�����Ҵ��Ͼ��������������ı㳵��˳�����ϸ���һ���ĸ�ʢ���Ĺ��С���Ȼ�ҵ�ѧϰ��δ��������ѧ������ת���ϰּ�֪�Ҳ��ǿ������ϣ���Ҳ�״���Ҳ����ͬ�����ˡ������д�ľͷ������������������ģ���ľͷҲ������ǽ��ƴ����һ����ҽѧԺ���������վ����ǰ��ڿڳ�ľګ��ֻ��������ʬ���ʵĹ���һ���֮Ϊ����ѧ�ң��������ϰ�����ǰ̧ͷͦ�������Ķ�ʮ�ꡣ������ʱ��ʱ�Զ��ṩ������ɻ�Э���Եķ����������Ҫ�ұ��и�־����Ը�������ɳ��˵���������һ����ᣬ���������ҵ�ѹ������ؼ����ˡ�
������˵���������ܲ��˽�����������˼���ϣ�����һ�����Ҿ���Ϯ���IJ���������ص����������������ϯ�ϼ��£����Ż�����ͷһ�������˱����������½���������Ե�״ɫ���������Ѿò���������Ӵ��������壬��������������һ��Ů�ˡ��˿̣�����ҵ�Ѳ�ȥ��룬�ϱߵĹ�ͷ��������ͽ�ܣ���ϲ���̵ؽ�����������˳���ۼ۹��ʶ���õ��ʹ͡�
������һ��ʮ������к����ԣ�����ʲô��ĸ�׳����������壬��Ϊ�ɳܣ�����ʱ֮�䣬�Ұֵ�ҹ��ɻ�ۼҵ���������ľͷ����ľͷ���ϵ���ɵ����������ʮ��������Ϲ�һ�Ĵ��������㲻��ʲô�ˡ�
�����һŰܵ��ӳ����ţ���һ��������ͷ�Ŀ����������˽���ʮ��֮һ��̨���У�������һ�����õ����������š����Ž�ӹ������С˵��ȴȫ���Ķ���������������������ǰ����Ҷ�ҵı��ޣ����Ǹ����յ������ַ���������������������������ܽ���Ұ���������Ĺ⾰��
������ʱ����ѧУ�Ķ�ͯ����ɢ����ֻ�ж��Ҽ�������ͬ�����ݹ��ϻƣ��ڶ����Ӳ�Ұ��������ʲ���Ժ���������������Ƕ�ʮ�ָ��ˣ����ϻ�ͬ�����������ǹ�ȥһ�������ľͷ�ˡ���èè֮�����Ϸ��
������Ҷ��н����ֵģ�Ω��������һʱ������������״������������ͨͨ�ģ�ת������һ��Ŵ����ϣ���ͷ�����������ţ�һ����������ľͷ�ˣ��������ÿ켫�ˣ��ּ���Ѹ�ٵ�ת��ͷ����ÿ�������˲������IJ��ȣ����ǻ��ڶ�������һ�ָ�Է���Ƥ��˭˭˭�ĽŸ�����Ӧ�ó���֮�ࡣ������ú����������ҵ����ۻ�Ц�ü���������������������ù��˷֣�û�ȿںź����ع�ͷ�����������������أ��������Ц����������ȴ˵Ҫ�ϲ�����ͷҲ���ص����ˣ����ö�������Ӱ��
����һ����ˮ�Ŀյ�����վ�����ⴰ�ڣ�˳�ƽ������ڱ����Ĵ������ϣ�δ�룬��������������Щ�谵�����ڡ�������������̬�����ó��档�ҳ����ţ�������̲�ס�����ò�����������̧����������˵������������ء�
������������������ֱ������������ȥ����û���ϣ��Թ���������ڡ����ʼ�ª��������������������ݵĵط������°����Ǽ�������Ϸ��٣����ֵ�ľ�Ƿ��Ŷ۶۵���⡣
����ÿ������������磬������������ǰ���ߵ��ߴ����dz�����Ү��ϲ�����ϵ�С�����������е�С�������ۺ�ƺڰ��֣���ΪҮ����ϲ����Ү��ϲ���������е�С����
��������Ǿ����һ���߰���ȥ����һ���ܵ����ٵļ�Խ��
���������ĺ��Ӷ����ˣ����ڰ�����������轲ʥ�����£�һͬ�質���������о��ġ�Ȼ����ȡ��������ӡ�ƾ����Ŀ�Ƭ������Ҷ�ҵ�����Ů�����Һ�������磬����ס�����ȵġ�������ġ���У���ϴ���Ժ�ģ������������еĺ��Ӷ������ˡ������賣�괩��ӡ�����ij�ȹ�������ֽ̻�ȼõ��������ѣ������ﲿ�ɽ�̤������������ȥ��ɹ�úںڵ�Ƥ��������������˵ļ���ˬ�ʣ����˱�¶������Ц�ݺ�һ�ڽ�����ݡ�ʵ�ںܽӽ���������Ψһһ�����Ƭ������һ�������Ǹ��ܸ���ʵ�ĸ�Ů����
�����������˵��ɷ�פ�������С��ص��ң����ǽ��Ӵ��������������С�ķ����о����ϣ����������ĺ�����˯�����Ǵ��ųಲ������̨��ε�����ʣ��������ݶ���©����ƶ������������ˣ����ֻ������۰��������Ų�������������ͳ�ɳ�Ƶ�ɤ��װ�ɹ���ģ��ͬ���Ƕ�Ȥ��ʥ����ʱ���������ʥ���Ϲ����������Ƿ����ǹ���
���������뵽����ҷ����Լ����ɣ�����һ��ϴ�ӹ�������¡��˼�Ҳ���������һƹ�ֻ�Ե����������ʣ��������ô�ţ��˼�Ҳ�����Ҹ�ĸ������
������������һֱ�浽��������������˴�����ٶ�����������ʱ���������гԷ��ˡ�
�������������ǽ����ƹⰵ����С���Χ�����¡������������ڣ����Һ�����Ϊ��ٲ�ͬ���������������˸߲��ҡ���ʹֻ������С�ˣ�С�㱬���ɣ��峴���IJˣ�һ��ײ˶��������ر�����������ֱ���ø�ˢ��ˮû�����������dzԵ����㡣����������С���ֳ���Ц���ò����ġ���͵�۳�һ�±��ޣ���ʮ�����ݵĹ����£������������Ǹ���Ů����ģ���ˡ�����������ָе�һ�����������й�˵���������ᣬ�����ؿ����Ƶģ�ֻ��һζ��ͷ�Ƿ��������Һ��Ӱѱ���û�����ʣ�����ϰײ�����
�����ǹ����ѵ���һ�ߣ�צ���̲�ס�������ţ�һ���ݹǸ��������졣һ����������������������¶�ȥ��
���������Һͱ���һֱ�����Ҵ��������������̻���ҹ���顣
���������Ǹ��յ˵ģ����ٲ�������������������֮�䣬Ҳ���Ǵ�����һ����ͨ������Ĭ���ɡ�
����ֻһ���ӣ����Ƕ������ˡ���ʱ������������һ�վ��ӣ��Լ�������һ�������Ҿ�Ȼ����һ�Ž����ϰ����������˵����ӡ�ʱ������һ�����裬�·����ӿ�ֵĺ����Ʋ㣬��֪��ʱ��Ʈ�����ˣ������ؽ����������ϰ�����������
������Щʱ��ʱ���ῴ�����ޣ����ѳ���һ��ϸ���������Σ���ѧŮ���涨��ֱֱ����̷��ǵ�ûʹ��ʧ����ɣ������������д�����������Խ���������������Ͷ�һ��˽���ļ���ѧУ��ֻ����ĩ�Żص������������������ѧУ������һ��������ȹ����ϥ�İ�ɫ���ࡣ��֪Ϊʲô����������Ҿ���Щ�Բ��λ࣬�����������㿪���������ڴ�����������û���⣬���Ǽ���ÿ����ĩ���磬�Ҷ���ʱ����������
���������ô�ʲôʱ��ʼ�����Dz��ٸ��Է�˵���ˡ���ʹ������������������к���������ô����һ�ۣ�����ǣ������ǣ�����Ц�ɡ���ʱ������������ı�ʾ��Ҳ��һ����ȥ�������Ӷ������أ��ҴҲ���������
�������������θ����϶�תȥ����һ��˽У������֮���ҾͲ��õ����ˡ�
����������������������������������������������������������������
���������������£��Ҳ������������ϰֵ�ҹ��Ӫ�������������������ľ��棬��ǹƥ�����˼�Ʊ�����ղ�����ͷ��˯���㵽ѧУȥ�������ӣ����������������档�ҽ����ջ�շת������Ǯ�ƣ�ȫ�������ؾ����˼��������Ĵ�ľͷ��������Ϊͬ����ʧ���IJ�����
�������鷢����ռ�ط粨���á�һ�գ��ò����ŵ���ɩͻȻ��ݹ��٣����������̽�ſ����������֪����ľͷ���������������¡�
�������������ۣ�һ����ڹ���ͤվ�ڵ�ֽ����һ��������Һ������ҡ���������ʲô�Ƶģ���һ˫ֱ��㶵ǵ��۳����˲��ţ������Ȼ�����ˣ����û�������ƽ�������ij������Ҵ���ү�ǹ��ӳ��������ɲ��ܲ��ܹ��ˣ����˳Բ����ۡ����漴�ݸ�����һ����ľͷ�ּ������š�
���������ϴ�ľͷ����һ�ٺ���Ұ�˵��Ҫ����ô�������۵ش��ɣ��ͰѴ�ѧ�����������š�һ������Ÿɻ����ȥ���Ұֿ���˵�������ġ����¾�����ɩ�Ĵ�����������������ַ��������ֵ��̸�۵�Ц�����ȱ���̫�õĴ��Ը����������˿ڡ�
����δ����Ҷ�ұ���������߸ߵ�Χǽ�ˡ�
���������Ҫ�����ʱ�������Ƿ������ҵΪ�����ޣ������ò�ƴ��С������ҹս���ڼ�ֻ�ɶ����Ƶ���ʮ�����ݵ��¸�д��С�������������ռǺ�����Ӣ����ѧ����ɫ����δ���������ڲ�֧ſ������˯���ˡ���˯�ü������ȣ���������ԶԶ��������˻�����С�
������Ȼ���ұ�_���������ĽŲ����ѣ���æ���˷��ţ������Ұֽ������������Ŵ���һƨ�������ڴ����ϡ���������һҹδ�����ۣ���ɫ�Ұܣ�����Ѫ˿�����������ӡ�
���������������������ˡ��ŵ�����ͨ��ͨ�����������Ͼ����������ҡ��ѳ�������֤�����˫�ַ�����һ��������ס���Ҽ����ⶼ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