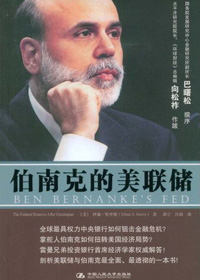̨�������������� ����:������-��15����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ܡ�����˵����ų���ū����ʵҲûʲô���߳ܵġ�
�������й�����������ϣ���ʱʧȥ�ô��κ�һ�����ӵ�������
����δ�������Ҵ�����Ϊ��殽����ס�����˵�����ѧ��ǩ֤�Ѿ������ˣ�����Ҫһ������ǩ֤��������ǷǷ�������
������段��ͷ��
�����㲻����Ҫ����ǩ֤����Ҫ�зݹ������ø���ס��
����������ɷ��ϵص���ͷ��
�������⣬�����ϻ���Ҫ�е���Ǯ������
������������룬�����治�������������꣬�ⶼ�Ǿ���̸֮��
����������ݸ���һ���ţ�˵����������ŵ������ȥ��֤�����ҵ�һ�����������Ĺ����������������������������������ջ�۲����ڽ��еĺ��ִ��������������������ѧ�йأ��ٷ�֮�����ǻ���㹤��ǩ֤��������Ҳ���õ���ʵϰǩ֤��
��������ֻҪ��Ը�⡪�����ó�Ǯ���Ҹ���ʦ�����̿������������ˡ����⣬���ҷݰ��칤����ͷ�ϾͲ���û����Ǯ�ˡ�
�������ǣ����˵���˼ҡ����������Ѿ�����ȥ̸�����Σ��Ҿ�������ϣ���ģ��������棬������Ҳ��������
�����˼��Ѿ�û����ȥ���
���������˼�Ҳû�лؾ��Ұ���
����������˵���Ǹ����ִ������������ܣ�����殾����������ִ�����Ӭ��
����������Ӭ������롣С�㣬�����Ѱɡ�������һ��С�������ߵ�ְ��Ӧ�����˶����ء������ܲ������Լ������˲��ã���ȥ�Ҹ�ĸ�ﲻ��Ӣ�ĵ�����д��ɡ������Ǹ��������ļһ�㲻��������������������
������������ر���ţ��Dz�Ӭ��
�����о��Լ����ѽ��ʵʵ����һ���������ȫû�����ӵ���ء������������춼û�п��ܡ���֪�����һ���ô˵������Ҫ����ŦԼ���ͱ��븶�����ۡ����������ܳԹ�ס������û���Ŷ��𣿡����������
����������ǰ��殻��Dz������䣬����ǰ��ͬѧ��绰ʱ��˵����ʵ���������ġ��㿴�������������ݹ���������������ѵ����֣�������ס�������ջ�Ү��һ�������ĸ����ϵ��ݵ���λ��
���������ô�ţ����Ҳ�����ʼǮ�ˣ���Ū��һ������ǩ֤�ء�����殴��Ǽ��ձ��ݾ��������ֿڵĹսǴ���������Χ������λ������˹��º��ѣ���������˾ơ����˲������Ӳ����Ʒ��⣬������Ů����ȥ��Զ�����������ź�����¡���λô��Ҳֻ��Ů�̸���ôһ��㡣���ÿ�ܶ�ʮ��Сʱ������Ѥ���ĺͷ��������Ǻͷ���һ���Ҫ��ȥ������һСʱ���ѵ�ʱ�䡣
������һ���ϰ࣬һ���ձ���̫������������ν���Ѳ������Ķ���ϵ���������������������������һֻ���ӡ�������֮����������������������������绨��Ц�̣������ڻ��Ƴ��ϵ��ջ��ˣ�����ƽ�����������ϵĸ���֧����
�����������������ڿտյ���������֮��Ҳ����������Ŵ̼�����һ����㹻�������ѵ�������İ��ͼ�����û�µ�ʱ�������洦�ҹ䡣���������ٲ����ģ��Ƕ�붼�Ǹ�����һ���������ջ�ȵ��������ļ�ֵ��ֵ�ÿ������չ��Щʲô�������á�
�������һ�˵���¿�����ˣ�ʲô����չ����ȥ���ģ���ԭ����һ��ټ��Ŀռ䣬Ư���ĵذ�����������һ�ζη�����ͭ�������У����ѵ���̡�
�������˵���Ҿ��û������ء�
��������ר��������ЩСëͷ�ġ����Ҳ�м��˵��
�����й�һ�����糵��Ŀշ�����ͷ����һ�кд�ľ�䣬��ľ���г���һ����շ���ѿ����������Ʒ���ֽ��������족��
����ร�ԭ�������Ķ����������������ú��������棺�ѹ֣�����Ҳ����Ů�˳��˻���Ǯ��������֮�⣬��ֻ����磬what��a��copycat�����ţ�������С������������������������͵Ĵ�붼��ʱ�����е�cutting����edge�����ȴû��ô�����Ȥ�����ּ���������ʱ���ϼ����Ҫ��ȥ��¼��������õ��ַdz�֮�٣��еĻ��ر������Ͷ��ġ�
������������ȥ����ꡢ���ߵꡢ�Ҿߵꡢ�Ŷ��ꡢ�ֹ��վ�Ʒ�ꡢ���ߵꡢ��������ߵ�ȡ�ʵ�ں��п�ͷ����Ʒ���������ʱ����壨��������������Ϊ��װ���������ջ�ߴ����Ŀⷿ�����У��ݶ������������λεĴ�ƻ����ƣ���ʹ���վ�ͨ���ţ���ֱ����һ���ʱ����������Ļ�������̨��
��������֮�⣬�����Ǹ������δ�һ��������ӰԺ�ij��͡�һ�����ٹ��һ�Σ�����ר������ŷ����������Ƭ�����ŵ�Ӱһ��ţ�ֻ��һ��ƱǮ�����һ����ۼ�Ʊ�������Ƕ����˼������иߴ�ظ��������Ρ���������ᡢ����³����˵�Ƭ�ӡ�Ӱ����������������ı�Ե���࣬����ֹ��ס���롢��˼�;�ϲ������ϷԺ��ƮƮȻ�������ǰ����������µ���·�ϣ���ֱ���Լ��������������Ǹ���ʵ��������磬ֻ����������������硣
������ʵ���������ǰ����Щ������ֻ����ʱ·��������̨Ӧ���ܸ����ġ�Ψ������Ļ������̨���߽����ϷԺ���߽�����������Ӱ��֮�У��Լ��ص����Ǹ���С�Ŀռ䣬���������������ŵ�ʱ�����һ��Լ������˹�����
����������ʱ����Ҳ����û�����ɿ������һ����ٽֵ��Ǽ������Ӣ�߿�����Ӣ�߸ߣ������ľ�Ĵ���վ�ڴ��ߣ����Ը��ܵ��ⶰΰ�����ĸ���ʷ��սǰ���������Ļ�ϲ���Խ��ǣ���Ҳ�Ǻ�ש�Ĵ�¥��ͬ��¥���ס��һ�������ۺ촽��Ů�����������ѣ�������һĻĻ�����ƾ磬��һ�洰��������һ�����ڡ�һ�����ǣ�һ��������һ����������������ڳԷ��ˣ�ҹ�����ҵ��𣻴γ����������ʻ��Ϸ�硣
���������ֵĶ����¥���ʾɻ��Ŷ����ӡ����ϲ��վ�ڴ��¶���������һֻ���ŵij�������ɫ���㣬��Զվ���ſ�ӭ�ӹ˿͡�һ���꣬��һ�ۿ����ľ����Լ���������������Ǯ��Ҳȥ�Ƕ��������ɹŶ��¡�Ƥ����ñ�ӡ����鱦��С���Ρ��̻Ҹף�����ʹ�����̣����ȵȡ�¥���Ǽ���ͬ�������ȣ���չ���ƻ��ʱ���������������ӰƬ���ͬ�����ɶԡ����Һ�������Ҳ�̲�ס�����ƣ��������ߣ�ָָ��㡣��һ�Զ���ұ���ӣ�����Ʊ���˦��ͷȥ�����Ц�����¸߰��������ھ�ұ��������������֮�䡣
�������һ��ҵ��ⶰ¥���и���ʵ�����ֵı��ݿռ䣬���С���������һ�����࣬����¥�����ƵIJ�ס����������������ͷ������ɶ��Ҳ�ɲ���ȥ����˷������Ʊ�����е�ס���˼ҡ�ֻҪ��û�Ű࣬���һ����ȥ��������ʱû�գ������Լ�ȥ��һ�ο�����Iaurie��Anderson����ʱ����û����������������������������̫��㽻����У���ʱ�������еĴ�����ƽ�մ����Ϸ�磬���Ǻõò����ˡ�������һ�Σ�ӡ�������ȴ���������ҵ����֡���Լ��ʮ�����˰ɣ�һ���İ��ƣ�����žž�������ij������Ƶ����ɽ��࣬���ƶ�����һ�°ڶ�������к�����ҡҷ�������赸��
����ÿ�ο�����ݻ��������������Ǵ���������ϴȥһ����ij���������һ�ᵹ��С�����ϣ�¥�ϴ����������������š���챼�ŵĵ��ӣ������ֻҪ���˿ͣ������������ط��������ڻ������ˣ��������ֱ���ͷ������������ϲ����ķ�ζ��ϴ��������Ϣ������ƻ����롣������������̹�����ţ������µ��ؿ����ý������¡���һ�̣��������е���Թ�ڣ�ֻҪ����ŦԼ����һ���ƺ���ֵ�ˡ�
������������ʱ�����˱�Bukowski���飬û��ʱ�㿴��һ�Ρ�����Ͼƹ�ʫ����һ���������ϼһ��ּǡ�������ר��������־д�ƹ�����Ů�����˺�������б�Ե�˵������ּǡ�����У��쭵û�죬��������ʫ��Ҳ���ǵ����в����������ˣ��ܵ¡���Ե���Ƿϵ�һ���ɵֵ��������ɡ�
������������������������������������������������������������������
���������������밢�ͬסһ��С�ӱ��ϡ�����һ������ᴩ��������ũ��Ұ�أ����������������С��һͬ�������۹������˼ҵ�С�ӹ�����
������段��ϰ֣��Ǹ��Ź���������̨������ѧ����ƾ��һֽʦ����ѧ����ҵ֤���ߵȼ춨���Ե��ʸ���С�ӵ��ס���Ұ��İ����������Сѧ��У����
����С���νӴ���·�ڣ��л�ר������������˼ң����ڽ���һ���ģ��С�IJ���������ˮ����ÿ���糿���ܿ�����������ǿ׳�Ĺ��ˣ���һ����ɿ�ɶ��ī��ɫ������ˮƿ�����ˮ����ϴ��
�������������ϸխ��ľ������dz��ɫ�ᣬ�м���ɫ������д��һ�����ġ������֣������Ǵ�����İ�ɫ���㣬�϶˻�������״˪ѩ�ᾧ��ͼ�����������ģ�����������Ƕ���·��Ŀ��Ľ��㡣��ʹ��ô�����ȥ�����ԭʼ������ͼ�ڰ��ʼ�ղ���������
����������խ�ű��ϣ�ÿһ���ļ����ļ���ÿһ���������Ȳ��ɵ����������һ����ڽ�׳�����ż��������ӣ��·�������Ԣ�Ե����䡪������һ����Ť���ļ��⣬��������ںӱߣ�ǰ��ʹ���������λεĴ�⡣��ɫ��м����ĭ��������������ݵĻζ�������һ����ɢ��������������ɢ��������ãã�ı�����������ʱ���ܻ���һȦ������Χ£�����������������������Ĵ�⿴ֱ���ۣ�Ҳ�������Ǹ���û�������������������ֵ���������ı��ˡ����Dz��������ɢ�ı�м���У��������̵���ʲô���һ����С����æ������������Լ���������ϻ���¼�ʰ������������������̳������ε�͵Ц��
�����������ⷬ������ˮ��ϴ��ˮƿ�ľ���Ҳ�ͳ��˵���˵������˽������ǵ��Ӿ�������
����������·���������������⼹�������˷����˴�⣬������ˮ�����ٹ������꣬�����ˮ��������С�����ⲿ�ֵ�ס������أ���ʼ������ľ����¥�����Ӵ˸����������˵�¥��������������������ȿ�ʼ����һ����Ρ��������Ľ������ͼ���壬�����ڿ���һ��������ϣ�������ڸ�������ţ�����鿴���ϵ�����¥������˿ͣ����Ƚɿ���ݵľ�Ӫ��ʽ���ۡ���ˣ��ڶ̶�ʱ��֮�ڱ��ۻ��˾�IJƸ���
��������ʱ�𣬰����е�����һ·��ҡֱ�ϣ��������꣬����˵��ص���֮һ�����ﳤ������Ա��������ǧ��Ƶľ��ѡ������������������һ���������������������ģ���ˡ�
�����Ǹ�����İ����в��DZ��ˣ������ǰ��ҵ��ϰ֡�
�������������ĵ�ҹ������殻���ͬС�����ˣ����Ż���С���ͳ�������İ���·�棬ȥ�������еĵ�������Ŷӵ����������С������ֵ���խ��ǰ�����һ��������������שͷ��С�ı��顣�������е�������ȥ���ǵ�һԪ����ǣ��ֽ���������һ���������ʵʵ�İѱ�˩�ã�������һ·�����Żؼҡ���ʹ�������˵��Ϊ��ˬ����ҹ����¶�����ʹ��������ܻ���һ·�εδ��梵������ᄀ������ϲ�ã�����ȴ����֨��������˵�䡰������㣬����Ҫ���ˡ���
����·���˼����Ƶ����ﴫ������������ӵ����죬��ͬ��Ŀ�ķ��������Ų�ͬ�ļ��ᡣө����ںں�����·�߲ݴ��ﻮ��������Ծ�����ߡ�梵������ܵ�����δ��ѹ�����Ų�Խ���ļ���������
�������û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