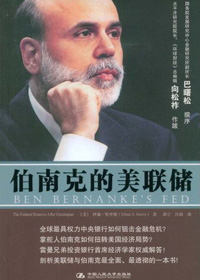̨�������������� ����:������-��1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Ҫ��������ѡ����Ͼ������İ�ҹ��������������峿��
�������ں췢������Լ�˵����Ϊͷ���Ѿ��ɾ�ҩ�ذ��ˣ�ֻ�ý�֮Ⱦɫ��Ϊ����ѡ���ʺ��Լ���Ⱦ������������һ���ԣ������������鵽��������������졣
����Ӧ�û���������ô��ɡ������ָ�ͷ��б�����������˸��������ĵı��顣
���������������й��DZߡ��˺ӽֿڵ�һ��㶫��ʳ�������һ�����������ظ��������ҴӲ��Լ��շ������������ҵij�����
��������������̳��ֲ�м��������ҵı��顣����ȴ����ΪȻ��˵�ˣ�С�㣬�������ŦԼ��������ϰ��ŦԼ�Ժ��֪��ʲô��������ࡱ�ա�
��������ס�������³ǵ��ջ�������ν���ջs0HO��������Houston�������ϣ��˺ӽ֣����й��ǣ����Ա��Ǽ����������̴��۽ֵ���С�����Ƕ�ԭ���Ƕѻ��ֿ�������ߡ�����Խ�����������ֳ��εΪ�����������������뻭�ȵľۼ��ء���չ������������ǰ��������ŦԼ�ķdz��ضΡ���Щ����������ǰ������֮���ͣ����˺�Щ�������IJ������ƹݡ����ε꣬���������ùݶ����������ˡ��Ƚ��й�����С����������뻪�����Զ�������ĵ���λ�ü��ϵ��������ĺ��٣�ʹ���ջ���Ȼ��Ϊ����֪���ľ��㡣
����һ����ĩ����ֱ���Ƕ����������ҹ������˵�˵������������һЦ���������ز�����������˺ü��ɡ���������������л��ҵ����á���Ϊ���й��ǽ�������ˡ��Է�����������������·�͵���
���������Լ���ÿ�������������㵽�˳Է��ò裬�Ķ����ı��¡�
������Լ��ͬ�ģ����м��������Ļ��ҹ������������졣Ҫ������������ȴ�绰���������ﻹ���á�������˵ĵ��ء���ƴ�����ߺ�ȡ���������������ꡢǽ�����������IJ˵������IJ���үͼ��ȸ�ʽ���������ȫ�Ǵ��й�ʽ�ġ��ڴ�Ҽ���ȫ�������˵�������̬���У��̶ܹ���������ôһ���й�����ʽ�ı�����Ҳ�����������������е�����ˡ�
�������ǰ�殡�����Сʱ����ھӡ���ô�����й��ΰɣ����������������Ŀ����������ܸ��Լ��ǰﻭ�����ѣ���֮����������Ͼ䣺һ������ǻ��������ء�
����ĩ��ȴ�������������������ҪС�ı������ˡ�
�����������Σ����������ǰ�����Χ�Ƶģ��˼һ��������������֮�������������ڵ��������ú�����������ƨ����ý����������ǻ�չ��ù�Ѫ��ͷ��ʱ����Ī������
������ʹ��һʱ֮�����������������ɳ��������ǰٿ�Ī�磬�Լ���������ʲô���������ء���ֱ������Ҫ��ô���������˷�����ʽ��Ů����һ��ӿ�ϵĴ���Ŀ�⡣
�������ϰ�殾�˯�ڰ��һ��Ҹ����һ��С��λ�ϡ�
������ط�������Ԥ�������������õģ���ʱ���������ˣ��������ȥ����ô����һ�¡����������ˡ���
��������̧̧�°ͣ���٬�������һ���Լ��ϲ�������䣺Ҳֻ�����������Ƕ������ˡ�
�����DZ��飬�����ǹ����������ǻ��������Ĵٳ��Ƶġ�
�����������ˣ��Ǹ���̫С�ӣ����ĵ������������ǹ�����ţ�п��ԲԲ���̵�ƨ�ɣ�һ�Գ��Ƚ�ʵͦ�Σ�����·�����ɶ�ֹ������עĿ��ֻ��һͷ��ëС����ǧ�����Ƶģ������²���һ�Ի�ɢ�ĵ�ɫ���ۡ�
���������Ӱ�殿ɲ���ΪȻ�ˣ�����ô����ô���һ��
��������ȴֻ����˵�����˿ɲ���ò�ࡣ��˵��ŦԼ�����˼���̫�˵ĵظ��ȡ�
����������������Ҳ����������ȫ������̫���Ӱ���
�����ã�����־�����ҵ��ǿ����㽫���ɸ�ʲô���ӣ������Ҳ�����������һ�ڡ�
��������ҹ������ֹ�Ȼ�����ˡ��Խֵĵƹ����ǽ��Ĵ�ӳ�ս����������������ڣ�ȴ���������������������ϲ���կ��庼���¥�岻�Ͽ�֨�죬������ͷ�����˲�������Ƶ��������ס���ź���̸Ц�ء�һ���ƺ����˴��������������ȵ�¥������һ��֨�죬�Ų���ȴ�·��������Լ��������
������殰���һ�����ã�����һ���첽�Ѿ����˴�ǰ����ֻëצ��һ��������������������������𡣵���ʱ�����ˡ�
����һ����ͷɢ����ԭʼҰ�����ġ�ë�ԴԳ�����Ļ�ë���˾���ô���ڸ�ǰ����ͷ�İ���ͻȻɢ��һ����٬��Ц�ˡ�
���������ﹾ��һ��ʲô���漴һ����������ǰȥ��������Щײ�ϰ�段�ͷ����ë�ּ��̴����������ͷ������һ�����������漴����һ��л�֡����������Ӱ��δ���壬�˾��Ѿ������ˡ�
������ͷ�İ���Ц�������£�����ȥ�ұ����ġ�
���������糿������ʵ�����ǹ����ˣ�������������ûȥ��ͬ�������
���������������㡪��ÿ���ʮӢ�߸ߵ�¥�壨���ⶰ�����Ͻ���ԭ�������ѻ��IJֿ⣬Ψһ��һֻ���ݲ�������ҡ������ֻ���ػ�������������������Ϣ�ȶ������ú���������ʣ�����һ�����ȡ�
������ʱ������������������ɹ�������DZߣ���ãã�Ĺ����Ҳ��֪�Ǹ�������뻹��ʲôԭ���Եú�г�쳣����ȴ���ˡ�
�����˶������µ����ţ��·�Duane��Hanson��������Ʒ�������Ǹ��ȶ�����ͷ�����Ժ����˸���β���ξ����°ͣ�����ȥ����ôʧ�˻��Ƶ�а���ˡ�
�������һع�������Ц˵������û������ɣ�����殻���ǿ����Ƥ����������ô����������ֻ��ϧû����������������
��������һ���ȣ������ף������������治���ء�
������������������ˣ������Ұ��֡�
�������ҳ��ƽ�������������ǰһ�ƣ�˳��˵�����ֲ����ҵ�˽���ղأ��ñ���Croissant����˭���Եá���������������ԡ�
��������Ů��������ߴߴ����Ц�����졣�е���һ�Ծ��ܺ���������Ķ���������ѹ�������������˵ʲô��ȴ�ָ����IJ��ں���
��������������殳��˵���Ϲ��Ϳ����ȣ������˲��û�Ǯ��Ҳ���״�ʱ�䣩��֮�⣬���д��ʱ���Ǻ��ڰ������ջ�Ļ����
������һ�ģ����Ǵ���꣬��֪���������������ù���ҹ������Ǵ������ڡ��ò����ױ��������ܻ�ӭ�ġ���������ѡ�У�����˵��Ҫ��ȥ�������������Ϣ���û�ϣ����˷��ţ��˼�ȴ���˵绰��˵�ݻ�һ�£���һ�ӣ�����û����Ϣ��
�������ǰ���Ҳû���������ţ���˵û�а׳Ե���ͣ���ŦԼ��������ˡ���������Ǯ�ķ����Ȼ�Ǯ�Ļ������ø��ࡣ
�������һͷ�Խ����ҵĹ�������������˰���ȫְ����������ӡ����Ӳ�֪������һ�����Ҿ�����˶�ĻӲ���������������⣬�Ӷ������������ϰ��ᡢ��ɫ���ӻ��ż������ż������֮���������ɫ��������������漰��ľ�����Ṥ�������ơ�����֪�������ֻ�ǰ��ҵ�һ���ֹ������ѡ����ಿ����ʱ�����е�¼����������Ҳ���ְܹ��Ҹ��硣����殶�˵��¼��������ѳ�Ϊ���ִ��������������Դӵ��ӻ�����O������������ǿ���֮�������ȫ���ˡ�
��������������ȫ���ˣ���段���������Ҳ���ˡ����ҵ�¼������ǣ�浽����¼�����㡢��������ӡ��Ƴ�cD�ȡ���������ص����Ҹ�����վ���Լ�ʱʱ������վ�������ĵĹ�����ʱ�䡣��ô��Ļ����˭���ֵ������ǵ�Ȼ�ǰ������
��������֮�⣬�����������������Ե����£������ɹ������ء����䡢���顢��˰�ȡ�������ŦԼ�Ļ��Ȼ��̡��ղؼҡ������ˡ�ý��ȣ����ѹ���һ����̳�������ƣ�����Ҫ������γɹ��ؽ��������ƣ����ʵ��⽻���Ӵ��������������Ҽ�Ϊϸ�£�ÿһ���������ĥ���������в�����С������Ҫ��չ�����ᣬ���������⣬��������ǰ��Ҳ����û�п��ܡ�
����ֻ�����ҽ���æ��������������ݵ���Ҫ��ɫ�����ɶԡ�����������������Ǹ�������չ�˳Է�������ӭ�����ò��ܵ��������£����ҾͲ��а�殲����ˣ���ϸ���ţ��±ع��ף����绰������������������Ū����أ����������������Լ�������������ϵ�����ֻ����һ�Կ����֣�������Ϊ�ǵ������Ǿ����������������ߵ�������̸��It's��not��what��you��know��it's��who��you��know�������������㶮��ʲô����������ʶ˭��������˰ɣ�����ֻ�ὲ���ۡ����ҹ�����Ҫ������ôִ�С�
����������������һ���ĵ��ӣ����ܺܶ��˶�֪������˵���������㲻�ñ���˵�û�Ҫ���������ұ�����ǿ�ĵط��������ܰ������������������������������ø������������
������殷�������ǰ�ﰢ������һ���糿ˢ�����ڵ�¼���ˣ��ͻ���Ҫ��Ǯ���������������û�£�����Ҳ�����ţ��㲻����������Ҫ�����𣿡����˵��������Ҫ�����˶����ֲ����Ͷ������������DZȶ��ڶ��𣿡�������������ˣ����ﻹ��Ҫ������
����������ʱ�����˵绰�����Ҹ��߰���й���һ�䱨��������ʱ����˷ܵü��������������û�뵽���������Ǹ�֪��ͣӪҵ������������段IJ���ֻ�õȱ��縴ҵ����˵�ˡ�
����˭��֪����ν����ʱ��������ζ�����㡣���û�ޣ�ֻ�м����ԹԶ��ڰ��һ���������ۡ�
����ŦԼ���ϻ��������������Ȼ��գ�Ҳ����ס���������������ҵ����⡣
�������ҵ��ϸ��̣�һ�����Ŵ�����İ�殣����������������Ŷ�ǹ��һ��һ�±��ر��Ż�����
�������������ΰ�����˵������ŦԼ���Ӳ��Ӳ�������˺���̫�˵����ĵ����ϣ���Ҫռ������������Ů�Գ�ͷ���������������ʤ�Ǿ����ܵġ�
������̧���°ͣ������ڿ���쨺��ţ����ǣ���֪���𣿡����Ѿ��ŵ��ˣ��Ǿ��ǡ����������ͱ�Ե�Ļ���������̧ͷ��������ȡ�����������ơ�
������殲��ý����ҵ���ˮ����һ������ҵĸߵ���һ�����룺�ⲻ����������룬��Ԥ����ֻ��Ʊ����һ���𣿡����������ԣ�����Ԥ�⳱���������紴��糱�������Ϊ���ҵ��ֹ۶������š�ֻ��ÿ�����������ϣ������ڰ��Ҹ��ǵ�������±Ƶú��������ء������ǰ��ң����Ժ���������ʱ��ذ��������ù�Ѫ��ͷ��
������֪�����㸸��Ӧ������������ʱ���������ҵ���˼�ǣ�������������ںõöࡣ
��������ں�ˮ�ͷ�˿֮�䲻������̧��ͷ�����������ڿյ�����һ�Dz��ϳ��̣��������۸��ӱ���İ��ң���װû�������Ļ���ֻ�Թ��Ե��ʣ������������Բ��ԣ������Ҵ�̴��߹��������ڰ�段���ǰ����һ��Ũ�̣������һͷһ��������Ҫ���˱������������ܿ࣬һֱ���㡪����ø���ǿ�����߲��������������
��������˵��Ӧ�øϿ�ȥ��飿���������Լ��Ľ��ۣ�����ô�ܸ����㣿���������ţ���Ӧ�ø����ҵ��ǣ��Ҹ�������һ��ū����
����û���������ҳ��˱�����������Ű�����˹��Ү��˹���ġ��������ּǡ���1��wasa��coward��and��a��slave��I��say��this��without��slightest��embarrassment�������Ǹ�ų���ū����������˵һ��Ҳ�������߳ܡ�����˵����ų���ū����ʵҲûʲô���߳ܵġ�
�������й�����������ϣ���ʱʧȥ�ô��κ�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