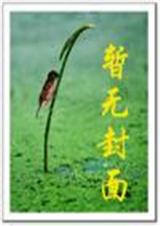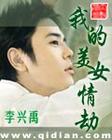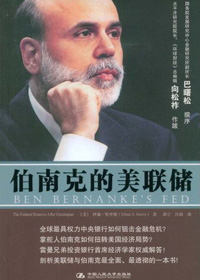̨�������������� ����:������-��13����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ļ�����κ�һ��Ů�Ӵ������Ŀ�кͰ�ο�����������ں����������ɣ�����Ϊ�����ϸ�����ȱŮ�ˡ��ڡ�������������������һ��˻��ر�������Щ����������������־ʿ����ݵ�����Ů�ˣ�ֻҪ�����룬����û�в������ĵ�����ÿ��һ������ٰ�һ�λ�����ύ���һ��ˡ���ֶ���һҹ�飬ż��Ҳ��һ����ģ������ⲻ�����Ƿ�չ�ɹ̶��Ĺ�ϵ������֮��������Щİ��Ů�ӵ����֣�ȫ��͵͵����һ��С�����ϣ�һ�겻�����Ѿ��ۻ��ж���ʮ��֮���ˡ�
��������˳�˱����Լ���������������Ȼ����װŹ�����һ�������˵�Ļ��ᣬ���Ƿų�һ��˵��Ⱥ�ڵ�ɿ��������Ҫ�����Լ�������û�����ֽ̱�����Ȩ����������Ĺ�ͷ����Ϊ������Ч�������������ͣ������˳�˴�Ӧ�ˡ�
��������˶����ĸм���Զ�����鰮��
�������������¼�����������ʱ���ǵ�һ�������������¡�
�����������������������룬����������һ�ο��ѵĿ�ʼ������֮ǰ������Ѿ����о������ַ�����ড����ǵ�����ͻȻ���ҵ�һ����Ϳ�����мҾ���һ��á���������˵�����̾������ӵ����湤��ȥ��ש�顣��ҿ���Ҳ����Ч�ȡ�
�������߾���ש�飺�����������ǶԸɣ��������Ҿ������������ʮ��Сʱ�ְ�פ�ء����ռ�һ���������������Щ���������г������ӵ���ʽ��
����δ��������ͬ־̨���ļ���Ҳ�����١�
�������Ǿ���������Э���ƻ��е������ճ����С���ʵ���������ѿ���û����·��ֻ�ܸ�����Ӳƴ�����ˡ�
��������Ӳ�ɵ�����������Ҳ���ھٰ졣������ʱ��һ��ǵ�����˵������ƭ�˵ġ�����������к����ݱ䵽�뾯����ͻ�����ʹ�����˹��������ʱ�����Ƕ��Ѿ����������ˡ�������ô����֤��Ӱ�������������գ���������ֲ��ġ�����֮�ܶ��˲��һؼң���ȻҲ���������ڣ���O�ᱱ�����˼��С��峿���ྯ�����Ž���ץ�ˣ������������Լ����ڼ������ؽ��Ż�˳�˺�Ӥ����
�����������dz�ҹ���ߵ�ƣ����Ѷ������Χ�����ߴ�����ƹ��������ܵ����ֻ�סͷ�۵�Ҫ����λ��û�б���ɲм�������˶���ʧ�������������е���������ˡ���ʱ����ȥ���Ƕ������ֱ����������������������DZ���д���棬�����䡣����Ҫ�IJ������ǣ������ʱ�����Ѿ���ʼ��ν�ġ��߸����������Сѧ���ǡ�����˼�롱�������ؿ�Ц����֪Ҫ��Ҫ�����ǵķ����ϳ�����Э�����������͵��̵����̣�ͬ����һ����ˣ��Դ˶��������š������ܱ���һ��ij�Ĭ����������䡣��Щ����ס���ļһ��Ϊ�������ӣ���ͬ�鶶���Լ����еĵ�ϸ���������������������������İ���ʯ��
���������º���Ѷ��ͥ�����Ǽ������Լ��ı����������������������ߡ�������ʦ������ôŬ���绤���������Ծ����ޣ������罫�ﶨ�ˡ�������ˣ������豰����ϥ��������������ͥ������������Ѷ�е�����ȫ����������Ϊ�Ʒ����ʵĺϷ����ݡ�
���������˵������ƺ����ظ�ij�ֹ��ԡ��������������ڼ����������ߵ����Ȼ��ֹ����һ���ţ����Ǻ�Щ�ꡣ
���������д���ߵ�ʮ����ͽ�̡�����������Ψһ��ʤ���˰ɡ���û�˱������̡�����������̵�ʱ����ֻ����롣���Ƿ��̵�Զ���̵�����������Ż����Ĵ�ȴ���ŷ��ʱ��Ҳ�����������ܸ��ܵ�����Ĵ��ºͱ��롣�������Լ�ǧ�ɷ���ϣ���������������ͬ־���ϸ����ǹ��裬����˳�˺Ͷ��ӡ���ƽ���������ֶ��ں������ʱ���ܿ���д���������˸տ�ʼ��������ʳҲ�����ԡ�
��������������������ʼ�ڳ���������֮�����ŵ��ŵĺϷ���������һ��������ί���Σ����Լ�����Ҳһ��������Ȩ���ƿص����ġ���Щ������������˿���ǧ����ĵ����ϣ�������Ϊ����������֪�������ˡ�
��������������������������������������������������������������������
����Ȩ��Ҳ������һ����ʩ����һ�������IJٿأ�һ���ƿ����ˡ�
������������һ���Գ��Ŀ���˵���������α�������Ļ�����ʮ��֮ǰ���ҳ�����ֻ�����Ǹ�ʧ�ܵĶ����ߡ�
����Ӧ��ƽϰ�ߵ��Լ��͵������������������ۡ����������ʦרͬ����С�ϵܣ�����ͷһ�س�����ѡʱ����Ȼ��֪����ð�˳�������ԸΪ����ƴ������������Щ��Ĵ����ʹ��СС�ķ��ˣ���Ҳ��Ϊ��������������Ļ��֮һ��
������ʱӦ��ƽ�ݸ���һ�ݾ��ڷ�Ƥ�С���������������Ů����Ƭ�ļ�����ͼ˵��������һֽ��ϸ�����������
��������������������С������һ�Ȼ�����ġ�
�����ţ���������������֪����������
������Ҳ��֪����Ҫ��������������������ö��꣬Ӧ��˵�Ѿ������ˡ���
�������ƺ�����������ֻϸ����Ƭ�µ�ͼ˵�����ڣ������������������ʱ���������Ϊʲô��������ԭ�����ֲ��Ǻúõģ���Ԭ����
����û��ô�䡣����ϸ��һ�������ģ���ͼ����ױ����������ƺͳ�����ҵ��Χ���һ���ԭ�������ӣ�����Ѱ�������˿������
����������о���������ƭ������ƽ��ӡˢ�������������ѶϢ���������Ϸ��ij���������Ů������Ʒ���һ�ޣ����˽������������֮�����Ψ����ͼ��Ŀ�ġ�
������ʱ������Ը��������������������������������Լ�����ò������Ͷ���п�ӹ�Ĵ���ý�壬���������������İ����������Ⱦ��
����������������������
�������λ��ʮ����¥�ߵİ칫�ң���ʵ����ѧУ�����������������������һ���糾���͵�ũ������Ϊ����������ӵ����ã�Ĵ��Ͷ��ᡣ�Ծ����ɸ���У�Ѱ���Ǽ�Сѧ�IJٳ���ֻ��Ȧ���۴��αȷ���֮��Ҳ������һС���顣����ͼ��ʶС�����ε������ֵĵش���������ȷ������������һƬסլ��һ�ǣ����dz����Ǽ�ᴩ�ϱ���·���ϵij����г�������������жϿ����г��ijɷ־Ӷ࣬������������ǽ���ˮ������£��������Ͻ�����·����С���Ծ�ĬĬ��������·���£���ô�Աߵ��г��õ��������յ������ˡ�
������һ�ȥ�����ǰ��������ʹ�����������һ�����ڶ�����������֮����Ҳ�ѻ����κ�֧�������Ƭ�Ρ�
����ֻ��һ�㣬���Ӳ������ף�Ҳһֱ�����ڻ���������Ϊ����һ����ʥ�����ɣ���ʹ��û�������Լ���Լ�������ȻŤ��һ���������Ĺ�ִ��ᡣ
���������Կ��Լ���������̨������һ���˿ڳ��ܵ�С�ط����˵ĽӴ��Լ��罻�Ĺ㷺�������ײ����ģ�����˵���������ȼ��������ˣ�Ҫ�����˻���ʲô���⡣
�������أ�����ʲô���ӳ��֣����߹�ʱ�С����������ʵ����ҷ�ӭ����������һ����ˮ�浴����˿������Ļ������������ʵ�Ц�ۣ��������ɣ�����Ӱ�Ӱ����֡���
������ٿ�������˾��ڡ�����ˢ��һƬ�հס�
�����ҵ��������ĵ绰��Ӧ��ƽ˵������������ѡ���ˣ���ڹ����ϣ��ҿ������Ȼ�һ�������ڹ�����־�������ģ�Ҫ������ͱ�������º���ȥ������������������Ǻ��ˣ��㲻��Խ��Խ�ڡ�
�������Ҷ���Ҫ����Щ���������£�Ҳ����û�п��ܡ�
����������ٿ��Ȼһ�������ֵĴ����д�š���������С����ʮ��ǰʦ������Ļ������û�������룺����Ȧ��û�������ǵ����ġ�
���������Խ�����ת��ȥ����Դ�Ͷ��ʮ��¥�ײ�Զ���ij��У��������ݺ�ĸ��š����ߵ���·��������Ҳ�����������ȵ�ˮ����δ�����ε�ũҰ���������������֣����֮��ɸ����µĹ�㣬���뵽һ���ˡ�
�������е�һ���㱡���Щ����������������������䡢�Ⱥ������ѣ��·�ȫ�������ˡ���ȥ����ؽ�������ģ���������������
����һ�����ÿ��ÿ�µ���ʵ֮����ν�����μ����ٷ�֮��ʮ���ϳ���Ȩ����ά���������ڵõ���Ȩ֮������Ϊ��ԡ�����ȷ�����������ɵ��£�����ħ�����ı�������ںš�Ȩ�������������������Լ��κ�Ȩ����Ҫ����ɵĶ�����
�����Լ������ô������𣿡�˼��������Щ��١�������̬����Ƭ����������Ը��������ʮ��¥�ߵĴ��ߣ�������Ȧ���α��۴η���֮��Ҳ������һС���顪���ǿ鱩¶��̫���¡���ͺͺ����һ������ǿ����һ��Ļ�ɳ�ٳ���ֻ�ǣ������̲�סҪһ���о���������Ŀǰ���ڵ�λ�á�
����Ҫ�����ɴ��Ҹ��˵������������Ϻ��ˡ�Ӧ��ƽ�������
�����ţ�Ҳ������
�����漴һ�룺�����������������ҳ�����λ�ã�������ô���أ�
����������������������С�Ӷ�Ů�����£������밢�
��������˵ŦԼ�Ǹ��������͵ĵط�����������˵��ȫ���������������ۺϵļ�ɢ�����ø�Ϊ��������������������е��ˣ���ʵ��û��ô���й�����Ǯ����ʱ��������������ж���һ�ĵľ�Ӣ�Ļ�����������ֵ���Ҳ���������ڹ�����ס��������������������ת���������������ط�����һ�����ص㲢��ͬ��
�������Ǿ�סŦԼ������С��С�������ȴ���ڣ���ʹ�����Ծɾ��ޣ����ΧҲֻ�ڼ���������ϣ����������ĵ���ȴ����Դ�����Լ����ȫ�������Ľ��㡣��������ϣ�����һ������������Ŧ����Խ�У���������������������ѣ�ֻҪ�룬̽��ͷ���춯���ֽţ������������ŵĿ����ԡ�����Ե�ڴˣ������ϸ���������������ϵس���������������ˣ��ر����ĸ�־������������������꣬���Ⱞ��ӵ���ˡ�
������Ȼ���������˽�פ���ˣ�Ҫ���˶�ñ������ɼ������һ����ս������������������Ľ����ת��������ɶ�����֮�£�������ʱ����Ҫ����Ƥ���ǡ������ۼ�����ʳ������
������ȴ�Ǽ�����̵Ķ������������˳��IJ��̲�ʳ���ܻ���Щ������������Ʃ���ȥ��һ���֣�һ���ӣ����������ĺŽǣ��������ɻ���Ȼ����������ʱ�ļ�������������ռ�г���ı����ͱ��ء���ʹ������һ��������̥���ǣ���ʹ��ŦԼ�����һ������ij��У�ɱ���������ȴ��ͷ���������ĸ������Ǹ����е��Լ����Լ������ֵ���Ƥ�²�ס��ð������
������������������������������������������������������������������һ
������û���꣬��殺ò������ѵ��˾�ʱ����װ��ȹ������������ѧ����������һ����ͷ����һ���ƶ�����ţ�п㡣���������Ž����Ѵ��ֻ������������Ư����ȴƶ�����������Լ��ճ�¯����ƾ����˴ӱ���������ѧ��Уֱ���ҹ���վ��ǧ�������ܵ�ŦԼ��
�������Сʱ�ڴ�����ͨ�绰�ŰѰ��Ҵ�˯���к��ѣ��ٵ���һ��Сʱ�����������ٳ����ڵڰ˽ֵĹ�����վ��������ͷ��ɫ���ɵľ�����һ��ҷ�س�ȹ�����ϵ����̾�����殻�δ���ü����ڱ�Թ�������Ѿ�������ΪȻ��˵�ˣ��ֲ��ǵ�һ����ŦԼ���Լ��в���ֱ�������Ƕ�ȥ�����𣿡���������֪��������ÿ�춼��ҹ�﹤������Ҫ��������ѡ����Ͼ������İ�ҹ��������������峿��
�������ں췢������Լ�˵����Ϊ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