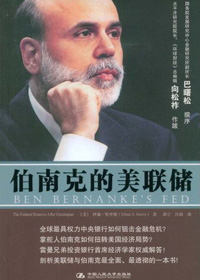̨�������������� ����:������-��1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ɵֵ��ˡ�
������������������������������������������������������������������
����������������������ȥ��������£���Ȼ���������˵Ĺؿ���������Ϊ��������ĺ���֢����Щ��ʹ��ڰ��������պ���ϵ��Ȩ���������ҵ�ϸ�Ĺ��ǣ��������رܹ�ȥ����ʹ�����ⲻȥ���롣���Ǵ���������������ĺ���������Ӧ����кͼ��齻֯�Ļ��죬ȴ���ص������ζ�٣��þ����Ʋ�ȥ��
����̫�����ȥ�����ײ��������ֺ�����ǰ�����ں����Ѳ�������ֱ档��֮�����������Եİ��ȳ²֣�ʹ�õ�ʱ��ʮ�����۵���������ȷȷʵʵ���ܼ��ȵ���Ҳ��������������ʷ�����͵��״Ρ�
���������ⲻȥ�������£�����������ȴ����Щ���������Ѿ��ɹ��������������¡����̺ʹֵ�ϸ�ڡ������������������ʲô���ӣ���Ҫôֻ�Ǻ��棩�����������������������ε��Լ�һ����û���˻�ȥע����ɾ�֮�����������Ϊ��ֻ��Щι��������㿷��Ԭ������һ�ȶ����������壬����ˡ�
������Ψһ�ǵ������ģ�������ˮ����ҹ��Ϊ������������������������������Ů�����ﳵ������ȥ������Ҳ�����ڱ�̫̫����ȥ������˿�������һ�����Ƶ���ڶ�ͻȻ���𣩡������Ǹ�·�ƻ����Ǻ��ձ�������������ӭ�����ϰϰ���������ҹ���������ŵ�������������û�о��롣
������һ������Ҫ����һ�Ρ������ͷ�·���ħ���̾����ģ���������һ�����ˡ����Լ���û�й�����ľ��飬���߾�����ˣ��Ÿ����ģ�Ҳ�������Է���������������Ҫ����ͬ������������ϣ����ֲ���̫¶�Ǻ���Ρ����Dz�ϧ����һ�����£���ҹ�������ؼҵ�·�ϣ����շ�������������һ�����ѣ����Ļ�����������Ů�ѣ�ȴ�����˶��dz��ĺ��ߡ���һ�죬���ﳵ��������������������������Ȼ�������������֣���Ů��һ�ع�ͷ�������㽫����ס�ˡ�
����˵�꣬���ẰԬ�������֣����ĵȴ�����ȴ�Dz��ϵ�������IJ���ͷ��
�����������˺�Ů������Ķ���ʵ�ڲ�̫һ��������˵���������ƿص�ʱ��������ͬ�������롣�����ٴκ���������С����͡�������һ���ظ��Լ��Ĵ������ǻص�ԭ����֢�ᡣ
�����·�֮������ʵϰ�����һ�����ͷϷ��Ū������������ҵ���������Ԭ�ּ�ֲ����ƻ�Ů���������������������壬��ǿ�������أ������͵����ߣ������κ�ѧУ�����ɲ��ϡ��Ǻã���������Զ㵽�������û��Ҫȥ��СѧУ����������Ϊ�����Ĵ����ΩУ������������������д����Ϊƫ�ġ�˼�뼫�ˡ��˸����֣�ȴ���������������һ����
������˵����Ԭ�ֵ�ѧУ����СѧУ�������������Ǹ���٣�ɤ���ر������С��У����ͬһ�������Ĺ��ѣ���æ���ҸϽ��ر����е��Ŵ������������������ķ�����ʩ֮�£�������û������©��Ԭ��������У��Բ�������ı�֤֮�°���ס�ˡ�ֱ�������Ҳ����֪�¶��������©�ģ��Լ�������δ�ɵ�Э�顣��������Щ���Ѿ�����Ҫ�ˡ�
������ԭ�ɰ�����������ƽ����Сѧ��ʦ�����Ԭ��ֻ��ijһũ����Ů��������û����������Ͳ��̵�ƶũ�������ijɼ�������ԭѧУִ�̱ز������⣬����֮�������ɻ顪������ȫ����û�п��ܣ��������ǵĹ��»�����Ϊ�ѻ������Ҵ�ģ�һ���в��������İ����������鷢��������Ԭ�����Ͼ���ȫ��������
�����ķ�֮һ�������������������ı�������ƺ���ȫ�Ϻ������������������Ԭ����������²�����й�����û��СѧУ����ʾ�Ե�����ñ�ӣ���ôֱ�����죬������һ��ӹӹµµ��Сѧ��ʦ�ء�
��������֮�����¸�ĸ���ˣ�ֻ�Ҵһؼ�һ�ˡ������ϱ��˸���ڣ�һͷȫ����СѧУ�����ϣ�˵��֪Ϊ�ε�����У��������д����������������������Dz������ˡ�
������ĸ��ʱ���˳���������Ҫ�����죿����ѧ�Ѷ�������ô��������
����������˵Ҫ���ֱ���ȥ���˼���
�����ҲŲ������ȥ���ˣ������ֵ������Ͼ���˵�����Ӻ����Լ������Լ�����
����û�������ֽ���������������ҹɫ���˼����ң���һ������ͷ�������ϸϴ��峿���ĵ�һ���������Ũ����ҹ��ɽ���ﴩ�У���ǰ�Ʒ·�ţ���Ƶ����һ�������ĺ��⡣
����ƾ���Ŷ�·;����Ϥ����������壬ȫ���ŵ��������IJ�̤������ǿ��ɽ�����������£���������Ƴ�ͽ�����ܡ��������Լ������˸��Ǹ��ܵ������������˹��ֱ����������
�������������л��������ˡ������У�������״��������ɽ����˯��������ֲ��ü���Ҫ�����˵�̫�����˿�ֻ����һ�����캬���������������վ���ϵĺ���һһ���ȥ��ͻȻ��Ҫ�ij嶯��ȴ�ڻ���ҡ�һι��ɵİڶ��У�ͷһ���˯�˹�ȥ��
��������������������������������������������������������������
�������ϲ���һ��ij�����ȫ�ܱ��ˣ�ÿ���ط������ô��������������������ĵ�ϸ���������¡������Ⱥ����ij��衣ֻҪ�ܺ��ڵĹ�����ʲô���ɣ���ʵ�ϣ����˸�����Ǯ�����۶��٣����ƹ�ʱ��������һ�磬�Ϳ���ȥ�ˡ�������������Ҳ��û������������ֻ�ܼ����˲��������ι���Ա��ˮ���ӹ��������������ɢ������һȺ��Ů��ͯ����һ��������ܡ�ˮ��Ĺ�Ƥ���ճɼ���ժ���ӡ��۽�������ȻҲ�ɹ�������������۸��е������������ô�����ͷ�Σ�ֻ�ܰ��������������Ÿ����������ũ�Ļ��������Ϥ�ģ���Ϊ������¹���ˣ����ǽ������ӣ�������һ�������������㡣
����û��ã���������һ����һ���ı��ӡ�ÿ��һ��İ���ij��������������張����ڡ���弾���ס������ͨ���Ƕ����á��պ��Ÿdzɵ�Υ�½��������������˿ڣ���������ܲ������⡣û�շ���ʱ����Ҳ�������˽��ʹպ�ס������������������һ�������乫���������Ӿ�����ζ�Լ�������ǧ�ϰ�Ť�������棬����ҹ�䲻�ϰ��˴������о��ѡ��Ⱦƾ۶ĵij��֣���ֱ��������������
��������һ�֣����ٽӺ����ȴ�Ժ��������ݣ�һ����ͨ�䣬����һ��С�ߵ���������ľ���ɵ�������Ȼ��һ��һ���������ͨ���ⶼ�Ǹ��мҾ������ס��������Ȼ��Щ�������¹�ʱŮ�˶�������ǰ��Ժ�����շ�����Ѽè����С����Χ�Ŵ�ת����������������д��������ʹн���������ζ������ͦ�������Ժ�������ֻ�ǵ���ҹ�䣬������ұ����ǿ�Ӥ���ĺſޣ���ʱ����ϳ��������ֵ���ҹ���߲��ݡ�
��������ã���������ɽȥ��ľ��̰ͼ��������ɽ���Ȼ�徲����ľ���������ף���ʵ��ֻҪ������������Ҫ�����������ò������������ţ������������һ����ڵ�������˵ã����Ͻ����˹�����Ǯ��û���ü����ϡ�
������ɽ�º�������ʲô���ɹ��ˡ��տ�ʼ���˲�����Ż��ɵ�Ŀ�⣬��ô����Ҳ�����Ǹ��ɴֻ�ģ��ٿ�����֤��д�ġ�ʦר��ҵ��������Ӻ����ˡ�������ý��ͣ����ұ�����ɾ�������ȥ�������а취�����Ұ���ǩ�ģ�Ƿ����Ǯׯ��ʮ����������ͻȻ�з磬�����������ö�����С����ԡ��������¾����ϰ廳�����ɻ��±�ѧУ����֮�ࡣ���ֲ����ñ�ҵ֤��ȥ�Ǽǣ�ʦר��ҵ���ʸ��²���Ҫ�������ɣ���һ��ʱ���ĥ�������������Ѳ��Ǵ�ǰ�Ǹ������IJ������ꡣһ˫��ڴ�׳�İ��ӣ���һ����Ѫ�Ƶ����ƣ�����ֻ�̾�������ʲô���Ĺ��������ǿ���������߰��ˡ�������һ��˵�о��飬���������������������˳�����ˡ�
����������˼����ǰ������ʦר��ʦר��ǰ�IJ���Ҳ�����롣
���������ڴ�����һ�����ȵ���ת�����Ƕϲ㣬������ѵ��һ��ʵ�飬һ����������һ����Ц��
�������췢�֣����е�������ʵ�������������ڶ�ʮ���Ͼ����˴����������𣬵�ͷ��һ���ա��������������û����ͷ��ֻ�ǿ�ʼ���α����ˡ�����С��Ƭ��һ���������ϵĺ�룬���Ű����ĵƹ⣬һ��һ�⣬�����Լ���
�������˼��ǰ;�����е�˼��������Ȼ��������Ψ�о����������
�����������Լ����ˣ����ٶ�ɽˮ���Ե�ϲ�������ٶ�ʫ������Ȥ����ǰ�����ɽ����������ɽ�ݽ״����IJ��������Ī���ĸж�������һƬ������Ƨ�����·��߽����������λã��þ���ƽ������������õĴ�Ҫ���̡�������ɽ�����ƺ��˺����������������£����Ĺ���ʱ����Щ�����Ͽڵļ�ʫ�䣬Ҳ��������Ԭ����¼�ڿα��ϵ���Щ������
����ͻȻ�䣬��ʧ����������˵����������������ĵ�������
�������������Щ����һ����ż��ȥ���������ţ������������������ȵ��������ֽкã����ҵش��ϼ������ڡ��ط��ϰ�Ϸ̨����Ҳȥ����һ�š�ij�գ���������ȥ��һ��������һ�������Ϸ��
����ʲôһ����������⡣
�������������߽����ҵĺ��棬��һ��ڰ������ҡ�һ�˷���һ�������������Ȼֻ��һ�����⣬ԭ���Ǹ���Ů������ǰ��
����ֻ�ܿ�������ม�
�����ϰ�߽��š�����綹�Ĺ�Ӱ�£������Ǵ��Ŵ�����һ�߿����ƶ��������Ҫ���IJ�λ��һ����С��ά���Ż���������
�������������÷dz��ͼ��������Ҳ����ȥ�ˡ�
��������������
���������������ҹ���������Ρ�
��������ε������������С�ӡ��չ��ɬ������϶��ɸ����£����ܵ���Ҷ�������˺�����ɳ�ĵײ㣬�������Ҷ�������Ե�ˮ������Ծ��������
����������Ϯ��ҹ�
����һ�������ĺ������ް��ĺ�ˮ֮���е���·�����Ĺ�Դ�������������Դ��⣿�����Ըо��ӵ�ʯ���ڰ߲���Ӱ��ӳ���£������¶��Ļ�ɬ֮�⣬�е���ȫȻ��ơ��Ӵ�������ˮ����������������������������ˮ��֮�У������ں�ˮ������γ��ҡ�ڣ������ʯ�������ﵲס����Ҫ�IJ�λ��������������Ƭ��ĵ���۹⡣�����ȵ�����·��ﳵ�����ǰ������˿������Ӳ����ֿ�����ǻ����ǵ���˱��ô���У����������ĥ�䲻����ʵ������������ò����������壬�����˷ܵ�������״�ĵ�������
�����־��������ʱ���������黧�ڻ����Ƿ�������С�������ľ���ϵͳͻȻ���֣���һ���������ҹ����Ե��ַ�������Ϣ�Ŀֲ�����ĵ�������ɱ������ǿ��Ŀ����ԣ���չΪ���������ʵ�壬�����������ǰ��
����Ȼ�·�һ���п����Ц�������IJ��̣�������������ͬʱ���������������֧�����顣�������Dz�����������κ�ϸ�ڣ�ֻ�ǵ����ʵĶ��Լ����ʵ�����������ζ��
�������˼�Ǯ�����ؼң���������ڵ���ҹ������һ�磬����������������������·�������Լ����ε����㣬�Ծɱ��ⲻ�����˺������������ϸ����繫���İ�Ա��������֮��ĸ�����ټҰ�Ǩ������Ѽ��Ĵ�����˰����˼������ף����ԹԹ��������£��ȵ�������������ʱ����������ĸ��ϲ������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