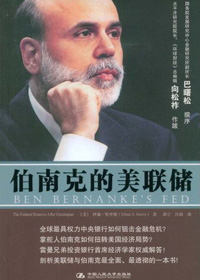̨�������������� ����:������-��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һ
������˵��һ���������ܵ��˿��ü����꣬����������������ע��Ҫ���ض����ص��ˡ���������ͬ��Щ�ܿ�������ĵ�ù��һ��������ů����������ߣ�ע��Ҫ�������������밵������ħ����Dz��ɧ�ź����䡣Ҳ���������Ҹ����еĻ�ɬ����Ĭ����Ľ������ӣ���Ϊ���ʹ���찲���ҿ������֮�Ϊ��֪���¶ˣ���Ϊ�����ĵ������ļ�֤�ɡ�
����ũ����չ����á��Ҽǵ��ǹ�ֽ������Ƥ�ͼ�ֻʣ�µ�С���ڻ����ڴ�����Ǹ��ں�������еļ���ո��̨��ѹ��Ǯ�����Ѹ��������ȥ��������˵�������ţ��������㽫���ϴ�ѧ���á�������֪���Ǵ���ƭС���Ĺ�����һ�����ȥ����˵��ѹ��Ǯ������ƽ��������Ҳȫû����Ӱ��������Ҳû�ϳɴ�ѧ��
����Ǯ��ȫ��ֲ�����������г�Ϣ�ĸ��ȥ�ˡ���Ҳ����Ƣ��ͬ���dz������Ұ־͵�����˫�������ܷ����������۾�������������Щ�겹ϰ�࣬�����Ǽ������Ǯ����ĩ����ѧҲû����һ����������ʲô�������Ͳ�����Щ���Ҹ���������Щ�ˡ����Ǽ���һ��������Զ�����õ�̨�����������������ų�����ʲô����ʵ��ƵĶ����Ǹ���
������˵���ǿ���ʱ��������ȴ�������ࡣ����ҹ�������صش��Ҽ������������Х�������ν�������϶�������Ƶģ����Ű������������ý���ֱ����£��ܾ��·��������Ƶġ����һ�������Ǽ��¼п��������հ߰ߣ�ȴ������ѣ���˯��Ҳ����������
������һ����˯����ʱ��û����������������������ԭ��ʱ��˵�������������ֱ���˯�������ӿ������˹����������յ�Ӱ�죬ҹҹ�������ţ�������һͬ��Ģ�����������ž��Dz����ϴ�ȥ��
������ʱ�Ұ�ͻȻ�ƿ�ů���ı��ѣ���������ľ�崲����һ�����쿪ʼ����ë�����������ӡ���ͳ�ڽ�Ь��������æ�����Ӹ��컨��ľ��³�������ش�����Ϊ������ȡ��һ������������С���İ������ϣ�����������װ���Ÿ�ʽ���ߣ������������������ֵ硢С�����ϻ�ǯ����˿�⡢�����ס�����ֽ����������������Լ����СС�����ڴ����ұ��⾰��Ū���ˣ���Ҫ������ȥ��ʲô����ȴ������ӱ���������ס�ˡ�
�������߰�����һ����ɫ�����£�����ñ�Ӵ��ϡ�������ͽ����״����Ѫɫ��üͷ�������ţ�ʹ�ø����۴�������������ʮ�ߵ��ݵ���ҫ���淢���Ե��´���˭Ҳ����˵ʲô�����������ź���ĬĬ��ע���£���һ��������սʿ�Ƶģ��������׳���������ĵ������Ŷ�ȥ���ҵ���ͻȻ��һ��Ī���Ŀ־徾ס�����ŵδ����ݶ��ϵ��꣬һ�����һ��һ���ţ���ͽ�����ĵ�ȫϨ�ˡ���һƬ�߳����ŵĺڰ���־��ͬ�ź�Х�����ķ����������ʶ�������
��������֮��һ�������и�һ���ذɣ��ϰ�Ҫҹ�����ȥ�ɻ������Ԥ���Ƶģ�����������ǰ���ñ㾪�ѹ�����Ȼ��ƴ��ȫ�������ڰ���������������һ�����ʵ����죻��ƾ�������ļ��䣬�����������IJ����붯������ʱ�����ؿڿ������˵ش����ţ�Ҫ����æ�ڴ������Ҹ�˵���������ü�������һ��������ġ����Һ����ȴ��һ����Ŭ��װ˯���Ҳ�֪�������ĸ�����Σ���Ϊ���Ǵ�δ�˴����۹�������������˵�����־�ľ��龡�ܵ�սȴ����˵�Ǵ̼��ġ�����������ڰֳ��źã��Ҿͼ�Ϸ������˯���ˣ������ڿ���֮��˯�ø������𣬾���һҹ���Ρ��γ�������˭Ҳ��������������ʲô��
�������Ǽһ���һ����ֵ�Ĭ�������Ƕְ�ҹ��ɻ������´Ӳ��������������ֵ�֮��Ҳ��̸�ۣ��Ҽ��ο���Ҫ�ʣ���������dz�Ĭ�;�ѵ���������ס�ˡ����������˵������ƽ������С�еģ�����¶���ȴ��δ©���ڷ硣����ҹ�ﲻ˯���ֵ��ţ���ҹ��������ͨ�죬ȴ����һ�ɿ��ܵĹ⣬ʹ��ԭ���ͻƺֵ�������ӳ��������������ŵ���ɢ�ҵķ����һ�û���ü����ڣ��ѱ���ĸʨ�������ɻض���ȥ�ˡ�
��������������Ҳ�����˶��ߡ��Ӿ���û���ɵ��ڴ����²����Ϻõ���װ�����ϡ��ֱ������Ρ��˲Ρ����̾ơ�����������һЩ���²����廨���ŵĶ������Լ��ϰ�ʱ��ʱ�����ڼ�������ƽ��·�������һ�����������ջ����۵Ĵ�����������Dz�˵��Ҳ֪���ϰ��ڻ������ع���֮����һ�Ϊ��֪��Ӫ���ˡ�
������������������������������������������������������������������
�������쵽�ˡ�
��������↑���˸�ɫ���䡣��ǰС�ӵ�ˮҲ���������������ؽ�Ҫ�͵����档����ׯ�����ϱ�����峿���ںӱ�ϴ�£���Ҫ����ĭ���ݽ��ú�ˮ����һ��һ�������̫�����������ɽ��ȫ¶�������������ֻظ��峺������������Ϣ��
�������Ǹ���ס���Ǽ���Ǯ�ˣ����ǵ�ǽ��������ӭ����չ��ɫ��Ǿޱ���������鸲�ź���ǣţ��������ɫ���Ƕ�������Ȼ��䡣Ժ�ڸߴ�����ӡ����֡�������â����һ�����ģ�֦������������Ϯ�ˡ�Ԥ��ʵ���۵�С��������ֲ�Ĺ��������ӡ��ž顢��ҩ��ɫ������������ɣ�����˽��ȣ���ʱ�����������������ɫ���峿�����У�С�ӱߵ�dz̲�ϣ�����Ұ���Ľ�����������Ҷ����ð����Ļ��룬������һ��ɢ������ķҷ���������Ҫ����ȥ����ð���������Σ�գ�����֦�������š�
����������Ҷ������һ�����֮�������Ǻ�Ժһ��ߴ��ܽ�����������������ǽ�⣬һ����������ܽ�ػ��������б������Ժ�����ˡ����������Ұ����������֮���ñ���ռҶ�ұ���һ��صIJ���죬�һ�����������һ��������Ƶ�������ǰ��������ת���Σ������Ͽ���רժ�����ִ�Ĺ������ԡ����ڣ�ȴ������Ҳ�������ҵ���ɩ����������˵�������߶��ˡ�
����Ҷ��ͷ�ڵ������٣���������ͬ����ͷͷ������ɩ˵�����Ұ���̨��Ŀ���ף����ǵ���������Ӧ����Ҷ�ұ��ڵش�����һ�����ݣ���չ����һʽ���䣬�ֽ���ǰ���������Ĺ���Ȧ������������Ժ�䡣�ɾ��Ұ�˵���ۼҵĵ��������˼�����Ԫ��Ҷ���������ġ�����ȴ�ǵ�����һ����������̨��ʱһ�IJ�����������Σ�Ҷ�Ҽ���Ϊ�Ұֵô���ߣ����������Ը���һ��שǽ������������������֮�ơ�
������שǽ��δ����֮ǰ��һ�������յ������Ϊʲô�ǵ����������أ�ԭ����ÿ����ĩ��Ҷ�����ܻ����ź�������������������Щ���ֵط�����Ӱ��������������ϲ�֮�࣬����ȫ�����Ǹ��˵����֣������������˼Ҵ�����û��ѵġ����ԣ����յ��ҿ���Ҷ������ī�����ᡢ����ѩ������ͷ���š����á���ɫ��������ֳ���������ʱ����֪������������ĩ���ֵ�ʱ���ˡ�
������������������������ڰ�С�ķ��︴ϰ���Σ�����ͬ���ǣ������Ұ�û�������Ǣ̸���⣬������ճ�ʱ�����̶ܽ��ӡ��Ұֶ����ǿ�ҵ���ϣ�һ����и�����ɼ��������룬����������ij���һ�٣�һֱ��������ȡ������ѧ��һ־Ը֮��ֹͣ�����������巣������
�����Ұֽ������������ϴ��˼��ƶ��ľɺ������ڴ����ϣ��������������������ı���һ�����ϰ����ǰ�����������η��ϸ�����һ�����衢һ���ɱ�ֽ������⾰��֪������Ȼ�������¿��ɼ�δ�����룬������ζ�ţ�����ö���ȥ�Ҹ���Ǻ��������룬������������֮�⣬����ҹ��ʮһ���㣬�����������ġ�
�����Ұ������ӴӴ������������ȴ�����������ɨ�������أ����ü�ë��ʺ�ij��ұƵ��������ۣ���һ����������ݺ�ļе������˸��ɶ�������ʸ��ӣ��������Ҷ�ҡ�
�������ʱ��Ҷ��ͷ���Dz��ڣ�����һ��������ʮ���ռ�����������Ӧ�����˲Ż������������������ڼ���˯���˿̼�û���������������������Dz��ڵġ�������ɩһ���������С�����żٻؼ��ˣ�����ҹ�ﲻ�ء�
��������Χ�ŷ���Ժ��ת��һȦ�����������Ҹ�ʰ����Ժ�ӣ�ûɶ�ɼ����ġ���ʱ�ڼ�����ժ��Ҷ�Һ��ӿ�����Ҳ������ȥ�ˡ���������Сʱ������ģ���ɩ��ʱ����������������Ժ��ͬ�����г�����Ҷ������Ů������ͬ�Ҽ������к���ͷ������Զ���������������Ұִ�ɵ�ˣ��������鿼�߷�������һ�Ų�֪��ɵ��㶵ǵģ��������˾ͽ�������ľͷ����ľͷ��
����ֻ����ͬ���ǻ���ÿ�������ʹ��ռ���¼������һ��Ǻ�����Ƥ������Ժ���û������Ҳ�����ż������С���ӣ����������ɩ�����������������Ҳ���Dz�ȫ���ǵ�ѧ����
������������֮�࣬������ǰ��б�Թ���һ�����š��ҵ����ϰ��Ŵ��������൱���������ַ��ȡ�����������������Ӱ��һ��ȫƾֱ����Ӧ�������ò���˼��������������ȫ������ȫ����ȥ�ˣ���ֵ�ȴ���Ŵ��㿪������������������֦�ӣ��ſ���������������Ӱ�ζ��š������������ݶ���è�����ӳ�������ȥ��
������ſ������Ƭ�ϣ����������ܳ������������˵������Щ���µ���������������ŵ������������
�������Ǹ����ž�װ�����ӣ��������磬�ò����������ֱ�������ͣ�������߶�����������Ͳ�С�ˣ��������ж����ȴ˵������������Ҳ����������ˡ��ݽ�һ�ߵĴ������ϣ�������ſ������д���ء�
�����Һ�Ȼ����������˭���ˣ��ɲ��DZ���������ѵ�̫̫�Ĵ���ӡ���½����У���Ǹ�����ʱ��ʱ��Ҷ���߶���һ�Ụ����������ɽ�á�У����ݰ����衣һ��輪�ճ�������ȫ��ȥ����ɽ�ͻ������������ٵ�һ����������ˮ����Ʒ���ò��ܵ����������Ҷ�ҵij����ˡ����������������Ѳ����汦��ϰ���Σ�������Ȼ�ڱ�������վ�������ɷ�˵�㽫������������һֻɳ����ȥ�����ǽ��������������ϣ����Ǵ�С�������ȹ��ˣ�����ֻ��������һ�£�Ҳû�����ܾ������϶�ľͷС���ֽ��ҳ������꣬����Ҳ����ʮһ�����ˡ����е�һ�ְ�ס����˫�ۣ���һ��������������ʧ�ڱ���ȹ�ӵ��¡���ʱ������ɫ糺죬����Ҫ���������ӡ����յ˵�ȴ�����������������ȥ���ס�
���������ǵ�ͨ�죬��̫��Ѩ�Ľ�Ҳ��������������������ͬһͷ���ޡ����������ѣ�ȴ���Ǹ�˶�����������һ����������ѹ�����ӵ��¡�
�����������ڵ�ſ���Ƶ�Ե�ʣ��Ҿ����Լ�ͷ��Ҳ����������
�����IJ��ɵ��������˼��������ؿڡ���ֱ������Ҫ���������������ˣ�һ�ߺ���һ�ߺ��ߣ���ʵ�ڲ�֪��������Ҳ����ͬСŮ������ô���ģ��ο���Ȼ����ͬ���ޡ������ּ��ֺޣ�ȴ����ʼ�ղ��ҷ���������졣
�����ҵ���ֻ������������ţ�ʮָ������ס������Ƭ��ͷ�غ��ϰ�������Ϥ������������֮�⣬����������С����ȼ��ѵ��ؼ����ƣ�һ�����Ҷ������ǣ��о����������Ǽ����ˡ���������Ͻ��ؼұ������軹���ü�����������ʱ������ͻȻ��¡һ��ֱֱ���䵽�ذ���ȥ������ʱ�ֵ�����������һ��������ˡ��ұ��ܵط����ݶ�������ȥ��
�������ɿ�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