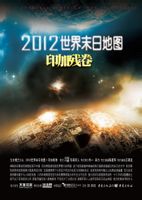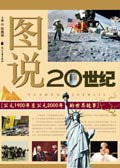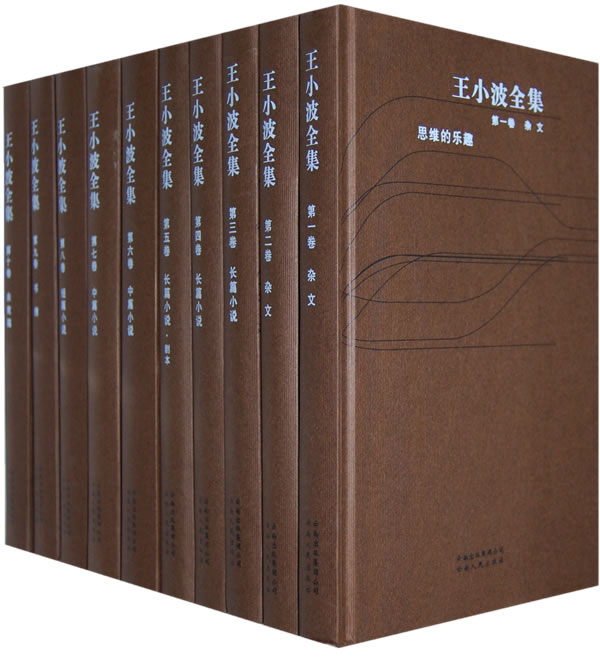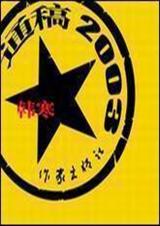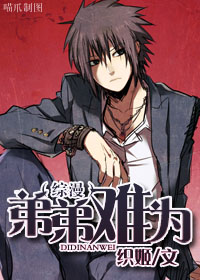2004年第4期-第6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们。而同时我已预感到这个极具个性、气息非凡的小村落的深层一定蕴藏着更丰
富和独特的文化信息。我一边思谋下一步该如何做,一边登上高原。此时,日头西斜,侧光人村,半明半暗,景象更加立体。然而山谷空气之清澄,令我惊异。每一口空气吸人肺,鄙像气化了的清泉,把肺叶凉爽地洗一遍。低头看到一村民蹲在下边一块突兀的山丘的顶上吃面条,人在这地方很是危险,看来他却早已习惯了。而且边吃边与更下边的另一位村民聊天。那村民坐在自家院中的磨盘上。
这下边吃面条的村民与我距离十来丈,他与更下边另一村民又距离十来丈。但所有说话的声音都像在我的耳边,清晰至极。他们平常就这么聊天吗?
据同来的一位东赵乡的人说,有时两人说话,全村都能听见。
我忽然悟到,所谓桃源,既非镜花水月,亦非野鹤闲云。原来——互不设防,才是桃源的真意。
陶渊明所写是他心中的桃源。我所写是我眼见的桃源。
不信,你可去看。但行动要快,倘若去晚,说不定已经被现代化的巨口吞掉了。第一部民俗志
初步考察过后,采样小组成员全都兴奋难抑。工作成果在摄影家李玉祥那里立竿见影。他用随身携带的手提电脑,将所拍摄的影像一一展示出来。更加证实后沟村具有典范的意义。他几乎将这个古村落所有重要的视觉信息尽收囊中。由于我们进村后各自行动,他还拍到不少我没有见到的珍罕的细节,显示了这位涉足过数千个古村落的摄影大家非凡的功力——镜头的发现力、捕捉力和表现力;以及在横向行动中纵向观察的深度。
我对他说:你下边的工作是编写“后沟村民俗调查摄影记录范本”了。
摄像师樊宇提出,他今天遇到村中一家正在办葬事。他决定住进后沟村拍摄该村丧葬民俗的全过程,然后抽样进行人户的民俗调查。
我知道樊宇是具有献身精神的摄像师。他锐利的眼睛已经看到后沟村在人类学和民俗学中的价值。他不会放弃或漏掉任何机会。摄像与摄影的生命就是抓住稍纵即逝的影像。
另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对后沟村的民间文化进行文字性的全方位和深入其中的普查。我将这—工作交给榆次区的文联与民协。他们是有普查经验的。我将乌丙安教授编写的《村落民俗普查提纲》交给他们,内分生态、农耕、工匠、交易、交通、服饰、信贷、饮食、居住、家族、村社、岁时、诞生、成年、结婚、拜寿、丧葬、信仰、医药、游艺,凡二十类,二百七十个题目,有的一题多问。请他们据此并结合当地情况,另行计划与设题。
随后,我们又赶往祁县赵镇修善村和丰固村考察民间窗花。这两个村庄的百姓都是心灵手巧,多才多艺。凭一把裁布的剪子,一张红纸,人人能剪出满窗的鸟语花香。我们想从中找到一位传承有序的剪纸艺人,来做民间美术及其艺人的普查范本。
从山西返回北京不久,传真机的嗒嗒声中,就冒出榆次文联传来的《后沟村农耕村落民俗文化普查报告》。榆次文联在接受我们的工作安排后,很快组成以张月军为首的普查小组进驻后沟村。并制定三种工作方式:一、对所有七十岁以上老人做调查;二、采用座谈、随机、抽样方式对全村村民做调查;三、对周围村落采用问卷和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同时将我交给他们的普查提纲,依据当地情况,或减或增,重新列出十六类,一百五十个问题,一问一题。这些题目是在考察之中不断提出和完善的。切实、准确、细微、针对性强,而且周全。这个普查小组颇具专业水准。这便使这份普查报告具有形成范本的可靠基础。虽然我们亲临过后沟村,但读了这份报告后才算真正触摸到后沟村的文化。
从中,我们详尽和确切地获知该村所有的物产,人们采用怎样的耕作方式和传统技术,制肥与冬藏的诀窍,节气与农事的特殊关系,与外界沟通和交易的方式,信贷与契约的法则,一日三餐的习惯,治病的秘方与长寿的秘诀,节日中苛刻的习俗与禁忌,蒸煮煎烤炸腌的各种名目的食品与风味小吃,居住的规范与造屋的仪式,生老病死、红白喜事的习俗与程序,分家的原则与坟地的讲究,各种花鸟动物图案的寓意,村民们崇爱的剧目,信仰的世界和对象……仅仅数十户人家的山村,竟有如此深厚的文化。而正是这深切而密集的文化,规范、约定、吸引与凝聚着后沟村中这小小的族群中的精气,使之生息繁衍于荒僻的山坳间长长数百年。
此后不多日子,榆次文联又寄来厚厚一本打印的集子。是他们进一步收集到的后沟村大量的谚语、歌谣、故事与传说。其中谚语中“短不过十月,长不过五月”、“人吃土一辈,土吃人一回”、“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去的山”、“不怕官,只怕管”等等,都是在这次普查中新搜集到的。多少智慧、经验、感慨、磨砺以及自由的向往与山川般阔大的胸怀,尽在其间。民歌民谣是集体创作的,它反映一种集体性格。我还很欣赏歌谣中的一首《土歌》:
犁出阴土,冻成酥土,
晒成阳土,耙成绒土,
施上肥土,种在墒土,
锄成暗土,养成油土。
这首民谣对土的爱,之深沉,之真切,之优美,真是可比《诗经》。村民们都是土的艺术家。他们真能把土地制造成丝绸和天鹅绒!还有那些关于喜鹊、石鸡、斑鸠、红嘴鸦等等充满人性的美丽传说,叫我们体味到这些从不猎杀动物的村民的品格与天性。比我们自以为科学万能而肆虐大自然的现代人文明得多了。
在我将这些资料编人《普查手册》时,感觉到全国性的民间文化普查启动之前,已经有了一宗丰厚又宝贵的收获。当然,后沟村也有收获。如今已经拥有全国一流的专家为他们编写的第一部村落的风俗志了。
观音堂考古
一切工作都做得有条不紊。没有急功近利,一如农耕时代的生活。再加上学术上必需的严格与逻辑。
从中我发现,观音堂是解读没有文字记载的后沟村史的关键。
耿彦波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我拜托他的三件事,即拓印观音堂中五通碑的碑文,还有对大殿建筑彩绘和院内古柏年代的鉴定。在历史上后 沟村有许多庙宇,除了观音堂之外,村民们都知道“东有文昌庙,西有关帝庙,南有魁星庙,北有真武庙”这句话。但保存至今的只有关帝庙;庙中具有史证价值的,也只有一块嵌在院墙上的村民们捐银修庙的石碑,年款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故而,观音堂中种种史料便如一堆宝藏,其中一定埋藏着可以打开后沟村历史的钥匙。
首先是散落在院中和嵌在墙上的五通碑。分别为:
《重修观音堂碑记》(66X49em)
《重修碑记》(143X70em)
《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143X66em)
《修路碑记》(128X73em)
《重修乐亭碑记》(189X76em)
其中前三块都是记载重修与扩建观音堂的石碑。经考证,将这三块碑的年代先后排列如下:
最早一块应是《重修观音堂碑记》。时在明代天启六年(1626年)。碑石很小,嵌墙碑,嵌在西殿南墙上,碑面无花纹图案,字体粗糙,排行草率,其貌原始。碑文说“榆次之东北有乡……建古刹一座……颓墙残壁”。可见那时观音堂只是一座简朴的村庙。明代天启年间的重修只是填裂补缺,没有大的改观。这在下面一块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块碑是《重修碑记》。年款已然漫漶不清,无法辨认。但是从碑文可以认定它是明代天启之后的一次再修。碑上描述观音堂时说“顾其庙规模,狭隘朴陋,无华欲焉”,表明明代天启那次重修之简单有限。但这一次大兴土木,故而碑文中对这次重修后的景象十分得意地记上一笔“今而后壮丽可观,焕然维新”。这次重修的成果在第三块碑上也得到了证实。
第三块碑是《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时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这是第三次重修。碑文中说,在这次动工之前,经过第二次重修的观音堂已经是“正殿巍峨,两廊深邃”,“自足称一邑之巨观焉”。乾隆年问的重修完全是锦上添花,但规模宏大,不仅扩建耳殿,还对大殿木结构的外檐进行改造,施用昂贵的贴金彩绘。山西省文物局古建专家柴师泽从檐板龙纹的形制也认定是乾隆时期的作品。单看这块《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的碑石就很讲究。碑体高大,碑石柔细,刻工精美,边饰为牡丹富贵,碑额上居然雕刻“皇帝万岁”四字,显示该村一时的显赫与殷富。
再看另两通碑就会更加清楚:
《修路碑记》记载着后沟村当年修筑村外道路的事迹。施工时,退宅让路,切崖开道,亦是不小的工程。修路是一个地方兴盛之表现与必需。这块碑也佚却纪年。所幸的是碑石上署着书写碑文和主持造碑的人的姓名。即“阔头村生员郭峻谨书,本村住持道士马合铮”。而前边那块乾隆四十一年的《新建左右耳殿并金妆庙宇碑记》也是“生员郭峻谨书写,道士马合铮监制”。由此可以推定,后沟村史上这次重要的筑路工程无疑是在乾隆年间了。
另一块《重修乐亭碑记》在前边已经说过,建造戏台的时间同样是在乾隆时期,几乎与扩建观音堂和修筑村路同时。此时,正是晋中一带大兴营造之风,晋商们竞相制造那种广宇连天、繁华似锦的豪宅。在榆次,车辋常氏的家业如日中天,浩荡又精典的常家庄园就是此时冒出来的。而后沟村既逢天时,又得地利。由是而今,虽然事隔三百年,人们犹然记得年产百万斤贡梨的历史辉煌。它的黄金岁月正是在乾隆盛世。由此我们便一下子摸到后沟村历史的命脉。
关于后沟村建村的时间,却有些扑朔迷离。历史的起点总是像大江的源头那样,烟云弥漫,朦胧不明。现有依据三个,但没有一个能够作为答案:
一是人们在明代天启六年重修观音堂时,已经称之为“古刹”。古刹“古”在哪朝哪代,毫无记载。碑文上只说“年代替远,不知深浅”。正像李白在一千多年前就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可是古蜀到底在何时?
二是榆次林业局对观音堂院内的古柏采用长生锥办法提取木质,又在室内以切片铲光分析年轮,最后推算出古柏的年龄为五百八十年,即明初永乐二十年(1422年)。这么一算,后沟村至少建于明初,但这棵古柏是观音堂最古老的树吗?观音堂是后沟村最古老的寺庙吗?还是无法推算出建村的年代。
三是后沟村中张姓为大姓,一位被调查的村民张丕谦称他的家族世居这里已有三十代。并说原有家谱一册,但在前些年不知不觉中丢失了。如果属实,应该超过六百年。可是这三十代究竟是一个切确的数字,还只是一种“太久太久”的概念?
当然,从以上三个依据,至少可以说元末明初已有此村。但什么原因使最初建村的那些先人远远而来,钻进了这高原深深的野性的皱褶里?
学者们有一种观点。认为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