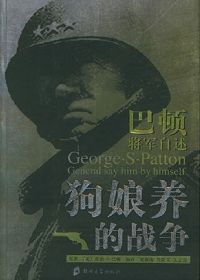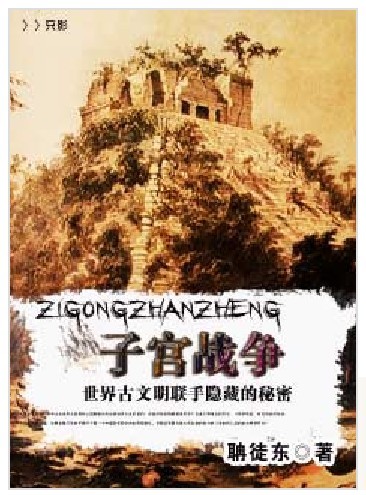战争启示录(柳溪)-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
1994年7月21日黄昏,这部长达80万言的长篇小说《战争启示录》终于最后完成了。我今年已70高龄,象这样的长卷,恐怕是最后一部了。这部书稿和我有着共同的命运,跟我经历了一次漫长的苦难,它终于要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40年代初,当我还是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的时候,我便怀着抗日爱国的热情,在沦陷区的北平,参加了党的城市地下工作。那时为了减轻革命根据地的负担,自己维持生活,同时也为了有一个公开身份便于掩护,我就在敌伪一家刊物谋得一个助理编辑的职务,从此便和编辑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我自小受家庭影响,喜爱文学,15岁上初中二年级时,便开始写小说,并在报刊上发表。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我们的小组被国民党的特务用“打红旗”的手段,即冒充进步青年混入我外围组织,使我们暴露了目标,幸好我们发现得早,我和哥哥杨溢连夜撤回解放区,幸免于被捕。这以后,根据革命的需要,我当过编辑,军区司令部的秘书、中学教员、文工团演员。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了,我成了一名土改队员。当时康克清大姐就是我们的小区委员,她常给我讲述自己的苦难家史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的英勇斗争故事。后来,为了更好地深入生活,搜集材料,我主动要求留在基层,当了区里的教育助理员。三年的基层生活锻炼,是我日后成为作家的基础。1948年,我到解放区后的第一篇小说《挑对象》,就是我伏在老乡家的窗台上写出来的。全国解放后,我进了保定,分配到河北省文联,并且在这里组办了《河北文艺》,由编辑、组长到副部长,培养和结交了一批很有才能、日后很有成就的文学青年。50年代开始了我文学创作的勤奋与旺盛的时期,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些短篇小悦,得到当时主编茅盾先生的鼓励和沙汀、秦兆阳等文学前辈的帮助。正当我孜孜不倦向文学高峰攀登之际,只因写了一篇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和两篇杂文《要有这样一条法律》、《摇身一变》而被当时那阵极左的反右风暴,坠入了政治深渊。从此,我由一个响当当的革命者、共产党员变成了革命政权的“敌人”、“革命对象”。丈夫和我离了婚,因怕政治上受牵连,我的一儿一女也由我的前夫带走。我的好端端的家庭拆得东离西散。我变成了孑然一身,受到的是“监督劳动”的处分,每月只有三十元生活费,还要养活我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我被轮番下放到工厂、农村、农场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老实说,这些残酷的作法都未能摧毁我生存的坚强意志。我当时就深信,这种失误终将得到纠正,正像雷阵雨之后必然是晴天一样。信心使我增强了力量,就在宣布我戴帽、开除党籍的会议后,我面对着拆散家庭后的冷落空屋,认真地思考着我今后要怎样生活。我决心即使用行政命令剥夺了我的写作权利,我今生今世还要继续写小说。我下决心割舍我所热爱的短篇小说的写作,确定了写长篇小说的计划。在等待上级批示和下放期间,我偷着起早贪黑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在节假日,同志们都回家团聚,我孤身一人偷着在农村和农场空寂的屋里埋头写那部小说。不幸的是,1960年我的写作被机关中一位女同志侦知,马上汇报给支部。他们认为我“不好好认真改造,偷着写小说,幻想东山再起”而加重我的行政处分,降级,送发场“监督劳动”。“文革”时这部写了上百万字的小说差点遭到洗劫。如果不是被我的好邻居黄文声同志帮我用塑料雨衣包好,埋在他家床底下的煤球堆里藏匿起来的话。“文革”后期,我结束了干校“牛棚”的生活,又被“战备疏散”到农村安家落户。一辆“东风”小三马,拉着那点可怜的家当,三筐煤球和那部经过伪装的小说原稿,一同来到农村。我在独流咸河边一住就是八年——一个整个抗日战争的历程。1976年10月的一声春雷,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倒台,也结束了我21年的劳改生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上得到改正,恢复名誉、职务、党籍,重新恢复了我的写作权利,我重新拿起笔,日夜奋战,希望以我超常的努力,来夺回无谓牺牲的时光。这时我光明正大地打开那部尘封的原稿,进行修改创作。1983年整理出版了一部67万字的长篇小说《功与罪》(上、下卷),它描写的时代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二九”学生运动到1936年的学生大军南下宣传团的故事。我这次写的《战争启示录》,是《功与罪》的姊妹篇,人物是统一的,但有它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不看《功与罪》也完全可以读这部长卷小说。它所写的时代是从1936年的绥远红格尔图的抗击战开始,经历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也可以说,这部小说写的全部内容就是八年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
2.
如前所述,由于我有几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城市地下工作经历——它不是一般的经历,而是一段奇特的生活经历。为了生活,我去投考“华北食粮公社”,又因为我是清朝朝礼部尚书、协办内阁大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晓岚)的六世女孙,不想我这个“书香门第”的出身,一下子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看中,这个华北头号的大汉奸当时兼任着“华北食粮公社”的理事长,他不但录取了我,而且还聘请我为他的家庭教师,教授他德国老婆所生的三个女儿(一共六个女儿)中文和古典诗词,有时还兼做一些文字工作。这一特殊的职务,很快就得到我的地下领导人和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的批准,于是这儿就成为我的一个保险的隐身处——我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交通站,接待根据地来往的同志、往根据地输送知识青年、大学教师、搜集敌伪各种情报、散发传单以及发展工作对象等等的工作,又由于我有三年解放区战场的战斗生活,从司令部到平津战役的前线战勤工作,更重更的是在这些惊险的战斗生活中,我结识了不少英勇无畏的战友,勤恳工作的同志,他(她)们有的已壮烈牺牲,有的或已生病死去,但他(她)们的业绩和光辉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他(她)们的音容笑貌,平凡而伟大的道德品质,便成了我笔下活起来的人物形象。我对他(她)们无限怀恋,当我把他(她)们的故事写进我的小说时,自然也掺进和追忆了我无悔的战斗的青春。
例如我书中所写的女主角方红薇,就是有其生活的原型的。我遇到她时,是在1960年自然灾荒后,我被加重处分送往农场执行“监督改造”的时候。我和她编在一个组里。她比我大几岁,是个进城老干部。我刚见她时,她不和任何人接触并总是躲着人。在学习小组会上一言不发。她被批判为“改造态度最坏的典型”。不久,我和她在挑担粪,一个阳畦面对面地拔草,我俩很快就熟悉起来。不久我就了解了她全部奇特的历史和丰富惊险的战斗经历。她虽然和我是同时代人,但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她是遵化县大山里一位贫农的女儿,这里是属于美国基督教北美美以美教会的传教势力范围,许多衣食无着穷困潦倒的山民便成了向教会承租土地的“教民”,这种人家被称做“饭碗教徒”。她的家庭就是一户“饭碗教徒”。在她八岁那年,她在河边给她妹妹洗尿布,被那位来遵化收租的美国传教士偷走,把她带到北平传教士的家中,成了传教士的一名养女。这位传教士的老婆不能生育,他便抱养了四个中国孩子——两男两女,她就是其中之一。她不再是普通山民的女儿,而是美国传教士的养女了。这就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传教士是属于富裕阶层。在她上北平教会慕贞女子中学时,她赶上参加“一二九”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成了民族先锋队员。“七七”事变后,随着邓华支队开赴抗日前线,以后留在冀东革命根据地,成为真正的女八路。转战南北,东挡西杀。1947年5月21日,身为冀东区党委组织部长的丈夫,在赴赤峰开会途中宿于柴火栏子为叛徒出卖,遭国民党匪徒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全国解放后她进城天津,分配在天津农林局做一名副处级干部,专管农场工作。1957年在鸣放提意见时,只因她对局长提了一点意见就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送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1963年她摘掉了右派帽子,分配在一家牛奶站卖牛奶。1966年“文革”时她被揪斗得很厉害,脖子个挂着破鞋,因她幼年缠过足。造反派故意不让她穿鞋光着脚走,拿她取乐,这种失掉人的尊严的野蛮批斗,使她无比气愤,在她生病期间又因她是“专政对象”而不允许她住院治疗。1968年她病逝于天津。她的侄子把她的遗体葬于遵化老家她抗击日寇时的山上。1978年我落实政策后,到她的住处去看她。新房主冷淡地说:“她早死了!”于是我赶到遵化,在大山里寻找到她的老家,迎接我的只是山上她那座冰冷的坟墓。我在她坟前心痛欲裂地大哭了一场。当地的老乡,给我讲了许多她英勇战斗的故事。她能双手放枪,百步穿杨,日本曾以高额金票悬赏她的人头,以致乡亲们不得不做一个假坟头来欺骗敌人。像这样的英雄人物没死在抗日前线,而惨死在“史无前例”的政策失误上。真令人痛心啊!我坐在她度过童年的那间石屋里,泪流满面地在心里发誓,我一定把她的光荣业绩写进我的小说里去,以此来安慰她的英灵。否则就对不起这些牺牲于九泉之下的同志。我从遵化返回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农林局为她落实政策到坟头。她终于得到了平反改正,单位专为她开了追悼会。我的这两部长书,就是以她为生活中的主要模特而加以综合、概括典型化的。《功与罪》写的是她的童年被拐骗和青年搞学生运动的生活经历,而《战争启示录》则是写她抗日战争中在战斗里成长和她的恋爱、遭受非人磨难的故事。由于她的经历奇特,她的遭遇也奇特。
至于书中的男主角的模特原型,是我在军区部队时的一位作战英勇无畏的参谋长。“文革”时他被搞成“军内一小撮”而被批斗,他的妻子或由于害怕政治上受牵连,亦或由于攀附权贵向上爬而跟他划清界限。……为什么对一个抗日战争时期有功的英雄会有这种惨痛的命运?想一想,真令人悲愤。当然我也综合了更多的我熟悉的人物,形成了这个典型人物。我对他(她)们是如此地有感情。当我写他(她)们的时候,他(她)们的音容笑貌是那么栩栩如生地活动在我的眼前。我仿佛又和他(她)们生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峥嵘时代了。
苦难生活是培养作家的温床。它给我们这一代作家以毅力、勇气和思辨的能力。我只想说明,我依然深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个人的经历,对当时历史时代的感受、思考以及我所熟悉的人们的各种遭遇,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部小说的基础。因此,这就决定它先天的一个特点:生活是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是真实的,时